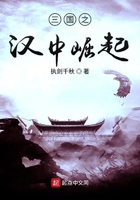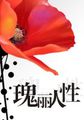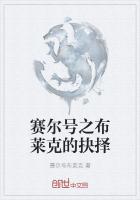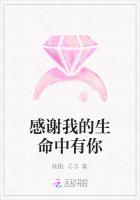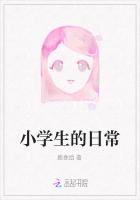一个小国的大政治家;一个纵横捭阖于大国之间的外交家;一个逆流而上意志坚定的探险家;一个大刀阔斧推行法治的改革家;一个客观评判鬼怪力神的哲学家……也许郑国的子产的头衔太多了,但是却是名副其实。只有100多年前的管仲(才)能与之相媲美,只是郑国国家褊小,地处四战之地,子产的改革也只能使郑国在大国之间维系生存。如果子产治理的是齐国、楚国或者晋国,那么他在历史上的威名绝不下于管仲。子产的改革开启了战国时期各国变法的先声,是一次承前启后的伟大改革。
铸刑鼎推行法治
子产生活的年代,礼崩乐坏,周王朝的政治秩序已经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各国士大夫已然成为国家的真正统治者,“陪臣执国命”的现象屡见不鲜。各国都经受着无休无止的政治动乱的折磨,预示了政治变革的到来。各国都身在一种外敌内奸的险恶环境中,如果不实施变法只能为潮涌的危机所湮没,郑国尤甚。
郑国自春秋小霸了一段时间之后,便如流星一样陨落,晋楚两大国仿佛是郑国身边的恒星,郑国时而围着晋国转,时而绕着楚国行,朝楚暮晋的事情,郑国人不知道干了多少次。更令郑国难受的是,内忧不断,弑君篡权,贵族作乱之事频频发生。子产深知郑国已经沉疴在身,必须下猛药才能治愈这个久病之国。面对不断猖獗的贵族势力,子产决定推行法治。
周公作礼之后,整个周王室都是以礼治国的,而礼的核心便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是一种严格的等级制度,庶人既不知道统治的秘密,也无法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来,他们只能接受刑罚的统治。所谓的大夫就是贵族,他们即使作奸犯科也不会受到惩处,更别说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争夺,杀戮无数,血染朝堂。
子产决定一改前辙,将刑法铸在青铜鼎上,公之于众,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懂得法律,按照法律的规则办事,一方面可以规制百姓犯法,另一方面又可以去除法律的神秘性,将贵族也置于法律的统治之下。贵族们曾经的遮羞布被撕扯掉了,因此子产的法治改革遭到贵族们的强烈反对。
在当时各国攻伐频繁的环境下,子产的法治改革引起了轩然大波。晋国无疑是当时的霸主,郑国是晋国的小弟,在霸主的眼皮底下进行这样的改革,必然遭到“大哥”的反对。果不其然,晋国的大夫叔向便致信子产,对他的改革表示强烈不满。信中说道:“先王治国都是以礼制,不事刑罚,而今您将法律公之于众,百姓已经对贵族没有敬畏之心,上下互相争利,成何体统?我看郑国离灭亡不远了。”
对于子产的改革,老百姓刚开始也不接受,认为子产破坏了既有的生活秩序,新制度刚刚推行一年,老百姓恨不得杀死子产。结果新法推行三年之后,百姓安居乐业,一片升平气象,百姓都感念子产的功德,在享受富足与和平的同时,他们开始担心子产死后,这样的繁荣将随子产而去。晋国的叔向固执己见,一再谴责子产破坏礼制,对于这样顽固不化的守旧分子,子产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吾救世也。”这句话可以让我们想到法国的枢机主教黎塞留的名言:“人可不朽,救赎可待来日;国家不得永生,救赎唯有当下。”
子产的法治改革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20年之后,晋国在赵鞅的主持下也开始铸刑鼎,各国纷纷效法。著名的历史学家周谷城先生认为,在中国的政治从礼治转向法治的转折之中,子产功不可没。
保乡校接受监督
子产荣任郑国之相后,大力推行改革,民怨四起,咒骂子产的歌谣开始在街市上流行开来。子产是个非常善于倾听别人意见的人,一天他上街遛弯,发现百姓正在乡校议论国事,其中不乏对子产不敬之语。乡校是当时的一个公共场合,人们在此休息,聊天,类似于今天的一个公共聚会的场所。
随行的然明跟子产说:“还是把乡校拆了吧,怎么样?”子产问:“为什么呢?人们劳动完了之后来到这里休息、聊天,不是很好吗?他们讨论国家的大政方针的得失,并不是一件坏事。他们觉得好的方针政策,我就推行下去;他们感觉不好的,我会修改。他们才是治国的导师呢。乡校就是我的课堂,为什么要摧毁呢?”然明点头称是。子产继续说道:“我听说,诚心正意为民做事,可以消弭百姓的怨恨,但是仗势弹压只能激起更多的不满与反抗。用强权堵住百姓的嘴巴,就像堵塞河流一样,水位越来越高,终归有一天大水会冲决堤坝,洪水泛滥,饿殍遍野。我没有挽救百姓于倒悬的能力,还是现在就开个小口子,疏导民意吧,循序渐进,也许会慢慢改变现状。”
然明被子产的一番高论给征服了,点头不迭,忙说道:“您的确是个干大事业的人,小人不才,没有您的胸怀与远见。现在郑国有了您做相国,真是件大喜事啊。如果您早日掌国执政,也许现在郑国会强大很多呢。”
孔子听到这个故事之后,对子产也是大为赞赏,跟别人说:“由此可见,子产是个仁义贤能之人。他日有谁再跟我说子产不仁不义,我是不会相信的。”
子产论鬼
春秋时期,人们还是非常迷信的,都认为人死之后必然成鬼,怪异的天文现象肯定有鬼作祟。春秋晚期中原地区出现过彗星,人心惶惶,那些巫觋便借题发挥,装神弄鬼。其他国家发生了火灾,那些巫觋们说,如果不按照他们的意思举办祭祀,郑国就要毁于大火中。子产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他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意思是说,天道很远,人道很近,相差十万八千里,那些巫觋怎么能知道天道呢?郑国人心稍稳,也没有发生火灾,人们更加佩服子产的高见。
精明子产糊涂事
子产将郑国治理得井井有条,这与子产的干练与精明是分不开的。据说有一次他乘车外出,听见一个妇人的哭声,没过一会儿,子产便派人将这个妇人抓了起来。一审才发现,这个妇人将自己丈夫给杀死了。
这件事情传出去之后,人们都把子产当做神人,即便作奸犯科之后,也不敢哭泣了,万一让子产听见,就会锒铛入狱。随行的车夫琢磨了好久,都没有参透子产听声破案的秘密,便忍不住问子产,靠什么判断这个哭泣的妇人已经犯罪呢?
子产笑了笑说:“这并不是很难,这个妇人的哭声中没有悲伤,只有恐惧,我猜测肯定是犯下了什么滔天大罪。”虽然子产并不觉得自己有多么高明,但是有几个人能听出哭声中的恐惧或者悲伤呢?毫无疑问这是精明的子产在长时间从政过程中磨炼出的独门绝技,郑国有这样一位如此精明智慧之人为相,不强大也没有道理。
话说有人给子产送了一条非常名贵的鱼,子产非常开心,但却舍不得吃掉,便让人送到后花园的鱼塘中,派专人看管。看管鱼塘的小吏听说连相国大人都不舍得吃,心想肯定是人间罕有的美味,于是便偷偷地把鱼给吃了。果然是一道美味,吃完之后,小吏便跑到子产那里报告说,那条鱼一放到鱼塘便摇起波浪,一会儿神龙见首不见尾,就不见了。
子产信以为真,便说:“看来这条鱼不喜欢这里啊,那就让它走吧。”小吏心里暗想:人们都说子产才智过人,怎么这么容易就被蒙过去了呢?这个小吏还以为自己比子产还聪明呢,因为他骗过了子产。
子产是个有大智慧、大视野的人,怎么会把心思放在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上呢?要不人们说,在奴隶眼中,从来没有英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