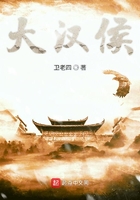凯撒目前所率领的兵力和凯特林昔日所拥有的那一小撮相当,而当前又无任何有效的预备部队,就对业已占据优势而又日日增加的、由能征善战的将军统率的敌人发动攻势,看似愚行,但这却是汉尼拔式的愚行。如果战争拖到春季开始,庞培的西班牙部队会在阿尔卑斯山北采取攻势,他的意大利部队会在阿尔卑斯山南采取;而战术上与凯撒相匹。经验犹多于凯撒的庞培,在这样阵式森然的战斗中,将是非常可畏的。在目前,由于庞培惯性的迟缓,由于他自信他一定能在大军召集之后发动战争,若给他全然不备的突袭,必然令他有措手不及之惑。冬季战的突发性与艰苦,对在高户受过严厉考验的凯撒十三军团,当不致造成重大挫折,但由凯撒的老兵与未经训练的新兵所组成的庞培部队却可能因之解体。
于是,凯撒进军意大利。从罗马向南,有两条公路:艾米利奥一卡西亚道,这条路从波农尼亚越过亚平宁山,至阿利提阿与罗马;波比利欧一弗拉敏尼亚道,这条路从拉文纳沿亚德里亚海边至法南,再从法南分岔为二,一向西?经富洛至罗马,一向南,至安康纳,再由此至阿普利亚。马卡斯·安东尼阿斯率军沿前路前进,直抵阿利提阿,凯撒则率军沿后路前进。抵抗根本不存在。贵族招兵官完全没有军事技巧,他们刚刚召集的新兵也根本还不是士兵。乡镇的居民惟一的希望则是不受围城之苦。当丘利欧带着一千五百名战士接近伊戈维的时候,厄布利亚的两千新兵闻风而逃,规模略小的溃逃事件处处皆是。
当凯撒的骑兵到达阿利提阿时,仅距罗马130英里了。凯撒必须决定究竟是攻取罗马,还是袭击鲁塞利亚的敌军。他选择后者,而令敌人大为惊恐。庞培接到消息说,凯撒正进军罗马。他一开始似乎打算防卫首都,但当他据报凯撒已进入比辛南地区,初战成功时,他下令罗马疏散。贵族社会于是极为恐慌,尤其是误传凯撒骑兵已兵临城下。元老们下令,凡留于首都者,一律以凯撒同谋论罪。于是争先恐后夺城门而出。执政官方寸完全大乱竟至国库未带。庞培要他们回取,因为时间尚绰绰有余,但他们说,如果庞培占领比辛南,国库当无问题。
一切均陷入混乱。结果,在提南·西底辛举行大会,参与者有庞培、赖宾纳斯和两个执政官等。凯撒的议和再度提出。凯撒到了此时仍旧宣布准备遣散他的军队,把高卢两省交给继任者,按照正常规则成为执政官候选人,但意大利须解除军备,庞培须至西班牙赴任。凯撒得到的回答是,他必须立即返回他的总督省,若此,则他们可以设法在首都促使元老院通过一项命令,使意大利解除兵备,庞培赴任。
这个回答或许并非明目张胆的欺骗,而实含接受之意。然而,在事实上表现出来的却完全相反。凯撒要求与庞培亲自会谈,但庞培却务须否决,因为他怕元老院对他的不信任更由此次晤谈而加深,因为元老院深恐两个军事将领有再度联合的可能。至于战事的安排,则提南会议同意要庞培执掌鲁塞利亚驻军的兵权。鲁塞利亚的部队虽然不可信赖,但现在他们却只有这一支部队可以用,会议决定由庞培将此部队率至比辛南——庞培与赖宾纳斯的本乡。会议决定,他当在此处以个人名义召兵(如35年前他曾做过的),率领比辛南可靠的同志与原在凯撒属下的老兵来抵挡凯撒的前进。
因此,一切都视庞培抵达比辛南之前,该地能否防守。但凯撒重新会合的部队却已经从安康纳沿海岸路进入该区。这一区,准备亦全然未妥。比辛南最北方的城镇奥克西慕,在普布利阿斯·阿西阿斯·瓦拉斯的指挥下,已经征集了人数相当多新兵。然而,在市民的要求下,瓦拉斯在凯撒到达之前,就撤守该城。在奥克西慕城前不远的防军,也仅由凯撒的一小撮部队即予驱散——这是此次内战中的第一次接触战。不久,盖阿斯·鲁西利阿斯·希拉斯也带着三千人撤出卡美利南,而普布利阿斯·蓝特拉斯·斯宾瑟带领五千人撤出阿斯丘鲁。这些人,忠于庞培,宁可抛家离舍,追随领导者越过边界。但当庞培派至该区的军官鲁西阿斯·维布利阿斯·乐博斯——这不是绅士般的元老,而是有战争经验的军人——到达,以整备初步抵抗时,该地已经失陷。他只能从无能的召兵官手上接取六七千新兵,撤至最近的集合地。
阿尔班西亚,马西亚与派林尼亚诸地区的指定集合地为考菲尼阿,而此处汇集的新兵已至一万五千人,系从意大利最好战最可靠的地区征集所得者,乃是可征之兵中立宪派部队的精英。维布利阿斯比凯撒早数日抵达考菲尼阿,因之他可以立即遵照庞培的命,就比辛南救出的新兵连,同集合在考菲尼阿的新兵共同加入在阿普利亚的主力。但考菲尼阿的司令为鲁西阿斯·杜米西阿斯,此人为元老院派定的阿尔卑斯山北高卢凯撒之继任人,是罗马贵族中最心胸狭小而顽固的分子之一。他不仅不肯遵从庞培的命令,而且禁止维布利阿斯带走比辛南的新兵。他是如此坚信庞培的迟来是由于顽固,而终则必定驰援,以致他不做认真备战,甚至不将周围各城镇召集的新兵聚集于考菲尼阿。
然而,庞培并没有露面。他固然用两个不可靠的军团做新兵的预备队,却无法单独用它们来对抗凯撒。几天以后,于2月14日,凯撒到达,其时,他已在比辛南会合他的第十二军团,在考菲尼阿附近会合第八军团;两团均来自阿尔卑斯以北。此外,又有三个军团业已组成,其组成分子部分系庞培部队之被俘者或自愿投入者,部分为随处召集的新兵。如此,凯撒抵达考菲尼阿之前,已有一支四万人的部队,其中半数有过战斗经验。
在杜米西阿斯仍认为庞培会来驰援时,他还做一些备战工作。但当庞培的信件终于骗了他时,他便决定再也不要死守在这孤立的岗位了(实则如果他守住这个据点,对他那一派有极大的利益),也不投降,却采取另一种方式:他通知士兵,援军即将到达,而自己带同贵族军官于次夜逃亡。然而就连这个小小的如意算盘他竟也无法如愿,因为他的慌张露了马脚。有一部分人开始兵变,马西亚的新兵试图对抗这批叛军,因为他们不相信他们的将军会做出这种丢脸的事。但终于他们也不得不承认事实,于是,全体部队将指挥部逮捕,连同该城于2月20日亲自交到凯撒手上。阿尔巴的三千人,集合于塔拉辛纳的一千五百新兵,在见到凯撒的巡逻骑兵时,迅即放下武器;而驻守于苏尔莫的三千五百人的第三分遣队前此业已被迫投降。
在凯撒占领比辛南之际,庞培就已非放弃意大利不可了。他想尽可能延缓上船时间,以救起他剩余的部队。因之他向布隆底西安——最近的港口——出发得相当迟缓。集合到这里来的有鲁塞利亚的两个军团,即庞培在弃守的阿普利亚匆忙召集的新兵以及执政官和其它特任官在坎班尼亚所召集的部队。此外还有若干政治难民,包括最德高望重的一些元老及其家属。船运开始,但船只不能一次运完全部撤退人员——总计约二万五千人。惟一的办法是把部队分为两批,大部分于3月4日启航;小部分(约一万人)与庞培则留在布隆底西安,待舰队回返。因为这个港口不论如何适于登陆反攻,却无法久抗凯撒。
同时,凯撒抵达,围攻开始。凯撒起先企图用堤道与浮桥阻挡回航的舰队,但庞培武装商船,设法阻止了堤道与浮桥的合口,直待舰队抵达。于是,在围攻者的骁勇、居民的敌意下,庞培仍极为巧妙的完成了登船的工作,不留一个士兵,未受任何损伤,驶向希腊。凯撒的追逐也像其围攻一样,因缺乏船只而一无所成。
如此,经过两个月,连一次重大的战事都未发生,凯撒已将十个军团的敌人击溃,其中落荒渡海而逃者不及半数。全意大利,包括首都及其国库均落入胜利者之手。败者有理哀号那“怪物”的迅速、明智与勇猛。
但凯撒的征服意大利,究竟是得是失,却很成问题。从军事上言,有很多的战争资源都为他所有,使他的敌人无法取得了。早在公元前49年春,由于到处征集的兵员,除了他原先的九个军团之外,他就已另有几个新军团了。然而,他现在却不但必须组织大量的卫戍部队,而且要对抗敌人封锁海运的战略;敌人封锁海运,首都庞大的人口就有饥荒之危。因此,凯撒原已复杂的军事任务变得极为复杂。
经济方面,凯撒取得国库当然十分幸运。但税收的主要来源,尤其是东部地区的,仍在敌人手中;军需品的日增,首都濒于饥荒的大量人口的供应,很快即将国库耗光。凯撒不久就不得不借助私人贷款,但这是一种无法持久的办法,因之大量的充公乃是一般预料的步骤。
意大利的征服所带来的政治难题更为艰巨。有产阶级普遍惧怕无政府性质的革命。不论朋友或敌人,都把凯撒视为凯特林第二,而庞培则相信——或装做相信——凯撒发动内战是因无力还债。这话固然纯属荒诞,但凯撒的先驱者们却事实如此,更令人不放心的是他的高级随员。名誉最成问题的,如昆塔斯·贺坦西阿斯、盖阿斯·丘利欧与马卡斯·安东尼阿斯(后者为凯特林纳利安·蓝特拉斯的继子,此人又系由西塞罗下令处死者),均身为最重要随员。若干久已不能还债的人,不仅养舞女,而且带着舞女公开露面的人,都被凯撒赐予高位。因此,就连政治上最持重、最无偏见的人都免不了预料流犯将得大赦,债权将被取消,肆行充公,剥夺公权,屠杀——不,甚至高卢士兵将劫掠罗马!
但在这一方面,那“怪物”却出乎他朋友与敌人的意料。当凯撒占领第一座意大利城镇阿利明南时,他禁止普通士兵携武器出现于城墙之内,而乡镇则不论敌友,都受到保护,免于任何伤害。当叛变的卫戍部队于夜晚包围考菲尼阿时,凯撒放下一切军事上的考虑,延至次日清晨进城,以免居民受到他愤怒的士兵的侵扰。俘虏之中凡不与政治有关的,均被纳入凯撒本军之中;军官不仅得到赦免,而且自由开释,不收押金,凡彼等认为系其自有财产者,亦不加严格审查即行交还。鲁西阿斯·杜米西阿斯本人就受到此种待遇,甚至赖宾纳斯留下的金钱行李也着人送至敌阵。
凯撒虽然经济极为困难,但他的对手们的巨大田庄均丝毫未动,凯撒宁可向朋友借贷,也不征收形式上可行、实际上亦早已有之的田赋。这个胜利者认为他的胜利只为他解决了少一半的问题,他认为只有无条件地原谅被征服者,他的胜利才得巩固。因之,从拉文纳到布隆底西安的路上,他不断重做努力,要跟庞培亲自会谈,以达成尚可忍受的妥协。
贵族们原先拒绝听取任何谈和之议,而现在,他们的败北则使他们原先的愤怒变做了疯狂。胜利者的谦和与失败者的气焰构成奇异的对比。这些败北者给全意大利各处的友人书信中,充满了充公、剥夺公民权、清除元老院与全国等等可怕的预料,与之相比,苏拉的复辟只算得游戏。这些话,连他们派系中较为温和的分子听了都不寒而栗。
无能者的狂乱和有力者的温和之间的对比,产生了结果。把物质看得比政治重要的份子,整个投入凯撒的怀抱。乡镇将胜利者的“公正、温和与明智”偶像化;甚至他的敌人也承认人民的这种敬意是出自诚心。大资本家,包税商与陪审员,在立宪派于意大利沉船后,不再急于希望把他们的命运重新交在相同的船员之手。资本又从隐藏之处出现了,“有钱的爷儿们又重拾他们的日常的工作,写账。”
元老院的大多数——至少从数字上言之,因为较高贵而有影响力的甚少包括在内——都没有理会庞培与执政官的命令,而留在意大利,他们默允了凯撒的统治。凯撒的温和态度即使在表面上看来过分,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种温和态度平息了有产阶级的焦虑,因而有助于实现其本意。无疑这对未来的安定与巩固,对无政府状态的防止,有重大的贡献,更有助于共和国的重新组织。
但以短程而言,这种温和却比辛纳与凯特林的愤怒更有害于凯撒。有时它不仅未将敌人变为朋友,而且将朋友变做了敌人。那些凯特林式的依附者,由于凯撒禁止他们掠夺杀人而愤满于怀,而那些大胆的亡命之徒——有些颇具才华,——则希望一展其离经叛道的长才。共和派份子则既没有被凯撒的宽大所改变,亦没有因之受到禁止。依照迦图派的命令,对他们所谓的祖国的义务超过任何其它考虑;即使那些生命与自由均受凯撒再生之恩的人,都有义务拿起武器来反抗他,至少也要设计反对他。那些温吞水的立宪派无疑愿意接受新君主的和平与保护。然而,他们在心里仍并未停止对君主及君主制度的诅咒。
政体的改变越趋明显,大部分公民——首都与乡镇者皆然——对共和的意识就越为强烈。立宪派在罗马的友人向流亡海外的弟兄们报告,家乡中所有的阶级,所有的人,都称赞庞培。这并非言过其实。贵族们对卑微与温吞的大众所造成的影响也愈使这批人不满。高贵者会因自己留在意大利而自责,半贵族则会因自己流亡海外而觉得置身于平民之间,即使自己坐在凯撒那批小人物组成的元老院中也仍觉自怜。凯撒极端的宽厚越发使这种沉默的反对有日增的政治重要性。由于凯撒一直不肯使用恐怖政策,他秘密的敌人便能够表示他们的不满,而不致冒险。
如此,不久凯撒就在元老院手中受到颇为可观的待遇。他内战开始是为了解放这噤若寒蝉的元老院。现在,在做到之后,他希望元老院赞同他的这种解放运动,并赋予他全权继续作战。为了这个原因,站在他一边的护民官于4月1日召开元老院会。与会者甚多,但仍在意大利的元老中最著名的一些,包括马卡斯·西塞罗——那奴性的大多数之原先的领袖——却缺席,凯撒的岳父鲁西阿斯·毕索竟也在缺席之列。
更糟的是,出席者对凯撒的提议也十分冷淡。当凯撒要求继续从事战争的全权时,出席的两个执政官级的人物之一,塞维阿斯·瑟比西阿斯·乐傅斯——这是个胆小如鼠的人,他惟一的愿望就是平平安安死在床上——说,凯撒如果放弃把战争扩延到希腊与西班牙的念头,则功莫大焉!凯撒于是提议,至少把他的议和之意转达庞培;这个提议未遭反对,但离城者对中立派的威胁如此严重,以致没有一个人敢于承当运达橄榄枝之任务。
由于元老院惯有的惰性,不久以前,庞培想求得内战司令之任命而不成。现在,凯撒自己也在同样的要求上受挫。其他障碍也随之而来。凯撒希望被任命为独裁者,以便使他的地位合法化。但这个希望未能如愿,因为依照宪法,这样的行政官只能由执政官指派;凯撒想收买执政官蓝特拉斯(他的经济状况极乱,因之甚有可能),却未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