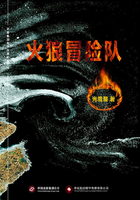当萧唯再次给江河讲述着凌萱的婚事的时候,江河再也不敢有口无心地应付妻子了,他听得津津有味,不时地还发表一点意见,让萧唯心里很是受用。
“当初人家凌萱可没少说你的好话!”
萧唯刻意地提醒丈夫不要忘本。
江河笑笑,没有做声,他分明记得凌萱也曾经对萧唯说过,北京的气候干燥,不适合上海的女孩子,这可是当时萧唯告诉他的。
对于萧唯选择了江河,凌萱当年可是很有些看法的,虽然只要萧唯感觉自己的爱情和婚姻美满她也会为之欣慰的,但她却象很多上海女孩子一样,从来都对上海以外,尤其是北方的男孩子有一些天生的抵触,她觉得上海的男生是这个世界上最温柔,最体贴,最适合做恋人和丈夫的了,为此,当爸爸的朋友钱伯伯的小儿子奉了其父之命专程来上海探望病中的凌萱的父亲时,那个马来西亚长大的男孩子虽然对她很明显地表露出爱慕之情,她还是不屑于父母的期望,很坚决地拒绝了。
“伊虽然生在上海,却一点都不象上海男孩子,肯定是因为在大马长大的原因,那些穆斯林国家的男孩子们都太大男子主义了!”
这是凌萱拒绝了钱伯伯儿子的追求的唯一理由,让她的父母从此感到对那位海外的老友心存一份歉疚。
“北京的男孩子是不是都很大男人?”
凌萱在萧唯和江河热恋的时候纠缠着她问。
“听说伊拉会打老婆的。”
萧唯差点被她气乐了。
“侬讲的啥格年代的皇历了!”
凌萱仍然不放心地盯着萧唯,似乎在研究她的话的真实性。
“要不要我脱了衣服让侬验验伤啊?”
萧唯调侃着。
凌萱相信了萧唯所说不妄,但还是对北方男人,不应该说是所有上海以外的男人心存一份戒备。
“凌萱最终还是嫁了个上海男人。”
江河有些替凌萱惋惜,在他看来,上海男人实在是比不上北京男人,让他象上海男人那样纤细温柔,他觉得简直是一种对男性的禁锢和摧残。
“上海男人怎么了?”
萧唯并不觉得上海男人有什么特别可爱的地方,但也没有觉得他们有什么不好,如果连对妻子的体贴和温存都能算得上是过错的话,那这世界上就不存在没有缺点的男人了。北京男人固然洒脱和大气,但并不能就说是十全十美了,他们的粗枝大叶,他们过于强烈的男人气息,有时候对女人来说也是一种压抑和桎梏。萧唯觉得无论是什么地方的男人,只要是深爱他们自己的女人,无怨无悔地承担起一个成熟的男人应尽的职责,他就是一个好男人,以地域界定男人的优劣,不论是上海人的标准,还是北京人的尺度,都难免有偏颇之处。
“上海男人也有好的,北京也不都是好男人!”
萧唯一句话把江河的嘴堵了个严严实实。
凌萱告诉萧唯,她的新郎是个医生。
父亲生病住院的时候,凌萱每天都到医院去陪伴他。凌家的家境今非昔比了,两个出洋的子女让他们家的生活早已超出了一般上海百姓的水平。几年前他们已经搬出了棚户区,住进了虹桥开发区的高档公寓,尽管过惯了清苦日子的父亲不愿意为自己的病过多地花费金钱,凌萱还是坚持让父亲住进了高级病房,又请了一个护工专门照顾老人的起居。父亲的病情稳定之后,凌萱开始考虑自己的工作问题了,以父亲目前的身体状况,短时期内自己是无法离开上海的,虽说父母多次表示他们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但凌萱还是觉得应该尽到作儿女的责任,尤其是在姐姐和哥哥无法守候在父母身边的时候,她肩上的担子就更加沉重了。现在的工作并不难找,难的是要找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凌萱所学的专业是法律,尽管这最初是当年钱伯伯的意愿使然,但经过了四年的学习,凌萱还是对这一领域有了更深的认识,也切实地喜欢上了自己的专业。她找了几分工作,却都不很满意,不是专业不对口,就是待遇不合适,难怪现在的大学毕业生都要提前一年,甚至更长时间就开始联系工作单位呢,看来临时抱佛脚确实是比较困难的。
“后来还是我现在的老公帮了我的大忙呢!”
凌萱在电话里对萧唯说。
负责凌萱父亲的病房的是一个三十出头的男医生年纪虽然不大,却已经是主治医生了,凌萱听说他是上医大毕业的博士。
因为父亲的缘故,凌萱和这位姓吴的医生渐渐地熟悉起来,吴医生对患者很负责任,每天都要亲自查房,遇到病人有什么情况随叫随到不说,还会主动地经常来探视慰问一番。凌萱生就的乖巧可人,为人 又很明理得体,一来二去的,和吴医生就成了十分投缘的朋友,有空就往一处跑,越聊越热乎,都觉得对方有那么一点意思,却谁也没有挑明。
吴医生了解到凌萱正在找工作,又听说她为了照顾父亲把出国的事情都耽搁下来了,很是感动,自告奋勇地替凌萱张罗起来了。做医生的一般都是结交广泛,方方面面的人头都很熟悉,本来嘛,人吃五谷杂粮,无论尊卑贵贱都难免有个病啊灾啊的,所以吴医生接触的患者中自然少不了有权有势的人物,吴医生回去把通讯录翻了一遍,还真挑拣出几个法律界的头面人物,立刻逐一地打了电话过去,当即有几位满口应承下来。
凌萱最终进了一家颇有名气的律师事务所,做了那位曾经也是吴医生的患者的首席大律师的助手。
“只要跟牢伊,用不了几年,侬就可以成为上海滩上著名的律师!”
吴医生对自己的患者,对凌萱,包括对他自己都充满了一份强烈的信心。
在后来一切似乎都顺理成章地发展下去了,为了报答吴医生对父亲的救治和对自己的关怀,凌萱接受了他的邀请,开始和他约会。一年之后,当父亲的病情得到了控制,吴医生腼腆地跑到凌家求婚的时候,两位老人就只剩下抿着嘴乐的份了。
“侬一定要来的,阿拉结婚以后,就要一道去马来西亚了,我去上学,钱伯伯给伊也联系了一份医院的工作。阿拉这次分开,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唯唯,侬一定要回来一次,我老想老想见见侬噢!”
凌萱情真意切地恳求着萧唯。
“咱们结婚的时候,我只是和凌萱和赵婉伊打了个招呼,也没有让她们来,现在凌萱正式地邀请了我们,不管你去不去,我都得回去参加她的婚礼。”
萧唯很坚决地对江河说。
江河梦见自己做了爸爸,一个粉团似的小男孩扎撒着手抚摸着他的下巴,然后“咯咯”地乐着,对抱着他的妈妈说,“爸爸的胡子好扎哟!”,江河想去看那个年轻的妈妈的脸却怎么也看不清,一着急,醒了。
和岳晴分手后,江河总是在做着同样一个梦。自从岳晴打掉了她肚子里那个属于他和她的孩子之后,这个被无数遍地重复过的梦就无休止地纠缠着江河,说不定会在什么时候冒出来,让他激泠泠地打个冷战,醒了,在精神的煎熬中慢慢地等待着黎明的到来。和萧唯确定了恋爱关系后,江河已经很少再做这个梦了,特别是他们结婚以后,他就没有再做过这个永远是没有结尾的梦,直到今夜,现在这个梦又象是复活的幽灵,悄然地飘入了他的梦乡,那么清晰,那么熟悉,就象是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一样。于是,他又从梦中惊醒,又开始痛楚万分地在不眠中企盼着黎明的到来。
岳晴过去时常笑话江河的过于敏感,她猜测说,这多半是搞美术的人的通病,对形象和色彩的执著,让他们的注意力总是太过集中,因此不免会引起精神上的紧张,对于一切在常人看来都不足为奇的东西,都会夸张地勘出一份非比寻常来。江河有时候觉得岳晴更能理解他,毕竟他们的生活环境和身世背景比较起萧唯和他来要相似得多,就是在性格上他们也很相象,都是那种自我中心感很强,很情绪化,又很敏感的人,虽然岳晴时常笑话江河的敏感,其实她自己恰恰也是这样的人。“太过相似的人往往不能最终走到一起。”这话好像还是一句至理名言,不过不管它是不是名言,江河确实觉得它很有道理。和岳晴在一起的时候,他会觉得好像彼此的举手投足、思维心态,对方都很了解,甚至是早有预感似的,无论对方做出什么在别人看来很不合乎常理的事情来,在他们彼此看来却好像都再正常不过了,就连当初岳晴对他提出分手的时候,他虽然免不了痛苦不堪,及至今日依然无法完全释怀那段情感,但在她开口的那一刹那,他觉得一切都很正常,那样的一种情形,那样的一种感情寄托的方式,那样的一种情感状态,不分手?才怪!
岳晴问他,是不是已经知道了自己要离他而去?他点点头,脸上平静得没有一丝意外。岳晴说,其实即使她不提出来,早晚他也会提出来的。他想了想,觉得似乎应该是这样的,就又点了点头。
“这样看来,我做得没错。”
岳晴似乎对自己很满意。
“那你怎么不夸夸我?”
她象他们刚认识的时候一样俏皮地歪着头望着他,然后不等他的夸赞,转身走了,走得象一阵拂面而过的风。
江河在和岳晴分手后的这些年里,一直在责怪自己,竟然没有在岳晴提出分手的时候,给她一个衷心的赞美。五年的耳鬓厮磨中,江河给过岳晴无数次的赞美,却在分手的时候吝啬了那么一次,就是这唯一的一次吝啬,让他把不安长久地留在了心头。柳林在得知了岳晴和江河分手的消息后,特地来安慰江河,把无限的遗憾写在脸上。当这个一向自诩为江河和岳晴的“介绍人”的老同学试探着问江河,是不是有些记恨岳晴?江河很惊异地看看他,然后让他听了目瞪口呆地告诉他,岳晴替他做了原本该由他来做的一切。
如果有人一定要追究一对分手的恋人或者离婚的夫妻间的孰是孰非,这个人不是疯子,就是笨蛋!江河一直到现在也是这么认为的。不错,岳晴曾经在他的心头插上了一把锋利无情的刀,让他的心从此滴着永远无法止住的血,但江河知道,倘若岳晴不那样做的话,早晚他也会自己插上那刀的。这绝不是什么自虐或者自我伤害,就象是一个救死扶伤的医生,在面对一对连体婴儿的时候,如果牺牲一个可以换回另一个的生命,他还会有假仁假义的选择吗?与其两个人在痛苦中互相折磨着一同死去,还不容把痛苦让一个人承担,以解脱另一个,这样世界上至少会有一个健全、完整的人和一个欣慰的灵魂,而不会多出两个满怀怨恨的孤魂野鬼。
“就象是在战争中,当遇到危难的时候,真正的战士选择的是死亡,而把生存的机会留给妇女和儿童。我是男人,男人就该承受他应承受的那一份,不论是幸福还是不幸,不论是甜蜜还是痛苦,也不论是生存还是死亡。……”
柳林在和萧唯熟识之后,一次在和江河夫妇聚会的时候,酒至半酣,忽然象朗诵诗歌一样,把当初江河对他说过的这番话说给萧唯听,让她抱着江河,感动了好半天,泪水把江河的肩膀都浸湿了。
“如果我是岳晴,我会感动死的。”
萧唯呜咽着说,一双泪眼凝望着江河。
岳晴并没有象萧唯一样感动,因为她知道换了自己,也会那样说,那样做的。
“其实你应该感激我。”
江河带着萧唯回到北京的一个月之后,岳晴给他打了个电话,第一句话就是这么说的。
江河在电话的这一头点了点头。
“我已经在心里感激过了。”
江河知道自己说的完全是心里话。
没有和岳晴的初恋,江河不会懂得什么是男女之间炽烈火热、激情四溢的爱;没有和岳晴的分道扬镳,他永远也不会知道为了爱付出的牺牲其实是那样的壮烈和美丽。江河感激岳晴,无论是在精神和肉体上都是她把自己造就成一个真正的男人;江河感激岳晴,是她让他明白了该如何去珍惜一个自己所爱和爱着自己的女人。于是,江河真诚地感激岳晴,替自己,也替萧唯。
萧唯早上起床的时候说是准备下午去看医生。
“不是说没怀孕吗?”
江河半夜没睡,红着眼睛望着萧唯。
“我最近精神很容易紧张,不知道是不是心理有什么问题,我想找医生咨询咨询。”
萧唯一边穿着衣服,一边解释说。
“我陪你去。”
现在萧唯是他的唯一,江河不能不格外地珍惜她。
“不用。”
萧唯给了他一个感激的微笑。
“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毛病,还用得着这么兴师动众的?”
江河依旧不放心。
“真的不用我陪你?”
“不用!”
萧唯加重了语气,然后在江河的颊上拍了拍。
“你忙你的吧,没准儿我今天还抽不出时间呢。到年底了,各个单位都忙着突击花钱,这几天生意好得不成,事情特别的多。”
萧唯对江河说是事实,却不是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