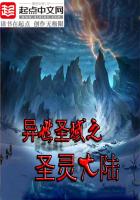春节刚过,成毅叔和乡亲们一起,随着移民搬迁的浪潮,将苦心经营了二十多年的家从故土腹地深处的小山村搬往较为平坦开阔的平原地区。异乡的柏油路上,夜色淡淡,凉风习习,劳碌之后归家的成毅叔不会想到,我们谁也不会想到,那个看似平静的夜晚,却酝酿着浓烈的血腥。当刺眼的灯光射向骑在摩托车上的成毅叔,当飞奔的农用车为了绕过路边的一堆沙石而脱离自己的运行轨道直撞向对面骑摩托车的人时,一场惨祸就地发生,我身壮如牛的成毅叔来不及喊出声音,连人带车被疾速的农用车撞出十多米远……刺耳的刹车声惊动了路边的住户,却惊不醒血肉模糊的成毅叔……还等着他回家吃饭的妻子,还未成人的儿女,他都撒手不管了;还未砌好围墙的院落,还未安好门窗的房屋,他也顾不上管了。
想着成毅叔,我的身心被巨大的关乎生命的无常和虚幻所笼罩。
有一年,从春到冬,我的目光从办公室窗户望出去,刚好落在一栋正在施工的楼房。绿色网布围住了楼体,隐约可见建筑工人晃动的身影,有时,他们的身躯在高高的支架上,工作服,安全帽,盯着他们,我会默默祈祷。我盼着那楼快些盖成。冬天了,楼房还没有完工,冷风阵阵吹袭,那些绿色的网布鼓着风,一晃一晃的,遂又掀起一波一波的褶皱,风大时更甚。寒冷中,偶然会见一两个人影在那里。我没有走近那楼,不清楚大冬天那些人还留在工地上干什么,想来是看工地的吧。工地上堆放着的材料、器具,总得是要留着人看护的。
第二年春天时,工地上重新热闹起来。一个黄昏,我带了女儿专门去那处工地看看。刚好是吃饭时间,民工们三个一簇,五个一伙,倚着工地上简易搭建的板房墙面蹲着,端着大碗,手里是大大的蒸馍。吊车、搅拌机、脚手架,那时候都歇缓下来,没有声响。女儿小声说,她听见了那些人吃饭的声音。我告诉她,他们吃得正香,不许打扰的。我们绕开堆放的杂物,从一条小道轻轻走过去,没有人阻止我们,一直走到小道的尽头,再没看见有人。一个墙角处,拴着的黑狗毛色光滑,竖着耳朵,有警惕之相,却并不出声,我们走远了,回过头去,那狗还盯着我们看。
现在,从窗口望出去,那栋早已完工的大楼很气派地矗立着,我不知道它要用来做什么,这不是我关心的事。那些曾在那处工地卖力干活的人也不知去向,那也是我所关心不了的事,可我总是记得那些安全帽,那些工作服,还有他们模糊的面孔。
最慢的是活着
她生于1923年11月。肖猪。
哦,她90岁了!
她生有五个女儿。56岁寡居。
将近三十年中的绝大多数时间,她一个人守着土院子,旧房子。一个人的炊烟也袅袅,一个人的院落也喧嚣,狗儿跑羊儿叫,蔬菜和花草的味道飘散在房屋上空,生命的气息纯正而浓烈。
近两年,小城里她所寄居的一百多平方米的房子里,三个卧室,客厅,餐厅,卫生间,这些有限的空间,她偶或扶着墙壁走动,迟缓无言;偶或双手背后,腰身伛偻;偶或倚门而站,瘦小孱弱。她这里瞅瞅,那里看看。寄居,这是她自己说出来的意思,在女儿家里,她一直觉得不是自己的家。有意无意间,她一副寂寥落寞的神情,诉说自己没生下儿子,老来没个去处,只能住在女儿跟前。她总是怀念在乡间的老院子,那是她自己多年经营的家,只可惜她已经没有自己打理生活的能力而独自住在那里了。
她平日几乎不下楼,只有在阳光和暖的日子,我们将她背到楼下,坐在凳子上晒晒太阳。她眼睛越来越不好使,看人也是模糊不清,喝水的杯子得放个固定的地方,并要给她说清楚。她刷牙洗脸,得有人帮着给倒水挤牙膏拧毛巾。有时大小便失禁,衣服湿了脏了,我们收拾洗整时,她会满脸赧色。
我们在餐桌上大快朵颐时,给她碗中夹放一些菜,她总是说够了够了;我们在电视机前争着论着时,她安静在一旁,眯起本就不够明亮的眼睛认真瞅着电视;我们围着孩子嬉闹时,她会立在一边,自言自语,或只是抿嘴微微含笑。给她吃水果,也只仅仅是一小块苹果,两瓣橘子,半牙西瓜或半截香蕉。有时候看着她,我会想她一个人待着时,都在回忆些什么呢?一定会想起过往岁月里经历的快乐和痛苦。我们有时拉起她满是褶皱的手,她会说都没样子了,还活着麻烦别人。给她洗头时,看着稀少的灰白发丝轻飘飘的,怎么也想不通她说自己当年有两根又粗又黑的长辫子。给她洗脚时,那些变形的脚趾让我们的孩子大为惊讶,她就会东拉西扯讲起当年缠小脚的事情。
很多时候,她蜷在小卧室的床上。枕头旁边,放着眼药水、止疼药、钙片。我们有空坐在她身旁说话时,她长长叹了气后,零零碎碎说起过往的人和事。说得最多的,是她被土匪活活烧死的父亲,被粗暴乖戾的继父气死的母亲,还有有着秀才之称却古板倔强又早逝的丈夫。岁月的河流不能带走那些使她疼痛的刻骨的细节,说着时,她黯淡无神的眼里有泪水滑落,伸手帮她轻轻抹去的那一刻,我觉察到了指尖的温热,还有冰凉同在,这感觉,许是一个慢慢走在生命旅途的老人心头错综的心绪。她也常感念着这世间的诸多好啊,寡妇拉娃娃,很多艰辛,生活却是一天天好起来了,女儿们长大了,一个个进了学校读书,一个个嫁人生儿育女日子过得不赖,不再像她和她的母亲在过去遭罪又受气,女儿女婿孙子孙女都对她好,她住乡间老院子时,节假日孩子们大包小包提着回去看她,她年老体弱了,也不用一个人受罪,来到城里跟孩子们同住,好吃好喝好穿的伺候,念叨着这些时,她又抿着嘴轻轻笑。
我们的孩子看她高兴,就缠着她讲跑土匪的事。她说起王家土匪马家土匪,无法无天,杀人放火,而有一拨土匪却是仁义得很,从不动穷苦百姓的东西。一声叹息又一声叹息。听她说那么遥远的事,遥远到有时我的母亲也须得想了再想才能理出个一二来,她却是说得那么努力而认真。而有时候,你问她中午或晚上吃了什么饭,她又是不记得了。
每次看见她时,就想起那句话:最慢的是活着。乔叶的文字就在心底铺漫,心绪跟着铺漫。乔叶笔下的祖母,我的外祖母,我们的祖母和外祖母,她们活着或死去,在时光的隧道里,究竟是短还是长呢?我们大家,都是泅在时间里的微粒,悠然安享生命的愉悦也好,拼命吸附残存的养分也好,一年一年,从孩子变成青年,从青年变成中年,从中年变成老年。我们的肉身和灵魂被时间裹挟着向前,向前,直到某一日终止!某些时候,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罢,你总是在时光里,被宠幸,被承认,被重视,被追逐,被诱惑,被哄骗,被冷落,被遗忘……更多,酸的甜的苦的辣的,本质是你活着。活着,是一场享受,也是一场苦难。
外祖母,从过去到现在,从咿呀学语到垂垂老矣,借时光之手,一页页抚过她的记忆,悉数所经历的那么多那么多,她的伤痛她的无奈,她的欢喜她的快乐,谁懂?!最慢的是活着!也只有活着便是最懂了。
很是喜欢乔叶的《最慢的是活着》,看过不止一遍,那份喜欢愈来愈深。那些文字,清水漫流般,流过眼睑,漫过心田,让心生关乎生命的柔软的疼痛和哀叹。
小说结尾,基本已经熟记于心了。在这个安静的夜晚,想着孤独的外祖母,想着生命的孤独本质,那段文字就跳将出来了——
我的祖母已经远去。可我越来越清楚地知道:我和她的真正间距从来就不是太宽。无论年龄,还是生死。如一条河,我在此,她在彼。我们构成了河的两岸。当她堤石坍塌顺流而下的时候,我也已经泅到对岸,自觉地站在了她的旧址上。我的新貌,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她的陈颜。我必须在她的根里成长,她必须在我的身体里复现,如同我和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和我孩子的孩子,所有人的孩子和所有人孩子的孩子。活着这件原本最快的事,也因此,变成了最慢。生命将因此而更加简约,博大,丰美,深邃和慈悲。这多么好。
我们,因为活着,所以珍惜。
从你的世界轻轻走过
偶然的机会,见到了传说中的哑巴。个头适中,身材匀称,五官端正,偏黄而光滑的皮肤,圆形针织帽子,雪青色毛衣,浅灰色旧外衣,黑裤子,布暖鞋,显得干净利落。站在她面前,我一时竟不知怎么表达自己的问候。倒是她揭开门帘,满脸笑意,手势示意我快进屋去。
屋子虽小,但整洁温暖。红砖地拖洗得潮湿而干净,炕角被褥叠放得有棱有角,桌上的瓶瓶罐罐摆放得整整齐齐,地中央的炉子擦得黑亮黑亮。连用来装炭的塑料桶外体都收拾得干干净净。
哑巴是姐姐的婆家婶子,先天性聋哑。姐姐曾给我讲过,哑巴勤快能干,为人热心,生有两男一女,生活算不上富裕,但衣食无忧。真是个心灵手巧的女人,一手好茶饭,针线活儿人见人爱,就是顺便拿起手边的毛巾,折叠几下,活生生的小狗或小兔样儿就在眼前了。姐姐说她刚结婚时,因为不熟悉哑巴的生活,她们交流时还制造过不少趣事呢。从姐姐那里听到的哑巴也仅仅是不能说话罢了,她的生活简单而丰富,似乎还比家里其他人多了一些机灵和耐心呢。
前几年,因为遭遇家庭变故,哑巴曾大病一场,在炕上躺了很久。也就是那段时间,我从姐姐姐夫口中频频听到关于哑巴家的事情。出嫁的女儿因为家事和婆婆闹矛盾,年轻不更事一气之下喝了农药,待人发现时身体已冰冷;外出打工的儿子遭遇不测身亡异乡……噩耗一个接一个,哑巴挺不住,病倒在床,不吃不喝,大概是心生绝望,也想一走了之吧。姐姐说,那段日子,看着哑巴真是可怜啊,披散着头发,急得用手抓破了自己的前胸后背。无声的世界,没有语言的生活,除了自己的比比画画,吱吱呀呀,她内心的苦痛和煎熬别人又能懂得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