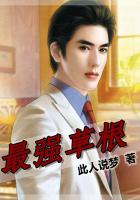老爸听医生的建议早晚坚持锻炼,注意饮食,精神状态很不错;大嫂再来复查时气色好多了,大夫说恢复得很好;老家捎话来说我姑扶着东西也能挪步了。这些情况让我感到些许的安慰,但细细想这些事情,内心的阵阵燥热会不停地袭击我,我无奈焦急郁闷。老爸干了大半辈子公家的事儿,老来退休生病尚能享受国家规定的退休干部医疗保障,而我大嫂我姑她们呢?辛辛苦苦一年到头,为的是家里生活好过些,孩子吃好穿好些,谁能料到病了伤了一进医院动辄就花去家里所有的积蓄还不止。大嫂要不是小腹胀痛经血猛流不止不能干活说什么也不会来检查动手术的,姑要不是亲眼看着自己被石头砸得断裂的白生生的腿骨头,而是轻微的伤筋动骨,她会来医院吗?而我们呢?我和丈夫不过是有幸在城里谋得一份工作干,靠不高的工资养孩子供房子顾及老人,我们能帮的就是多跑跑路,多长长精神,买点零吃的零用的,给几个少得可怜的钱,我也想好好帮他们的,可心有余而力不足!问他们关于农村医保的事,他们什么也不知道。
唯有叹息一声。
秋日之夜
秋的凉意一日胜似一日。
绵密的雨丝让这座小城在白日里更显寂寥冷清,而在夜晚,不够奢华的灯光亮起,却有了朦胧的醉人的感觉。
夜色,很好地藏匿了人们的重负和疲惫。
在光亮处,在幽暗里,在雨丝下,在遥远的似乎是河水的流动里,在似有若无的乐曲声中,一定是存有了那些属于小城的故事的。
街道两边的有些店铺已关门上锁,而另一些才开始热闹,闪烁的彩灯,晃动的人影,嘈杂的话语,衬托着夜晚的生活。
雨中的树木习惯了承受秋的寒意,枝头偶有那么几片叶子,恰被透过的光照得亮亮的,倏忽间,让人觉得那里会于瞬间产生童话故事。
街头,有踽踽独行的身影,没打开的雨伞提在手中。猜不出那个人的年龄和身份,也无法看清他的神色,只察觉到他的缓慢,缓慢的脚步带动缓慢的身姿,许是连思维都较白天变得缓慢了。不知道他的目的地在何处,想象他是孤单的,却没有理由,也许此刻一个人的缓慢行走正是他一天生活的最好状态,幸福的感觉正涌动在他的血液里呢。
更多一些的人,在这样的雨夜,还是希望有人伴着,有酒伴着。于是,便开始了呼朋唤友,漫谈小酌或歌舞笙箫。
说到底,人,总是害怕孤独的。说着话,喝着酒,即便是孤独,也都暂时被搁浅在一边了。表象的繁华在特定时候是很能麻醉人的,所以,聚在一起的每个人都很热烈,都很果敢,都侃侃而谈,都很有感觉地做着这个小城的一分子,都在这个秋日的夜晚赋予小城一种区别于乡村的气息和氛围。
没有人真正能拒绝内心的不安。生活的安宁不等于灵魂的安静。他或她正用文字,用图片在网络里构造着自己的精神世界。窗外细密的雨丝或许更能牵动他们的情怀,没有月光的夜晚,却有月光般的富有和静谧。倾诉,发泄,说出,都是方式,不要拒绝,只要守候,不要评说,只要倾听。而一个倚窗远望的背影,她的面前或许已然铺开一片海,幽蓝舒缓的《月光曲》正从心底升腾,演绎成一个清亮的世界。
有一条巷道,却没有青石板铺就的小路,没有撑着油纸伞走过的姑娘。老房子斑驳的墙面上凌乱地布满着各种字迹。这是将要被拆掉的巷子,静静的雨夜,昏暗的灯光,幽怨和惆怅是否该属于小巷?小巷不知道自己的命运,被拆掉就意味着改头换面,被拆掉就意味着永远地消失,被拆掉就意味着进入历史。小巷曾有过辉煌,被拆掉就意味着消散了它的芬芳。以后,没有几个人会知道巷子曾在这个雨夜有过一地忧伤和孤独。
杯盏趋于静默。
声音渐入沉寂。
忧伤慢慢消遁。
雨丝飘然依旧。
夜晚渐渐沉入深处。
比梦更深。
一些比秋夜更深,比梦更深的心事渐渐泛起……
在路上
从早晨开始。
车子行进在山间公路上,一段一段已经失修的路面显得破败不堪,人的身子随着车身摇晃不定,车后漫起的尘雾翻卷过来,窗玻璃立时就落上了一层细尘,那些猛然间铺落了一层的尘土,随着车子的走动,又慢慢滑落下去,我闻到了灰尘的气味,是干燥的土腥味,干燥到不带一丁点儿山野的清新。是啊,好多天都不曾有过雨了,这干渴的山梁、山路又怎么会有清新的气息呢?偶尔能看见一两株树木挺立着,它们是路两边唯一能显出绿色的东西,它们是生命的存在。它们缓缓从窗前退后,侧身望着并想着它们,我不由肃然起敬。在自己内心,其实一直有着对我们这干山枯岭的地方存活的植物的敬畏!自家小院四围那些挺立的新疆杨,青白色的叶子在风里唰啦啦响起,我感受到那是一首吟唱生命的赞歌。老家叫做簸箕湾的山谷里,那一谷的香叶草,我总觉得它们是大自然对那片山谷的恩赐,派了那么葳蕤的草木来守护装点,让山谷充满美丽并不寂寞,母亲那片蓝色的犹如海面般的胡麻花,也就在香叶草的陪伴下摇曳多姿。还有,并不风调雨顺的年月,那些山山梁梁沟沟坎坎总还是能生长出山花野草……这里的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如既往经营着自己无限热爱着的家园。
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一个乡镇。那里,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但我却没觉着它的陌生,相反,我感觉我对那里的一些东西是熟悉的,比如,水泥铺就的并不很长的街道,街道两边的店铺,店铺门口摆放的塑料用具、水桶、铁炉,戴着白帽的回族老人,骑着摩托车的小伙子打着口哨,老太太伛偻着腰,干部模样的中年人背着手缓慢走过……早听说,那个乡镇的一部分百姓将被作为移民搬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直觉告诉我,生活在那里的老年人说什么也是不愿离开故土的,就像我的爷爷奶奶,他们常说要走就让年轻人走吧,出去好闯去,自己都是快进黄土的人了,哪里也不想去了……
路过一个叫不出名字的小村,公路正好在村子头顶。有人提议下车看看,因为透过车窗我们看到统一建筑模式的院落。下了车,望向村子,果然,不大的村子是整齐划一的院落、房屋。天空蓝而高远,小小的村子显得相对寂静,但还是有生活的声息依稀传来,孩子的喊声,鸡狗的叫声,也有屋顶的炊烟袅袅,远远看见村头有几棵树冠颇大的树木。恍惚间,竟觉得那就是自己生活过的村子,郭家奶奶正拄了拐杖挪着小脚赶往村头的老榆树下,因为柳家奶奶李家奶奶张家婶子早已候在树下了,她们一边做着针线,一边家长里短的说开去;隐隐看见村小学的红旗在晚风中飘扬,隐隐看见二爷正赶了羊群进圈,隐隐听见母亲唤我回家的声音……
被别人提醒上车,好久,还未能从内心的村庄里走出来。
车子依然颠簸,师傅说快到了。果然,很快就听到了属于街市的吆喝,很快就看到了属于集市的模样。
这里的一切还在按照自己的秩序进行。留下来未必不好,搬迁也未必不好。如果内心一直保有对生活的热望,这些人到任何地方都能开拓自己的领域,就像热爱这荒芜却厚重的故土一样热爱生存的地方。
大概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我是站在小镇街道边感受着一些情景的:一个戴了头饰的回族小媳妇推了自行车过来停在街边阴凉处,她从后座上卸下一个不大的纸箱,揭开盖在上面的白布单,是大半筐紫红的桑葚,她也不吆喝,就那么悄悄站着,看着走过的人,那脸上却是带了些许期待的神情的。终于有人站在了纸箱旁,她立刻弯腰下去,用塑料勺子取了几个桑葚递给大概是准备买桑葚的人让他尝,一笔小小的买卖成交,小媳妇数着手里极少的钱,粉白的脸上笑意盈盈;从街道拐角处走来一支小小的队伍,那是放学的孩子,他们戴着红领巾,唱着歌,有一个教师吹着哨子护送着队伍;乡镇卫生院门口立了几块展板,上面张贴着常见疾病以及如何预防的内容;不知什么地方传来清真寺里的诵经声……
突然,特别想在这个地方待一阵,就像以前在乡下学校教书时住着一样,并没有给那里多做些什么,却是认真生活过一段时间。对自己而言,这个夏天,没有多少微笑盛开,内心的芜杂并着眼角的皱纹一起疯长,超出常态似的。困惑,还有因为困惑而产生的疲惫,还有无以言说的种种,相混着,裹挟着,时时带着击打而来。失望梦魇般地紧缠内心!茫茫孤独,亦如梦魇般地塞满内心!
突然想起一句话:“我们拿什么拯救别人?我们每个人都飘摇在‘风尘’之中,谁来拯救我们?”可不是,我们每个人在某些时候内心的挣扎就是在等待拯救,可是,我们拿什么拯救别人呢?每个灵魂,都有挣扎的时刻!生活不是跟我们开玩笑,它只是定睛在一旁,细瞅了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舞台上,愿意也好,沮丧也罢,只能自顾演绎。
那一日,从早晨到午后,我们走走停停,一直在路上,我不知道,同行的人内心是否和我一样,也被巨大的困惑笼罩?脚踏土地,仰望茫茫天宇,有亘古久远的感觉。我一时不能拿定主意:可不可以喊出来,存在就是困惑……
寂寞养蜂人
车窗外不时有蜜蜂飞过。果然,在车子转过一个山弯后,看到公路边空地里摆放着好多蜂箱。泛白的旧木蜂箱大概有三四十个,还有养蜂人居住的帐篷。这熟悉的场景,让我心生喜悦,赶紧下车,竟没有往昔害怕被蜜蜂蛰的胆怯。下了公路,侧走几步,靠近军绿色的帐篷,不闻人声,未见人影,面前可见的蜜蜂不是想象的那般多,它们绕着蜂箱兀自飞舞,并不曾理会我这个陌生的闯入者。轻咳一声,想换来帐内主人的招呼,却依旧是没有人声,耳畔是嘤嘤嗡嗡的声音。养蜂人正在帐内劳作还是外出不在?我不得而知。
公路两边是大片的庄稼地,正在扬花的作物飘散着浓郁的香气,还有山野间其他草木的气息,混合在一起。我站在地埂上,近乎贪婪地呼吸着醉人的香气。
一会儿,从坡地的小道上走过来一个戴着草帽的人,两只手分别提着塑料壶。我猜想他应该是养蜂人了。
等他走过来,我看清他提的塑料壶里装的是水,他抬头看我一眼,深情严肃,低沉着声音说去沟底提水了。听口音不是当地人。他进了帐篷,我跟到门口朝里望了望,地上乱糟糟的摆满东西,水桶、煤气灶、木凳、铁锹、雨鞋。从帐篷里出来,他不言语,顺手拿起一个小铁铲铲胶鞋上沾着的泥水。看他那样子并不希望被我打扰。但我还是没忍住问了一些话。我问就他一个人?他说一个人南来北去的二十多年了。他低着头闷声说话:姓安,老家在甘肃,十九岁开始养蜂。刚一开始被蜜蜂蛰,就会肿起又大又红的疙瘩,好多天奇痒难耐。慢慢就适应了,蛰的地方只是一个小小的红点,一两天就不见了。以前产的蜂蜜好卖,现在用蜂蜜加工的厂家多了,蜂蜜制品真真假假五花八门,他们生产的原始蜂蜜受到了冲击,收入并不好,但家里土地不多,再做什么生意也不容易,就只能继续养蜂,再说,已经适应了和蜜蜂相伴的生活,真的喜欢上了这小生灵。话说完了,鞋上的泥巴还没收拾干净。
车子再次环绕在山间。远山似乎是顶托着低低的云层。一面面山坡好似被大手涂抹成了五颜六色。安静的公路,转了一个弯又一个弯。想着寡言的养蜂人安,记起一个旧电影《养蜂人》,那镜头的力量,真的能让人感到深深的忧伤:养蜂人斯皮罗暮年的悲哀,回忆的疼痛,不理解的沟壑,沟通的失败,面向未来的举步维艰和永远逝去的青春……那一切,通过沉静诗意的画面徐徐展现……
我面前的养蜂人安顾不上管什么电影。他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奔波在外,供女儿上大学,儿子上中学以及其他一切家用开支都指望着他和他的蜜蜂。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山川梁峁,吸引他和蜜蜂的是那些繁密的花朵,大的小的,高的矮的,红的紫的,浓的淡的。他基本是以山野为家,几乎不看电视,不懂网络,拿的手机有时也没信号,随身有个小收音机,闲下来时偶尔听听。大多时候,他沉默着劳动,歇息时蹲下来抽烟,吐着烟圈想想留在家里的老婆,上学的孩子,想过了,继续劳作。大自然的气息包裹着他,人世的烦扰不能完全摆脱,俗世里的养蜂人安,清净又孤寂的夜晚,他心里的有些话儿向着谁诉说呢?
养蜂人,也许生来就暗藏了一颗蜜蜂的心,具有蜜蜂的灵性和浪漫,总是逐花草而居。比如安,他说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在田间地头安顿好自己和蜜蜂,就什么都不多想了,养蜂,割蜜,没有多少闲时间,辛苦而忙碌,也乐在其中。
下到山底,我向高处望去,远处的天空变成了橙色。养蜂人安此刻正享受着来自天际橙色的沐浴,看蜜蜂起起落落,飞来飞去。在天地间,他寂寞,也热闹,寂寂寞寞,热热闹闹,都交给大自然了,且由他在其间吧。
尘埃里
火车上,我邻座的中年男子,头发凌乱,衣着破旧,神情木讷。他专注于面前泡着的方便面,粗黑的双手正在撕开一袋榨菜,榨菜的红油汁液顺着手指流下来,有一滴一直流到手腕处,他也不擦一下。我掏出纸巾,是真的想递过去,但一瞬间,又没了勇气。我想到他也许会狠狠剜我一眼,以此来证明他对我的矫情的不屑一顾。我有过那样的经历,不止一次,对方不知道我内心的真实想法。那些时候,我总会想到我漂泊在外的叔叔弟弟以及更多的亲人。他们在车站,在码头,在货场,在工地,在煤矿,在所有底层打工者可以到达的场合,他们干活,流汗,有时挨饿,受冻,他们被训斥,被哄骗,有时默默流泪,有时抱头干嚎,有时身体遭遇伤害,内心更茫然。领取工钱的日子,他们高呼万岁,快乐得像孩子,干完活儿,他们呼朋唤友,在异地的小酒馆大笑,畅饮,讲段子,怀念故乡,想念亲人。
邻座的中年男子,我丝毫不厌恶他邋遢的衣着,冷漠的神情。我多想和他说句话。也许,我们有着共同的乡音。
2012年早春时节,草叶虽已冒尖,鸟鸣婉转,但西北的空气中仍有余寒,而我们经历的何止是那微微的寒意,家族老小几十口人都承受着骨肉分离的透彻心骨的严寒:我年仅四十八岁的成毅叔在瞬间与亲人们阴阳两界。被伤悲浸透的那些日日夜夜,搜索记忆,身形结实,面相俊朗,细致,寡言,坚韧,耐劳,如此简单又何其丰富的几个词,定格成为我心底的成毅叔,而他,永不会再苏醒过来,与这个世间哪怕及其微不足道的某人某事发生丝毫的对话。丧事期间,我一次次目睹年迈的四爷双膝跪地,手指苍天,嘶哑着喉咙干号,白发人送黑发人,人生暮年里这残酷的事降临,四爷被悲痛击倒,浑浊的眼里竟已流不出一半滴泪水来,我衰老的四奶身处异乡,从头至尾,被瞒着不知真相,天天嚷着心慌心急,天天抹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