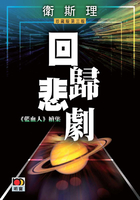曼尼·加西亚上楼,走到到堂米盖尔·雷塔纳的办公室。他放下手提箱,敲了敲门。没有人回答,但是他觉得房间里面有人。这一点,他是隔着门感觉到的。
“雷塔纳,”他一边说,一边听着。还是没有人回答。他在里面,肯定没错,曼尼想。“雷塔纳,”他提高了声音,砰砰地敲着门。“谁啊?”办公室里面有人问。“是我,曼尼。”曼尼说。“你有什么事吗?”那声音说。“我要找工作。”曼尼说。
门上有样什么东西咯咯响了几下,随后打开了。曼尼拿起手提箱走了进去。
一个小个子男人坐在房间一头的一张大办公桌后面。在他头上方的墙上,有一个公牛的头,看上面的字体,是由马德里动物标本剥制者剥制的;墙上还有几幅装在镜框里的照片和斗牛的海报。
那个小个子男人坐在那儿直勾勾地看着曼尼。
“我还以为你都被它们弄的送了命呢。”他说。曼尼用指关节敲着办公桌。小个子男人还是坐在那儿隔着办公桌看着他。“今年你斗过几次牛?”雷塔纳问。“就一次。”他回答。“就是那一次?”小个子男人问。“是的,就那么一次。”
“我在报上看到了。”雷塔纳说。他往后靠在椅背上,还是看着曼尼。曼尼抬头望了望那公牛标本。他以前经常看到它,而且他对它有着一种他们家特有的兴趣。那是大约九年以前,这条牛挑死了他的哥哥,他们几个兄弟中很有前途的那一个。曼尼还记得那一天,公牛头的盾形橡木座上镶着一块铜牌。曼尼不认识上面的字,但是他想像那准是纪念他哥哥的。嘿,没错,他真是一个好小子。
那牌子上写着:“贝拉瓜公爵的公牛‘蝴蝶’,曾九次受到马上的矛刺,于1909年4月27日挑死见习斗牛士安东尼奥·加尔西亚。”
雷塔纳看到了他在望着那公牛头的标本。“公爵给我送来的那批供星期天用的牛准会出丑。”
他说,“它们腿全都不好。对了,知道人们在咖啡馆里是怎么议论那些牛的吗?”
“我不知道,”曼尼说,“我刚到。”
“对,”雷塔纳说,“是啊,你还带着提包呢。”他一边望着曼尼,一边往那张大办公桌后面靠着。“坐下,”他说,“先把帽子脱下。”曼尼坐了下来,脱下帽子,他的脸变了样。显得苍白,而他的短辫子则从后面往前别在头顶上。这样,戴上帽子别人就看不出来他有个小辫子,而这给了他一副古怪的样子。
“你脸色可不好。”雷塔纳说。“是的,我刚从医院里出来。”曼尼说。“我听说他们把你的腿锯了。”雷塔纳说。“没有,这是谣传”曼尼说,“腿好好的。”雷塔纳在桌子那边俯身向前,把一只木制香烟盒朝曼尼推来。
“来吧,抽支烟。”他说。“谢谢。”
曼尼点了一支。“你抽烟吗?”他一边把火柴递给雷塔纳一边问。“不了,”雷塔纳摇摇手,“我从来不抽烟。”雷塔纳看着他抽烟。“你干吗不找个正式的工作,干点活儿。”他说。“我不想干活儿,”曼尼说,“你知道的,我是个斗牛士。”
“再也没有谁可以算得上斗牛士了。”雷塔纳说。
“我是个斗牛士啊。”曼尼说。“对,要知道,只有你在场上的时候才是个斗牛士。”
雷塔纳说。
曼尼笑了。雷塔纳坐着,什么也不说,只是望着曼尼。“你要是愿意的话,我把你安排在晚场,怎么样?”
雷塔纳建议。“什么时候?”曼尼问。“就明天晚上吧。”
“要知道,我可不想去给哪个斗牛士当替身。”曼尼说。他们都是那样给挑死的。萨尔瓦多就是那样死的。他用指关节叩着桌子。
“可是我只有这个了。”雷塔纳说。“你为什么不把我安排在下个星期呢?”曼尼建议。“你知道的,你卖不了座,”雷塔纳说,“人们要看的是李特里、鲁比托和拉·托雷。这些小伙子都是最棒的。”
“但是他们会来看我把牛干掉的。”曼尼满怀着希望说。
“不,人们不会来的。你太乐观了,事实上他们再也不知道你是谁了。”
“我身体还很强呢。”曼尼说。“听着,我给你安排在明天晚上,”雷塔纳说,“你可以和年轻的埃尔南德斯搭配,在查洛特以后杀两头新牛。”
“谁的新牛?”曼尼问。“我不知道。应该是他们那牛栏里的牛吧。正规的兽医在白天不会通过的那些。”
“我还是想说,我可不喜欢做人家的替身。”曼尼说。“没什么好商量的了,接受不接受,随你便,”雷塔纳说。他往前俯下身子看文件去了。看得出来,对于曼尼,他不再感兴趣。曼尼刚才的求情有些叫他动心,因为他一时回忆起了从前的日子,但是现在那种情绪消失了。他倒是想让曼尼替代拉里塔,这是由于他可以便宜地雇下他。他也可以便宜地雇下另外一些人。不过,说真的,他想帮他一下。到最后,他还是给了他这个机会。现在得由他决定了。
“给我多少?”曼尼问。他心里还是有些想拒绝接受。不过他心里知道其实是没法拒绝。
“二百五十比塞塔,”雷塔纳说,他原来考虑给五百,但是一开口却说了二百五十。
“可是你给比里亚尔塔七千呢。”曼尼说。“要知道你又不是比里亚尔塔。”雷塔纳说。“这我知道。”曼尼说。“因为他卖座,曼尼。”雷塔纳解释说。“那当然,”曼尼说,他站了起来,“那就考虑一下,给我三百吧,雷塔纳。”
“好吧,就这么定了”雷塔纳同意了。他把手伸进抽屉去拿一张纸。“那我能现在先拿五十吗?”曼尼问。
“当然可以了。”雷塔纳说。他从皮夹里掏出一张五十比塞塔的钞票来,并把它平摊在桌子上。
曼尼拿起钞票,放进口袋里。“斗牛助手你希望怎么安排?”他问。“这个不用你操心,我有那些一直在晚上给我干活儿的小伙子们。”雷塔纳说。“嗯,他们都还不错。”长矛手人手不多,雷塔纳承认。
“我可得要有一个好的长矛手才行啊,你知道的”曼尼说。
“那你去找吧,”雷塔纳说,“你去把他找来。”
“总不能从我这里出钱啊,”曼尼说,“我可不从六十个杜洛里拿出钱来付给哪个斗牛助手,这没门。”
雷塔纳没有出声,只是隔着大办公桌望着曼尼。“你知道,我一定得有一个好的长矛手,我需要那个。”曼尼说。
雷塔纳没有作声,只是远远地望着曼尼。“你知道的,这不成。”曼尼说。雷塔纳还在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他靠在椅背上,远远地凝望着他。“正式的长矛手有的是。”他说。
“我知道,”曼尼说,“我知道你那些正式的长矛手。”雷塔纳还是没有一点笑容。曼尼知道事情到此结束了。
“我只是想做到两边力量相当而已,”曼尼分辩说,“既然我要出场,那我就要求能扎中牛。只要给我一个好的长矛手就行了。”
很显然,他这是在跟一个不再听他说话的人讲话。“你要是需要额外的东西,”雷塔纳说,“那你就自己去找。我只给钱,别的我管不了。那儿外面就有一批正式的斗牛助手。你爱带多少自己的长矛手你就带多少。我不管,不过请记住,滑稽斗牛十点半结束。”
“好吧,”曼尼说,“要是你认为这样做比较好的话。”
“就这样了,回见。”雷塔纳说。“明天晚上再见。”曼尼说。“好的,我会到场的。”雷塔纳说。曼尼拿起他的手提箱,走了出去。“请把门关上。”雷塔纳喊道。曼尼回过头来看看,雷塔纳正俯身坐着在看一些文件。曼尼卡嗒一声把门带上了。他走下楼梯,出了门,来到炎热而明亮的大街上。
街上很热,照在白色建筑物上的阳光突然强烈地刺进他的眼睛。于是他沿着有阴影的一边走下陡峭的街区,径直向“太阳门”走去。屋子下面的阴影叫人觉得像流水那样纯净和凉爽。就在他穿过横街的时候,热气突然袭来。从他旁边经过的来来往往的行人有很多,曼尼没有看到一个熟人。
就在“太阳门”前面,他转身走进了一家咖啡馆。咖啡馆里静悄悄的,很少的几个人坐在靠墙的桌子边。有四个人正在一张桌子上玩牌。绝大多数人背靠墙坐在那儿吸烟,而他们前面的桌子上,放着一堆空空的咖啡杯和玻璃酒杯。曼尼穿过这间长长的房间,走进后面的一间小房间。他看到有一个人坐在角落里的一张桌子跟前睡着了,于是曼尼在其中一张桌子边坐下。一个侍应生走了进来,站在曼尼的桌边。“你看到过舒力图吗?”曼尼问他。“是的,吃午饭前他来过,”侍应生回答,“但是他五点以前不会回来。”
“那好吧,给我一点咖啡和牛奶,再来一杯普通的酒。”曼尼说。
侍应生回到这间屋里,端来一个托盘,上面放着一只大的玻璃咖啡杯和一只较小的玻璃酒杯。他左手拿着一瓶白兰地。然后胳臂一转,就把这些东西都放到了桌上。在他后面跟着一个孩子。他从两个亮闪闪的长把壶里把咖啡和牛奶倒进玻璃杯。
曼尼脱下小帽,侍应生注意到了他那向前别在头上的小辫子。他一边把白兰地酒倒进曼尼的咖啡旁边的小玻璃杯里,一边朝送咖啡的孩子顽皮地眨了眨眼。那个送咖啡的孩子好奇地望着曼尼的苍白的脸。
“您在这儿斗牛?”侍应生问,一面盖上瓶塞。“是啊,”曼尼说,“就是明天。”侍应生站在那儿,把手握起靠在大腿上。“您在查理·卓别林班里吗?”他问。送咖啡的孩子觉得很窘,直往别处看着。“不,在普通班里。”
“我还以为,他们安排恰维斯和埃尔南德斯搭配呢。”
侍应生说。
“不。和他们无关,我是跟另外一个人。”
“谁?恰维斯还是埃尔南德斯?”
“我想应该是埃尔南德斯。”
“那恰维斯怎么啦?”
“他受伤了。”
“你打哪儿听到的?”
“雷塔纳。”
“嗨,路易埃,”侍应生向隔壁房间喊道,“恰维斯让牛挑了。”
曼尼撕了包装纸,把方糖放进咖啡里,然后搅动了一下,把咖啡喝了。这咖啡又甜又热,让他的空空的肚子觉得暖暖的。他一口气喝光了白兰地。“再给我来一杯好吗?”他对侍应生说。侍应生斟了满满一玻璃杯,溢到茶托里的也有一杯那么多。这个时候,另一个侍应生来到桌子跟前。送咖啡的孩子已经走开了。
“请问恰维斯伤得厉害吗?”第二个侍应生问曼尼。“我不清楚,”曼尼说,“这个雷塔纳没说起。”
“他怎么管那么多啊,”一个高个儿的侍应生说。曼尼以前没有看见过他,他准是刚走过来。“在这个城里你要是搭上了雷塔纳的关系,那你可真就走运了,”高个儿侍应生说,“你要是搭不上他的关系,我想啊,那你还不如走出去自杀吧。”
“你说对了,”又走进来的一个侍应生说,“你真是说对了。”
“不错,我是说对了,”高个儿侍应生说,“说到那个家伙啊,谁都知道我并没在胡扯。”
“瞧瞧他是怎么对待比里亚尔塔的。”第一个侍应生说。
“事情还不止如此呢,”那高个儿侍应生说,“再瞧瞧他怎么对待马西亚尔·拉朗达的,瞧他怎么对待纳西翁那尔的。”
“嗯,你说对了,孩子。”矮个儿侍应生表示同意。曼尼看着他们站在他桌子跟前议论。他喝完第二杯白兰地。他们把他忘了。他们对他并不感兴趣,这很正常。“瞧瞧那一帮子笨蛋,”高个儿侍应生接着往下说,“你见到过这个纳西翁那尔第二吗?”
“我们在上星期天见过他吗?”第一个侍应生说。“嗯,他是条长颈鹿。”那矮个儿侍应生说。“我怎么跟你说来着?”高个儿侍应生说,“那些人都是雷塔纳手下的。”
“喂,再给我来一杯好吗?”曼尼说。在他们谈话的时候,他已经把侍应生溢到茶托里的酒倒进玻璃杯里给喝完了。
于是那第一个侍应生机械地给他倒了满满一杯酒,三个人就边谈边走出屋子。
在远远的屋角里的那个人还在睡觉,他吸气的时候发出轻轻的鼾声,这和他的头仰靠在墙上不无关系。
曼尼喝了白兰地,自己也觉得瞌睡了。但是这会儿走出去到城里,天太热了。再说,又没有什么事可干。他想去看望舒力图。他想,就趁等着的时候睡一会儿吧。于是他踢了踢他的手提箱,用来确定它确实还在桌肚里。兴许把它放在靠墙的座位底下更安全些吧。于是他俯下身子把手提箱推到座位底下,然后他伏在桌子上睡觉了。
一觉醒来的时候,他看到有一个人坐在他桌子对面。那是一个大个儿,深棕色的脸,活像一个印第安人。看样子他已经在那儿坐了一些时候了。他挥手叫侍应生走开,坐着在看报纸,还时不时地低头望望正把头搁在桌子上睡觉的曼尼。他看报很认真,一边看,还一边动着嘴唇念出字来。看累了,他就望望曼尼。曼尼沉沉地坐在椅子里,他的科尔多瓦帽子歪向前面。
曼尼坐了起来,看着他。“你好,舒力图。”他说。“你好,老弟。”那个大个儿说。“不好意思,我睡着了。”曼尼用拳头的背面擦了擦前额。
“嗯,我也觉得你是睡着了。”
“怎么样,你过得好吗?”
“还不错。你过得怎么样?”
“不太好。”
两人都沉默了。长矛手舒力图打量了一下曼尼那张苍白的脸。曼尼看着那长矛手用他那双大手把报纸对折起来,塞进他的口袋里。
“说真的,我有件事要请你帮忙,铁手。”曼尼说。“铁手”是舒力图的外号。他没有一次听到这个外号不想到他的那双大手,他不好意思地把双手放到了桌子上。
“咱俩喝一杯吧。”他说。“当然。”曼尼说。
侍应生进进出出好几回。他走出屋子,回过头来看看这两个坐在桌子边的人。“怎么回事,说来听听,曼尼?”
舒力图放下他的玻璃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