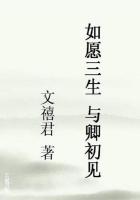我被情况逼迫着急于逃走,却惶惶不知逃向哪个地方,或者说,我该去哪个地方或港口。我那合作伙伴尽管一开始时还忧心忡忡,但现在见我垂头丧气的样子,却过来为我打气壮胆。向我描述了一番那一带沿岸的几个港口,说是他准备到交趾支那(交趾支那指的是今天越南南方、靖公河的下游一带;它的北方和西北方是柬埔寨,东北方是安南(越南中部)或东京湾的那一带海岸,然后打算去澳门,从那儿取道中国。葡萄牙一度占领了澳门那个城市,到现在还有许多欧洲人的家庭,特别是有许多传教士住在那儿。
于是我们决定去那儿;就这样,经历了一番超乎想象的劳累,一路上缺水少食的航程,终于在一个清晨,我们能远眺见海岸;考虑到我们已有的经验,考虑到如果我们无法逃出而必然面临的危险,我们决定先驶进一条水深充分的小河,然后要么上岸,要么进一步派出大舢板,想办法打听附近港口里有哪些船只。真是谢天谢地,这一举措解救了我们众人;由于我们当时虽在东京湾没看见一艘欧洲船只,但第二天上午就有两只荷兰船进入湾中;尽管第三只船没打出任何旗号,但我们依然相信它是只荷兰船,它在距我们六海里左右的地方驶向中国海岸;到了下午又有两只英国船驶过,走的是同一条航线;在此情况下,两面受敌的感觉袭击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现在处在一片蛮荒之地——那里的人偷盗成风,甚至以此为业,尽管我们事实上对他们别无多求,除了要补充一些食物以外,也不想多与他们打交道,但也大费力气才使自己免遭他们的种种骚扰和攻击。
我们呆在离这国家的北部边界不到几英里之遥的一条小河里;我们乘上小船沿着河岸向东北方航行,来到濒临浩渺的东京湾的一处地呷,而正当我们沿着河岸艰难地溯流而上时,我们发现自己周围布满敌人。那些困住我们的人,是这一带沿岸居民中最野蛮的人,他们不同于其他任何民族,用来交易的只有鱼和油,以及诸如此类的初级产品,而更为令人瞩目的是他们的野蛮,这在一切居民中是屈指可数的。在他们的种种奇风异俗中尚有这么一条:如果有船在他们的海岸出事了,不管是什么船,船上的人马上被他们抓去做俘虏和奴隶;我们随后也经历了一件事,从中目睹了他们的这种“宽宏大量”,请听下文分解。
在上文我曾说过,我们的船在海上曾漏水,直到最后还找不到漏水的地方;我也说过,幸亏我们运气好,在接近退罗湾的北方,我们这船在将要被荷兰船和英国船逮住的时候,却又出乎意料地突然不漏水了;然而,既然我们已发现这船已不像我们希望中的那样漏不进一滴水,再不是完好无损,我们就决定找机会把船弄上岸,把船上的重物卸下来,清理一下船底,尽可能找出漏洞在哪儿。
于是我们减轻了船上的荷重,把全部大炮和其他一切可移动的什物都搬到一侧,试图令它向一侧侧倒,这样便可以修船了,但转念一想,我们就不想把船弄上陆地了,另外,想这么做也找不到适当的地点。
对这种场面,当地的居民见所未见,他们好奇地走下岸来望着我们;但看到一艘船侧倒在一边,倾倒在岸上,而我们的人又一个不见,由于他们要么是乘着舢板在船的外例修补船底,要么是在搭着的脚手架上工作;当地的土著人当时就以为这是只被遗弃的船只,现在在陆地上搁浅了。
他们抱着这种想法,聚了一大帮人,乘着十一二条大划子,每条划子上要么是十个人,要么是八个人,两三个小时后便全都集到我们的船的附近,看那架式无疑是想上船来劫掠一番;万一上船后发现了我们,就带回我们当作奴隶送给他们国王什么的——我们对他们的统治者一无所知,不知道称呼他什么。
他们划到我们的船前,便在周围划来划去,发现我们正卖力地在船舷和船底的外侧做工,有的在重新刷上涂料,有的在于清洗工作,有的在堵漏,这些可都是每个航海人的拿手好戏。他们暂停了一刻,凝视着我们,而我们也十分惊诧,却猜不出他们的真正意图;但为了保险起见,我们让一些人趁机进入船舱,又让另一些人递给其他在干活的人武器和弹药,以防万一之时用来自我防卫;然而,它的必要性随即便显现出来了——由于他们商议了不过刻把钟,似乎已取得共识,确认这确是一条海上遇难的船,而全体的我们在努力干活只是想让这只船起死回生,要不然我们的选择就是乘我们的舢板逃命;他们看到我们把武器递进舢板,竟然把这种动作想象成我们正在拼命地抢救货物;于是,他们认为我们全归他们是自然不过、理所应当的事,然后似乎以某种队形直冲向我们的人。
我们的人看见敌众我寡,不由得惧怕起来,由于我们的处境不利于作战,于是他们大声朝我们喊叫,取得上层人物的对策。我连忙喊那些站在脚手架上干活的人,要他们赶紧下来,从船舷马上爬进船来,同时还命令舢板上的那些人,让他们尽快划着绕过来,赶紧登上大船;而尚呆在船上的几个人则全力以赴,召集一切人员努力把船位恢复正常;然而,无论是舢板上的人,还是脚手架上的人,面对来犯的交趾支那人,都没能执行我的命令;现在,主人的两条划子已经靠上了我们的大艇,我们的人已开始被他们当俘虏逮住了。
英国水手是第一个被他们抓到的人,他长得孔武有力,手中握着一支枪却并不射击,反倒把它往艇上一放——我当时就想,他是个十足的蠢货;然而他对于他要干的事,知道得比我清楚多了。用不着我的废话教他,只见他伸手揪住那个异教徒,稍一用劲就把他从他们的划子上换到我们的大艇上,拉住他的两只耳朵,把他的头往船舷上尽力一撞,那家伙便一命呜呼了;与此同时,旁边的那个荷兰人拾起那杆火枪,抡起枪柄向四周乱打一气,五个想要登上大艇的人便被击翻到海中了。然而那三四个人并不因他们干的这点事而惧怕后退,他们也不盘算一下自己眼前的危险,壮着胆子,竟开始扑进大艇;我们只有五个人留守在大艇上,但随即发生的一件乐事,使我们笑破了肚皮,也令我们这一方大获全胜。
我们的木匠用麻絮堵好了漏洞,准备用热沥青一类填好裂缝,并在船外加涂一层,恰恰让大船上的人把两口大锅吊到大艇上,一口锅里满是动物油脂、天然树脂和油料,另一口锅里装满了沸腾的沥青,反正是船上的木匠干此类活计时必不可少的东西;给木匠打下手的人拿着一个大铁勺,大家干活时如果要用那滚烫的东西,他便舀上一勺子给他们;他当时站在大艇的艄座处;恰好两个对方的倒霉的家伙来到这地方,他当机立断把这样一勺滚烫的混合物朝他们迎头浇去,这两个半裸着身子的可怜人,烫得一下子牛叫似的大吼起来,结果他们难忍剧烫,都跳进了海水中,木匠见此情形,高兴地大叫道:“干得棒,杰克!再给他们来几下子!”说着,他上前几步,拿起一只拖把住沥青锅里一浸,和他的手下一起朝那些人的头上乱撒沥青,结果那三条划子里的人没有一个漏网,全都被烫得焦头烂额,狼狈不堪,发出我从未听过的凄厉嚎叫声;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所有的人都会对痛楚产生自然而然的叫声,然而每一个民族的叫嚷都有其独特之处,正如语言的不同,他们的叫嚷声也不同。我无法给予这些家伙发出的叫声以更为贴切和准确的名字,只能借用嚎叫一词;由于在我听到过的所有声音中,只有他们的叫声最无愧于最像粮群的曝叫的桂冠,而前文我也提及,我在朗格多克〔朗格多克为法国南部一省旧名〕边界处的森林中有幸听过这种狼嗥声。
在我的一生中,我对这次胜利最为满意,由于这对我来说,在迫在眉睫的危险面前,我们不仅取得了超乎想像的巨大胜利,而且我们几乎兵不血刃地就取得了战斗的胜利,我们那英国伦赤手空拳地杀死了一个人是唯一的例外;我心中对这件事感到非常不安,由于哪怕是出于自卫目的,我也对于杀戮了这种尚处于未开化地带的可怜家伙感到万分痛心,由于我深知,他们从来认为干这种事非常正当,而他们的认识水平也仅限于此;而我们的做法既出于必要的目的(由于在自然界,决没有无缘无故的邪恶罪行),当然也可能是正当的,然而如果我们总是以杀死自己的同类为代价来保全自己,我眼中这种人真是再可悲不过了;说实话,我至今仍抱这种想法,而且,至今我甚至自己宁可吃大苦头,也不愿对伤害我的人下毒手,哪怕他是个十恶不赦的家伙;至今我还深信不疑,任何有点脑子的人,只要认真地思索一下这个问题,只要知道生命的价值,就一定不会反对我的想法的。
但我还是言归正传吧。上面发生的那件事期间,我的合作伙伴和我指挥着大船上的众人,很是得心应手地把船位基本恢复了正常,然后炮手把全部的炮安装在原来的炮位后,就让我下命令,让我们那大艇退出中间的地带,由于他想朝那帮土著人开炮了。我喊话叫那炮手别开炮,由于无需他动手,木匠就能把事情摆平的;同时我也命令他烧开另一锅沥青,而起初,各司其职的却是那正呆在船上的厨师。我们挫败了敌人的第一轮进攻,惨败的他们肝胆尽碎,一百个胆子也不敢重新进攻;他们其中的几个家伙远远地在一旁瞧着,我们这大船已渐渐平衡地浮在水面上,依我们看来,他们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看到事情比他们想象中的要复杂,便无奈地最终放弃了这种冒险行径。不过如此,一场闹剧似的战斗已经结束;于是我们在买了一些米,一些薯类和面包之后(加上两天前已装在船上的十六头猪),决心离开这里,不管什么事发生,也毫不迟疑地继续前进,由于我们毫不怀疑,第二天就会有人数更多的坏家伙包围住我们,到那时他们就不会简单地就被我们的沥青锅子打发走的。
于是当天晚上我们把全部的杂物都收拾上船,到第二天早上已准备停当,只等出航了。当时我们在离岸尚有一段距离的地方下锚停泊,这样,万一有什么敌人出现,我们既可以马上出航,也可以马上作战,因此不足挂虑。第二天,我们干好了船上的一切活计,发现我们的船已经完全修好,不漏一滴水,便起帆出航了。我们本想驶进东京湾,了解一下有什么关于先前到达那里的那只荷兰船的情况,然而我们没敢这么做,由于不久以前我们已经看见了一路驶过的好几条船;于是我们掉头向东北,驶向台湾岛;就像在地中海里,一只荷兰或英国的商船害怕被阿尔及利亚的战船看到,我们也害怕被荷兰或英国的商船发现。
我们就取向东北方,好像我们要去马尼拉或菲律宾群岛;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碰上任何一条欧洲船;然后我们航向朝北,来到了北纬二十二度三十分的地点,我们由那里直驶台湾岛,并下了锚来补充淡水和新鲜食物;当地的人非常殷勤有礼,高兴为我们提供这些物品,而且他们在与我们商议交易时,办事公道,交货准时;这是我们在其他处民众中不曾遇到过的,由于荷兰新教徒曾在这里传过教,因此也可归因于基督教的遗风;从另一面讲,这情况也证实我常常不离口的一句话,也就是:什么地方接受了基督教,那里的人就会变得文明,那里的民风也会得到改进,教义是否对他们起到了救校的效果暂且不论。
我们由那里直驶向北方,始终同中国的海岸保持一定的距离,直到我们确信自己已越过了欧洲船只来往频繁的一切中国港口,由于我们决心尽一切努力决不在这国家里落入敌人之手,我们的情况显示,要是在这儿发生什么意外,那我们就彻底完蛋了。
现在船已驶到了北纬三十度,我们决定,遇见第一个商埠就毫不犹豫地进去,当我们驶向陆地之时一只走了六海里的路程的小船来到我们的船前;船上载着的那位葡萄牙领航员知道我们是条欧洲船,就前来问我们需不需要他领航;我们自然万分乐意,马上请他上船;他刚听到之后,也不问我们的目的地,便离开他所乘坐的小船,打发它返回了。
如今,我认为我们可选择的余地很大,可以请这位老汉领我们前去任何想去的地方。于是我告诉他,请他领我们去中国海岸最北部的南京湾。老汉说他对南京湾轻车熟路,却微笑着询问我们前去的目的。
我就告诉他说,我们要把船上的货物卖掉再购进一些中国瓷器、生丝、茶叶、白棉布、丝织品诸如此类,然后循原路返回。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到澳门去,那是我们的最佳选择,我们的鸦片一定可以在那里卖上一个好价钱,然后用卖得的钱购进各种各样的中国货,当然价钱一点也不比在南京湾贵上哪怕是一点点。
我看这老汉说话自以为是,刚愎自用,也没法闭住他说话的嘴,于是我就告诉他说,我们即身为商人,不是没身分没修养的人,十分渴望去瞧一瞧北京这个偌大的都市,去见识一下中国皇帝的著名宫殿。“那么,”那老汉说道,“宁波是你们该去的地方,到了那儿,循着一条通到大海的内河驶上十五英里,便可以汇入大运河,这条可以通航的运河,一直贯穿辽阔的中华帝国的心脏地带,贯穿所有的河流,通过一些水网和闭门便可超过一些蔚为奇观的山丘,一直流到北方的北京城,全长将近八百一十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