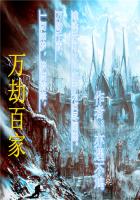我应当告诉你我丈夫把他所有的款子,一百零八个金镑,我前面已经说过,那些都是现金,带在身边,都交给她,去购买这项家伙,此外我还给她一大笔款;所以我并没有损伤到我留在她手里的那一项款子,而且我们购买了全部货物之后,我们还有将近二百金镑的现金,那于我们已经很够了。
在这种情形下,很高兴,看到我们这么有幸她受良好的看待,心里的确很快乐,我们就从布格拜洞扬帆向格来维森得去,在那里船又停了十天,船主就最末一次上船了。在这里船主给我们这么一种礼貌,那真是我们所预料不出的,就是请,他让我们上岸,去换一换空气,只要我们郑重地宣言我们不会离开,一定将平安地再回到船上。这如是表现出他对于我们的信任,我的丈夫不胜感激,他出于感恩之情,向他说道,他既不能如何报答这么大的恩惠,所以他不能接受它,而且他于心不安,船主为着他冒这么大的危险。彼此互相礼让一会儿之后,我给我丈夫一个钱袋,里面有八十金币,他就将它放船主手里。“这里,船主,是我们的忠实的一部分保证金:若使我们在任何方面对你不忠实,这就是你的了。”这样交涉之后,我们上岸去。
那位船主的确十分相信我们去的决心,因为既然这样子预备好在那边垦殖的工具,那真是不合理的,我们会愿意冒生命危险,在这里滞着,因为假使我们被抓住,我们是免不了一死的。总之,我们大家和船主同到岸上去,在格来维森得一起用餐,在那里我们非常高兴,住整夜,就宿在我们用餐的那家店里,第二早很老实地和他同上船来。在这里我们买了十打好啤酒,别种的酒,鸡鸭,同其他我们想在船上用得着的东西。
我的保姆这些时候都是同我们在一块儿,和我们一同转到丹兹,船主太太也是这样,她就跟她一起回去。我和我母亲分手还从没有和她分手这么悲哀,我后来再也没有看到她了。我们抵丹兹后三天来了一阵好东风,我们于四月十四号从那里扬帆。我们再也不靠近那个海岸,一直等到在爱尔兰海滨被一阵凶猛的狂风赶着,我们在一个小海湾里抛锚,近一条河的口,那条河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但是他们说这条河是从里摩黎克流下的,是爱尔兰最大的河。
在这里,被不好的天气耽搁了一些时候,船主,他还是像起先那样一个仁慈可亲的人,又带我们上岸去。他现在的确是为着对于我丈夫的好意而这样干,因为我丈夫很不能经风波之苦,人很不舒服,尤其当刮那么大的风时候。这里我们又买了许多新鲜的食料,尤其牛肉,猪肉,羊肉,同鸡鸭,船主等着腌好五六桶牛肉,来增加我们船中食料的贮藏。我们在这里还没有过五天,天气转温和了,来了一阵好风,我们又扬帆,四十二天之后安抵维基尼亚的海岸了。
当我们快近海岸时候,船主叫我去同他谈谈,对我说从我的说话里他看出我有几个亲戚在这地方,同我曾经到这里过,所以他想我知道他们处置流犯的办法,当运到时候。我告诉他我不知道,至于在那地方我所有的亲戚,他可以相信我不去认他们,当我是居于流犯的情形里面时候,至于其他,我们完全让他来帮助我们,因为他慨然答应过我们。他对我说,我必得找到本地的人来买我们做仆人这个人,将向都督负责,若使他问及我们。我告诉他我们将照他所指导的干去;他于是带一个垦荒者来和他谈论购买这两个仆人。我的丈夫和我,在那里我们正式地卖给他,和他一起上岸。船主和我们一同走,带我们到一家店里,到底是不是叫做酒店,我不知道,但是我在那里喝一大杯五味酒,那是用红酒等做的,我们大家都很喜欢。过了一会儿,那垦荒者给我们一张释放的执照,声明我们诚实地伺候过他,第二早我们已是自由人了,随便到我们爱去的任何地方。
为着替我们干了这件事,船主要我们买六千磅烟草给他,他说他应当缴这么多给雇船运货的人,我们立刻买赠他,此外还送他二十个金币,他就觉得非常满意了。
有好几种理由使我不宜于在这里详细说出我们住在殖民地的那一部分;就讲底下这么多已经够了,我们走进大河颇陀马克,我们的船也是向那里驶的;我们起先打算住在那里,虽然后来我们的心又变了。
当我把我们一切货物运上岸,搁在货栈或者栈房,我们租了这间栈房连同一所屋子,在我们登岸的那个村里之后,我所做的第一件要紧事情是去打听我母亲同我兄弟(我认为丈夫的那个不幸的人,我前面已经详细说过了)的消息。稍稍一探问就使我知道,某某太太,我的母亲,是死了;我的兄弟(也可以说我的丈夫)是还活着,我自认我听着并不十分高兴;但是更坏的是,我听说他迁出他从前所住我同他一起过活的那块垦殖地,却同他的一个儿子住在我们上岸,租一间货栈的那个地方邻近的一块垦殖地里。
开头我有一点儿惊惶,但是我既然大胆地相信他不认得我了,我不单是十分放心,而且很想去看他一下,那是说若使能够看见他而不被他瞧见的话。为着要干这件事,我探询出他住在那个垦殖地,就同一个本地的女人,我雇她来帮忙,像我们所谓女轿夫,向那个地方漫游,好像我只是想看看那地方的情形。四处观察了一下,最后我走得那么近,我看见他的住屋了。我问那女人这是谁的田地;她说这是属于某一位绅士的;稍微向右边望着,她说道:“那就是这田地的主人,他父亲同他在一起。”“他们的名字是什么?”我说。“我不知道,”她说,“那个老绅士的名字是什么,但是他儿子的名字是汉符理;我相信他父亲的名字也是这个。”你们若使有本领,一定可以猜出,此时我的思想是被快乐和恐惧模糊一片占住了,因为我立刻知道这人不是别个,就是我跟她所指出的那个父亲,我的兄弟,亲生下的儿子。我没有戴了面具,但是我把头巾这么绉褶着遮住我的脸孔,我相信隔了二十多年,而且绝没有料到我会来这一部分的世界,他一定不能够还认得我了。但是我用不着费这么多心机,因为这位老绅士患了目疾,瞧东西已经不大清晰了,刚能够走着没有碰树或跌到沟里。同我在一起那个女人偶然把这件事告诉我,一点儿也不晓得这对于我是多么重要的。当他们走近我们时,我说:“他知道你吗,奥文太太(他们都这样称呼她)?”“知道,”她说,“若使他听到我说话,他知道是我;但是他看不清我同任何人。”于是她向我说出他眼睛的情形,像我前面所说的。这使我觉得安全,我把头巾掀开,让他们从我身边走过。那是一件刺心的事情,一个母亲这样看到她自己的儿子,一个在良好环境里的风姿潇洒、和蔼可亲的少年绅士,却不敢向他自白,不敢对他招呼。让念这本书的任何有了孩子的母亲想一想这种情形,再想一下我是多么痛心地遏制住自己;我灵魂里多么切望拥抱着他,俯在他身上哭一哭;当时我真是想我的肚肠颠倒了,我的脏腑动摇了,我不知道如何是好,正如我现在不知道怎样表现出那些苦痛!当他走过后,我站着痴痴地望着,浑身发抖,老是望着他,一直等到看不见了;然后坐在草地上,刚刚是我看他踏过的地方,我好像只是坐下休息一下,但是我背转过来,脸向地面,哭着,吻他的脚踏过的土地。
我不能如是对那个女人隐起我的心乱,她看出来了,以为我的身体不适,我也不得不假说她猜的是对的;她就劝我起来,因为草地是潮湿同危险,我照她的话办,和她同走开。
我在回去的途中,还谈着这位绅士和他的儿子时候,来了一个悲哀的新机会。这个女人好像要讲一桩有趣的故事来替我解闷,开始对我说道:“这位绅士从前住的地方的邻人相传有一个很奇怪的故事。”“什么?”我说。“啊哈,”她说,“当这位老绅士是个青年的时候,到英国去,同那么一个年轻姑娘发生爱情,一个罕见的艳代美人,他娶她了,带到这儿,和他母亲同住,她那时候还活着。他和这位太太在这里住了几年,她继续说道,跟她生几个孩子,今天同他在一起那位少年绅士就是中间的一个;但是不久之后,那个老太太,他的母亲,对她谈起自己从前在英国时候的情形,和那时的境遇,那都是够坏的,那个媳妇开始很惊愕,很不安;总之,再仔细考察一下,知道那是绝无法否认的,这位老太太是她自己的母亲,所以那个儿子是他妻子的亲兄弟,这使全家都突然感到惶恐,把他们弄得这么混乱,几乎将他们都毁了。那个年轻的女人不肯和他同住;那个儿子,她的兄弟同丈夫,暂时疯了;最后那个年轻的女人到英国去,人们再没有听到她的消息了。”
那是容易的事,去相信我听到这个故事深为感动,但是我的烦闷真是言语所不能形容。我好像听到觉得惊奇,问她成千的问题,关于里面的细节,我看出她都知道得极清楚。最后,我开始问那家人的情形,那位老太太,指我的母亲,怎样死去,她怎样分配她的遗产;因为我母亲曾经很郑重地向我约好,当她死时候,她将替我干一些事情,把财产的一部分这样子保留下来,若使我还活着,我总能够得到,安排得使她的儿子,我的兄弟同丈夫,无法作梗。她说她不十分精确地知道这是如何分派,但是她听人说过,我母亲留下一笔款子,指定她的田地来付这项款,给她的女儿,假使听到她的消息,在英国,或者其他地方;这个责任就托在这个孙子身上,就是我们看见和他父亲一起的那个人。这个消息太好了,不容我忽视过去,你们可以相信,把我的心装上成千的念头,想到我将走哪条路,怎样,何时,同怎么样子我将露出我的真相,以及我把不把自己的真相露出。
这是一个我真没有本领去对付的难题,我也不晓得怎么办才好。整天整夜这些念头沉重地压着我的心上。我既不能睡觉,也没有心情谈话,所以我丈夫看出来了,纳罕什么叫我这样不舒服,努力来使我开心,但是都没有效力。他迫着要我告诉他什么使我难受,我用话敷衍了,等到最后因为他不断地向我噜嗦,我迫得虚做出一段话来,可是里面有实在的事情做根基。我告诉他,我心里难受,因为我看我们必定要迁个地方,改变我们垦荒的计划,因为我恐怕我将被人们知道了,若使我滞在这个地方,我母亲死后,有几个亲戚来到我们此刻住的地方,我不是迁居,就免不了被他们知道,当我们处在目下这种境况,这在许多面都是不便的,到底是怎么样办我不知道,就是这个使我这么沉闷,这么愁思着。
他赞成我的话,认为在我们那时所处的情形之下我是绝不宜于被任何人瞧破;所以他告诉我他愿意迁移到这个国境里的任何地方,或者甚至于任何其他国境,全凭着我的意思。但是现在我有另一个困难,那是,若使我搬到任一个其他殖民地,我总是隔得太远,不能好好地去探询我母亲剩下给我有什么财产。我又不能将我从前结婚里面的秘密向我新的丈夫道破,简直连这个念头我都不敢怀;我想,这是一个不堪讲的故事,我也预料不出会有什么结果;但是要去寻根追底地打听我母亲给我的遗产,又免不了弄得那地方的人民都知道我是谁,和我目下的境遇。
在这个烦恼里我继续了许久时间,这使我的丈夫很感不安:因为他看出我心里烦恼着,但是暗想我对他不坦白,没有让他知道我一切的忧愁。他常常说,他真不知道他干了什么,叫我不敢把心绪告诉他,若使是令我伤心同难过的事情,尤其应当向他说出。实在说起来,他真该受我一切的信托,因为世上没有一个人比他更值得一个妻子的亲爱;但是这件事我真不晓得向他怎样提起,然而没有人可以相告这件事的任何部分,这个重压是我的心儿所不能胜的;因为不管人们随口怎样说我们女性不能守秘密,我的一生显明地证明给我看这话是不对的;但是无论是我们女性,或者男性,一个重要的秘密总该有一个推心置腹的人,一个密友,对着他我们可以说出这秘密的欣欢,或者愁闷,不管是喜是悲,否则那将变成双倍的愁苦压在心头,也许甚至于变为不能忍受的;这句话的真实我诉诸全人类的经验。
也就是出于这种原因,常常有男人同女人,甚至于在别方面具有最伟大同最良好的性质的男人,发现出自己在这一方面却很无能,不能够独自忍受一种私下的快乐或者私下的悲哀的重压,却迫得向人说出,甚至于只为着替自己发泄一下,使那个给这件事的重量压得难受的心儿可以松活一下。这也绝不是愚蠢和糊涂的表现;这班人们,若使再挣扎着来制住这个需要,一定会在梦中说出,把秘密全漏泄了,不管是多么危险性质的,也没有顾到会被谁听见了。这种天生的必然有时在那班犯了什么穷凶极恶的罪的人们,尤其暗地里杀了人的凶手的心里这么剧烈地活动着,他们迫得不能不向人道破,虽然那结果必定是他们自己的毁灭。那固然也是真的,天理昭昭,叫他们不能逃出法网,但是上帝常常利用自然的能力,在这里也是靠着天生的冲动来产生这些奇异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