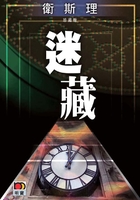那真是几乎不能想象的,人性能够堕落到以至于从本身是最悲惨不过的情形里居然感到快乐同舒适。我想天下不能找出比这个更坏的境遇了:凡是像我这样有生命,健康同金钱帮着的人们不会处在更苦痛的地位了。
我有一个重负压着我,那足够使任何人沉下去,凡是他还具有一点反省的能力,同对于这生的快乐和他生的苦痛尚剩有些微的感觉;我起先的确有反悔,但并不是忏悔;现在我是连反悔都没有了。我挨一个罪名,那个罪的责罚照我们法律说起来是处死刑;证据是这么确凿,我简直没有辩护无罪的余地。我又背上积案重重的犯人这个名义,所以我不能期待有别的,除开了在几星期内处死,我也绝没有脱逃这个想头;然而一种奇怪的心灵麻木占住我。我心上没有烦恼,没有恐惧,没有悲哀,开头一下的惊奇已经过去了;我很可以说我是自己也莫名其妙了;我的感觉,我的理性,甚至,我的良心,都沉睡了;我四十年来的生活是一大堆可怕的作恶,****、通奸,乱偷,扯谎同偷窃;总而言之,从十八岁左右一直到六十岁,除开了杀人同谋反外,什么事我都干了;现在我是沉在责罚的苦痛的深渊里,一个丢脸的死法正在门外等候着我,然而我并不感觉到我的情形,没有想到天堂同地狱,除开了一下子就过去了的瞬时感触,那好像针刺,只给一点暗示,就消失了。我既没有心去求上帝的慈悲,的确也没有想到这一点。在这几句话里,我想,我说出了地上最完全的苦痛了。我一切的恐慌都过去了,那地方的可怖现象变成熟识了,我对于狱里一切喧哗吵闹正同做这类声音的人们同样地没有感到不安;总而言之,我变成一个新门的老犯,坏恶无耻得像他们里面的任何人;不,我连一向谈话时所带有的良好礼貌同态度这些习惯都失掉了;堕落是这样子把我占住,我已不是我一向那样子的人了,好像我除开现在这种态度外,绝未曾具有别的态度过。
在我生命里这段良心麻木的时期之中,我碰到另一次出乎意料的事情,那使我尝到一些悲哀,这的确是我起先已经失掉感觉的东西了。一天晚上她们告诉我前晚上深夜时候带来狱里三个强盗,他们在到温德琐尔去的路上某地方犯了抢案;我想是韩思洛·希斯,被乡下人追到亚克斯不力诸,在勇敢地抵抗之后被擒了,我记不起来那时有多少乡下人受伤,有几个死了。
那是用不着奇怪的,我们这班囚犯都很想看一看这班勇敢优秀的先生们,据说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尤其是因为听说早上他们将移到前面院子去,他们拿钱给监狱看守长,所以得到许可享用监狱里较好的所在。于是我们这班女人都站在路头,为的是一定会看见他们;但是我的惊骇是无物可以形容的,当我看见第一个走出来的男人就是我在朗加斯德尔时的丈夫,就是在但斯塔不鲁那么阔绰地过活,后来我在布拉克喜鲁瞧见,当我嫁给我最后一个丈夫时候,这些事在上文都已经述过了。
一见到这个人,我惊骇得说不话来,既不知说什么好,也不知道干什么好;他却不认得我,这是我此刻所有唯一的安慰。我离开同伴。退到那可怕的地方所能给人的隐避所在,我猛烈地哭了许久。“我是个多么可怕的东西呀”,我说,“我害了多少可怜的人受苦?我送了多么绝望的不幸人到魔鬼那里去?”这位先生的灾难我算作全是我的过失。在支斯得尔时候他告诉过我他是被这段婚姻弄毁了,为着我的缘故他弄成绝望了;因为心里想我拥有巨资,他借了他绝无能力还偿的债,他现在不知走哪一条路好;他想从军去,背一把枪,或者买一匹马,****所谓巡游的生涯;虽然我绝没有告诉他我是一个大财主,所以实在没有骗他,但是我设法使人们想我是个大财主,因此我做了他一切不幸的根源。
这件出乎意料的事情比我所遭遇的任何事也更深地打到我思想里,使我发出更强度的忏悔。我整天整夜为他痛心,我更加痛心,当她们对我说他是那一帮领袖,他犯了这么多的抢案,汉底,飞直利,金农夫这班大盗拿来跟他一比都只好算作傻子了:
他总得上绞台,就说他的母国里所有男人全死干净了;有不少的人都要来控告他。
我为着他而淹没于悲哀之中;拿同他的一比,我自己的情形丝毫没有给我苦痛,为着他的缘故,我将许多自责的话载在自己背上。我是这么深深地伤悼他的不幸同他现在所遇到的毁灭,我对于任何东西都没有像起先那么觉得有味,我开头对于我一向可怖可恨的生涯所发生的感想开始又到我心上来了。这些念头一来,我对于我所住的地方,和里面的生活的厌恶跟着也来了;总之,我完全改换了,变作另外一个人了。
当我这样替他伤心时候,一个消息传来,时期已近的第二次大审判开庭时将有一张呈子递给大法官告我,我一定将在老狱里受审问,我的生死也在那时断定。我的性情已经变回来了,我先前得到的死心不要脸的顽劣精神已消沉了,自己感觉到是在狱中,罪恶这观念也流入我心里了。总之,我开始用心思索,思索却的确是从地狱到天堂的一个步骤。我前面所说的许多的地狱里灵魂麻木不仁的情况只是思索的失掉;恢复了他思索能力的人是恢复了自己的人性的人。
我一开始思索,我第一下的感触是这样子冲口说出:“上帝!我将如何结果?我一定会被处死刑!我将判为有罪,这是一定的,判决之后除开死刑外不会有别的处置!我没有朋友,我该怎么办呢?我一定会判为有罪!上帝呀,可怜我吧,我将如何结果?”你们将说,这些是这么久麻木之后,第一次奔到灵魂里去的悲哀思想;但是就说这些也只是对于临到头来的祸患的恐惧;这里面没有一句诚恳忏悔的话。然而,我的确是愁得可怕,烦恼到极点;因为世界上我没有朋友可以向她说出我这苦楚的思想,这些沉重地压着我,一天中我总有好几回因此而晕倒,顿失知觉。我请我的老保姆来,说句公平话,她的确尽了一个忠实朋友的义务。她用尽法子,想阻止大审判得到那张呈子。她找到一两位陪审官,和他们谈话,努力想使他们对于这件事存个好感,因为我没有拿走什么东西,没有破屋而进,及其他这类的情形;但是也全是没有用的。因为他们受其他陪审官的支配;那两个姑娘坚决地誓言那是真正的事实,陪审官又看到状子告我偷窃同入室行劫。
当他们带这个消息给我时候,我晕倒下去,我醒过来后,我想这个重压会把我压死。我的保姆对于我真可说是一个忠实的母亲;她可怜我,她陪我哭,为着我而哭,但是她不能帮助我;更增加那可怕的是全狱里的人们都谈着我将受死刑了。我能听见她们常彼此谈论这件事,看到她们摇着头,说她们也觉得难过,同其他在那种地方常说的话。但是仍然没有人来向我说出她们心里的意思,等到最后有一位看守生偷偷地来到我面前,微叹一声对我说:“法兰德斯太太,你将在星期五受裁判,(那天才是星期三),你想怎么办呢?”我的脸色变白得同鹄一样,说道:“只有上帝知道我将怎么办吧;我是不晓得如何是好。”“啊哈,”他说,“我不来恭维你,我请你预备死吧,因为我相信你一定会被判为有罪;他们既然说你是个积案重重的犯人,我相信你不会碰到什么大慈悲。他们说你那案子是很明白的,证人们这么结结实实地发誓说看到你犯罪,那是无法抵抗的。”
这对于像我这样背着沉重的忧虑的人,真是刺到要害的一戳,有许久时候,我不能对他说出一句话来,好的同坏的;最后我却大哭起来,对他说道:“天哪!——先生,我应当怎么办呢?”“怎么办!”他说,“去找狱里牧师来;找一个神甫来,和他谈一谈;因为,真的,法兰德斯太太,除非你有很有势的朋友,你将不是这世界里的女人了。”
这的确是干脆的说法,但对于我未免太残酷了,最少我是这样想的。他走后,我陷在意想得到的最大纷乱之中,整晚我都是醒着。现在我开始说我的祈祷了,从我最后的丈夫过世之后,或者不久之后,我就老没有说了。我真可以把他叫做说祈祷的话,因为我是在这么一种混乱之中,心里这么恐怖着,虽然我哭着,重复地说了几遍这个通常祈祷,“上帝,怜悯我吧!”我却从没有想过我是个可怜的违了上帝旨意的罪人,我的确是这样子一个人,也没有想起向上帝忏悔我的罪过,求他为着耶稣的缘故而赦我。我瞧着我的情形觉得非常沮丧,因为将受生死的裁判,我十分知道会判为有罪的,同样地料得出会处死刑;因此我整夜喊道:“上帝呀!我将如何结局呢?上帝呀?我将如何是好呢?上帝呀!我将上绞台了!上帝呀!怜悯我吧!”同其他这类的话。我那位伤心的可怜的保姆现在正同我一样地焦心,比我还更诚实许多地忏悔着,虽然她并没有受审判同处分的危险。她正同我一样地该受罚,她自己也这样讲;但是有许多年了她自己没有干什么,只是接收我和别人所偷来的东西,同鼓舞我们去偷东西。但见她哭着,举动像个疯子,绞扭她自己的手,哭道她毁了,她相信有个诅咒从上天落到她身上,她一定会受天的责罚,因为她害了她一切的朋友,她带着某人,某人,某人,上绞台去;一连数了十个或十一个人,那都是不得其死的,里面有几个的事实我在前面已经述过了;现在她又做了我毁灭的原因,因为她劝我继续干下去,当我想放手时候。说到这里,我打断她的话。“不,妈妈,不,”我说,“别这样讲,因为当我得到那绸缎商的赔偿费时候,同当我从哈威治回来时候,你都是要我离开这种生涯,我却不听你的话;所以你不该负责任的;这全是我把自己毁了,我带自己到这种悲惨的地步。”这样子谈话着我们在一起过了许久时候。唉!我们找不出补救的办法;控告还是进行着,星期四那天我被带到裁判所去,在那里受他们所谓预审,指定第二天做正式审判的日子。在预审时候,我不服罪,我的确很可以这样办,因为我的罪名是偷窃同破屋行劫;那是说,偷去值得四十六金镑的二块绣花缎子,安孙尼·约翰生的货物,同打破他的大门;我却很知道他们绝对不能证明我打破了大门,他们甚至于不能说拿我开一根门闩。
星期五那天我被带去受审判。前两三天我已哭得很累了,所以出乎意料我星期四晚上睡得很好,因此去受审时俱有我真以为办不到的勇气。
当审判开始,罪名说出之后,我想说话,但是他们告诉我见证的话应当先说,然后审判官可以听我的自辩。见证是那两个姑娘,真是一对利嘴女人,虽然事情多半是真的,可是她们夸大其词到极点,誓言这项货我已经全拿着了,我把它们藏到衣服里面,我是带着它们走了,当她们出现时候,我一边脚已跨过门限,那时我又把其他一边脚跨过去,所以在她们抓着我之前,我已经带货完全离开那屋子,走上街里了,然后她们拉着我,带进来,就在我身上搜出那些东西。这许多事实大概都是真的,但是我相信,同坚持着,她们阻止我,在我的脚完全走出门限之前。但是这没有什么大用处,那总是确实的,我拿这些货物,我把它们带走,假使没有给人们捉住。
但是我辩护,我没有偷什么,他们也没有失丢什么,门是本来打开的,看见货物抛在那里,我心里想买东西,就走进去。就说看见没有人在店内,我拿一两件在手上,那也不能证明我存心偷窃,因为我没有把它们带到门外,我不过是想在光线较好地方瞧清楚一下。
法庭绝不肯承认我这句话,跟我开玩笑,我怎么会存心去买东西,因为那不是个卖什么东西的铺子,至于带到门口为着可以瞧明白些,那两个姑娘对此说出她们无礼的嘲笑,费了许多她们的滑稽话在这上面;她们告诉法庭,我看它们已经看够了,很觉得满意,因为已经将它们包在衣服里面,带着走了。
总之,我定为犯了偷窃罪,但是被认为没有破门入劫,这不能给我什么安慰,第一个罪状已使我受死刑的判决,第二个罪状不能再影响我什么了。第二天,我传去受那可怕的判决,当他们问我有什么理由不该就下判词,我站着不出一声一会儿,但有一个站在我背后的人大声劝我向审判官细说,因为他们也许能够原谅我。这鼓起了我说话的勇气,我告诉他们我没有什么话可说,能够阻止他们不即下判词,但是我有许多话可说,求法庭的慈悲;我希望他们看到这件案子里面种种的情形会有点原谅;我并没有打破什么门,没有带什么东西走,谁也没有失掉了任何东西;那些货物的主人也愿意说他希望宽恕地处置我(他的确很诚实地说出了);充其量,这也不过是初犯,我从来没有到什么法庭过;总之,我说时俱有我自己起先以为做不到的勇气,说得这么动听,虽然含着眼泪,但是眼泪没有多得挡住我的言语,我能看出这一篇话使听到的人们下泪。
审判官严重地,沉默地坐着,自在地听着,给我时间让我把全部的话说出,但是不置可否,最后对我下死刑的判决,这个判决由我看来好像是等于死刑,这个判词宣读后,将我弄糊涂了。我什么力气都没有了,我也没有舌头可以讲话了,也没有眼睛望着天或者看人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