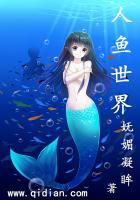当一个人认定自己最倒楣时,往往没料到可能会更糟;而当一个人确信自己占了天大的便宜时,大概就离倒霉不远了。
费九和朱六是童叟无欺的道士,只不过并非道门弟子。不是他们不愿背靠大树好乘凉,只是不得其门而入。邪门歪道倒是没什么门槛,但两人又不屑与之为伍。勉强形容费、朱二人的身份,就是心高命苦、囊中拮据的游方道人。两人毕生夙愿就是寻一座仙山洞府,开宗立派,广收门徒,风风光光做一派开山祖师,免得受那份鸟气。至于派名,搜肠刮肚后就定为“费朱宗”。
遍寻九州,游历百年,灵气充盈的洞天福地不少,可不是有上古仙人设下的禁制,就是已被修道之人占据。空下的几座都在荒蛮之地,方圆三百里内,飞禽走兽土块山石常见,人影则半个也无。每每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弄得两人都笃定——世间最不幸者莫过于怀才不遇的费、朱二宗师。
今日他们路过昆舆山,顿感此地才是梦寐以求的开府佳处,皇天后土总算相求灵验,一时涕零不已。谁知正驾遁光游走寻那灵脉根源时,眼前山色一变,打量四周,竟又回到山脚。几次三番,再蠢的人也知道有修道者设阵于此,闲人免观。
换在旧时,二人八成拍拍屁股走人,顶多骂两句“贼老天不开眼”之类。但今日不同,屡屡空手而归埋藏下的失落终于积攒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他们决定访客做不成就作盗匪。
盗匪撬门,两人破阵,动手时手法各不相同。费九得意地摇头晃脑。
“六子,当年丑道士让我做了大师兄,你还不服。看这玄牝指在咱手里随意化磨盘粗细、十丈长短的柱子,却是比你那绣花针强上不少。”
他身材高瘦,脑袋又极大,摇晃起来活托托是个庙会上杆顶球的杂耍。
朱六怒道:“老九,你这么说就有失厚道了,要不是老道贪图你烤得一手好野味,怎能让你站在我头上拉屎?你家磨豆腐出身,连个玄牝指都要弄成磨盘模样,真是老不长进。谁不知道力凝于一处才可无坚不摧?你见过拿磨盘捅牛皮鼓的吗?”
矮胖的朱六气得双腮一鼓一鼓的,颇有几分形似雨后出塘的蛤蟆,样子滑稽可笑,双手乱挥之下,指间精光划出道道金弧,半空一阵扭曲。
刚刚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两个农户模样的家伙,口口声声说此处是他们一派的修真地。费九以一敌二,险中求胜,已经自鸣得意了好一会儿。朱六为自己没能捞一个解闷,还要听人聒噪吹嘘,哪有好脸色。
说来那两个农户真元深厚,用的道法不俗,可惜临敌经验太差,他费九费大宗师刚一发狠,对方便露怯躲闪,不愿硬拼。狭路相逢勇者胜得道理,可是他费大宗师在生死历练中悟出的至理。虽然和对方硬对了两掌并不轻松,但表面上的轻松劲儿是一定要做出来的,免得被朱六胖子瞧扁了。
“唔,二位道友有何事需小道士相助吗?”
冷不防这似笑非笑的声音滑溜溜地钻进耳中,费、朱二人大惊,飘出数丈后落定身形,转身看时,一个身着青衣的小道士笑眯眯地抱着肩膀,那份泰然劲儿仿佛整个山岭就是自家后院,眼下只是饭后溜达。一副懒懒的样子挂在小道士脸上,口中叼着半根草梗,不知哪里学来的山歌小调歪歪扭扭地胡哼一通,自得其乐。
“六子,这家伙什么时候冒出来的。你一直站在后面观敌掠阵,总不会一无所知吧?”费九忐忑问道。
朱六余怒未消,没好气地答道:“掠你个大头鬼,你当我闲着望风吗?那家伙鬼魂儿似的,你不知,我也不知。”
“小道青鱼,就在山里修炼,二位贵客到访,真是茅厕升烟啊。”青衣道士仍是那种滑溜溜、懒洋洋的口气。
费九刚想说“久仰”客气一下,猛然想起自己是做恶人来着,当下横眉立目道:“费朱宗两位开山祖师费九、朱六……哎呦,你踩老子作甚,师兄自然排名在前……要占此地开宗立派,识相的速速让出,不伤和气。罢了,我们大人大量,大不了再分你们一处别院,如何?”
青鱼望天不答,良久才像是自言自语:“那就没办法了,蓉姑娘不让我动手,那么用脚好了。”余音未落,费、朱二人只觉眼前青影闪过,对面的青衣小道士消失不见。
“老九小心后面!”
“六子,你右边!”
“老九,你眼前呢!”
“明明是你……那一腿是冲你去的!”
他们平时互不相让,临阵遇敌倒也同仇敌忾。二人吆五喝六地忙活一阵,连对方衣角也没挨着,那团青影如同清风liu水无迹可寻,缠在身前身后无法摆脱。玄牝指本是极高明的道法,可惜捞不到敌手踪影一切都是枉然。
“呵呵,肥猪鬃,鬃虱,小道青鱼领教了。”短短数字却好像从四面八方同时传来,远近不一,飘忽难测。
费、朱二人明知这次算是狠狠一头撞在南墙上,仍心有不甘,当下齐喝一声,四掌相对,霎时间金光大盛。道道光箭朝四面八方疾风骤雨地狂射而出,破空的尖啸声不绝于耳。
“这下还有点意思,莫要破坏了此间景致才好。”青鱼语调不紧不慢,显得游刃有余。
叮叮当当的密响有节律地串成青鱼初时哼唱的小调,金色光箭纷纷被一道绿芒击落,转眼间烟消云散。漫天青影重又汇成青鱼的身形,他手中的草梗破烂得不成样子,额头上微微发亮,却还是一副懒懒的模样。
费九愣了一愣,低声道:“六子,你听说过用草梗破‘金霞满空’的吗?我看还是找个台阶下好了,你脸皮厚实,不如求饶。”
“放屁!你小子怕了便滚,老子和他拼了。”其实朱六早就看出不妥,心中对走为上计是千肯万肯。但听了费九之言立时血往上涌,泄气话成了激将法。
朱六上前几步,扬声喝道:“臭道士听着,你家朱六爷今日和你单挑,不死不休!”大有一去不复还的悲壮之韵。
“朱六道长何出此言?过门是客,伤了和气就不好了。”回答的并不是青鱼懒懒的声音。一言既出,宛如空谷鸣泉,清灵悦耳,将朱六满肚子火气消解得一干二净。
青鱼暗笑,蓉姑娘随出一语即消弭杀机,根本不用凝神运诀,看来醒神静心咒已臻“无为法”妙境。
山前不知何时又多出三人。当前的女子如笼在一团薄雾中,面目看不清稀,却没人怀疑她的绝代风华。身后两个少年都背着行囊,似要远行。年纪稍大的白衣少年神色也不如何冷峻,偏偏让人如面对亘古冰原,心里发寒;年纪稍小的黑衣少年阴沉着脸,双目中隐有赤血魔魇。三人正是薛蓉携清辉、方和出山。
青鱼敛襟施礼,不等薛蓉问话便笑道:“小道士只用了回风步和草梗御剑,没有动手伤人,扫知章阁的事能不能免了?”
薛蓉无奈,笑道:“千年修道还是这般模样,真不知他日道家天劫你怎么应付,一派长老却在这里胡闹。”
“小道士就知道蓉姑娘宽宏大量,青木师兄的替班还要几年才能寻到吧。”青鱼如释重负,飘然而去。临去时对清辉眨眨眼睛,将那支烂草梗丢了过来。这两个月里,在青叶门弟子中清辉与他最为稔熟,听说他当年和大闹丹霞道门大会的青简是一条裤子穿大的玩伴,为人行事多有相似之处,也闹不清到底是谁效仿谁。
费九听出这女子才是主事之人,面现难色:手下都如此难缠,这女子定是惹不起了。嘴上偏不肯放松,色厉内荏地宣称:“费九爷不会对女子出手的,小娘子回去换个男人出来,道爷与他大战三百合。”
清辉见他一会儿自称宗师,一会儿如山大王般口称大爷,忽而又成了道爷,明知不敌还死鸭子嘴硬,不觉莞尔。观者恍觉寒冰消融,春暖花开。
薛蓉正色道:“我身边这位就是本门第一高手,费道长若要请教,不妨一试。”
清辉哑然,不明所以。薛蓉低声笑道:“送上门的靶子,言公子不妨小试身手,临敌应变之道我可指点少许。这两人修为尚可,不必留力,他们当自保有余。新收的弟子对你尚不心服,可借机一展所学,收伏其心,日后省去许多麻烦。”
清辉颔首,缓步上前。冰麒灵角不可轻现,家传的短刀又拔不出鞘,索性空着手静待对方出招。
费九一眼看出面前少年身上散发的灵气虽颇精纯,但火候未足,不由大乐。适才败得毫无还手之力,谁知扳回颜面的天赐良机这么快就送上门来,只有傻子才不捡这个便宜。当下他忙道:“我兄弟二人向来是上阵不离。今日道爷贤人雅量,就吃个亏一对一好了。不过你们那边不可中途插手!”
“就依费九爷。但不知朱六爷的主,费九爷可做得?”
薛蓉此言一出,清辉暗笑。果然,对面的两位宗师很是口角一番,那朱六才讪讪退后观战。
费九右拳探出,五指依次展开,五道尺许长的金芒发自指尖,片刻暴涨至两丈长短,空中战鼓声大作,声威惊人。
清辉不为所动,食指尖冰蓝色的冰凌长约三尺,晶莹剔透宛如水晶长剑。数月前在安平酒家对付来自鬼域的四鬼使时,他还需借酒水施展凌冰术,如今已能凭空聚水气成冰,显然长进不小。
无声,无动,眼前的一切陷入静止。蚱蜢不知趣地自草间跳起,两条人影绞在半空。双方都未持兵刃,比拼的却是实实在在的剑术。费九以玄牝指运指剑,清辉则将拿手的破胄锥加持在三尺冰凌上。金光织成一道锦幕,卷天覆地,气势恢宏正大。冰蓝色的寒光往往凝而不发,偶一施展,凛冽的剑气或如飘飞雪片,或如经天长虹,撞得金色剑幕摇摇欲坠。
修道界中除了少数修士以剑术入道外,大多不擅技击。据载,以剑术入道而能得证仙道者寥寥,概因沉溺日久,杀伐争斗之心太盛,修心悟道的静水功夫就荒废了。这类修士战力不弱,但渡劫时千难万险,大多落了个魂飞魄散的下场,故而被称为左道。左道即佐道,可通而不可主。
费九于剑术极有自信,出手后一阵急攻,想以此占据上风。怎料清辉也精于搏击之道,登云谱和破胄锥用起来得心应手。百招过去,是个平手。
薛蓉灵识微察,已知身后观战的黑衣倔强少年早收了不屑之意,沉浸在眼前激战中。又战三十合,薛蓉知时机已到,传音提示道:“一心数念,收剑转守,术器并运,攻敌不备。”
清辉心领神会,连击数剑迫退如潮剑气,口中轻吟法诀,一面古色古香的铜镜自腰间宝囊飞在半空,滴溜溜旋转不停,五色霞光如悬河倒泻重重砸在玄牝指结成的金色剑幕上。镜花一出,清辉尚恐制敌不住,“离魂引”同时念动。费九哪能料到对方有如此后招,失神之下被那五色霞光冲破剑气,轰出十余丈,头上乱蓬蓬的道髻成了冲天扫帚状,道袍破烂,周身冒起缕缕青烟和烤肉香气。
朱六急冲过去要扶费九,却冷不防被其用力推了个趔趄,心知人家留了情面。费九看似狼狈,实则受伤不重,否则哪有这等力气把好心当成驴肝肺。
费九可不领情,怒吼一声又要冲向清辉,才迈两步,一道纯白光带将其裹住,一收一放送至朱六身边。费九摸摸头脸,伤已痊愈,又见那女子冲自己点头微笑。双方修为天差地别,又受了对方恩惠,费九一跺脚,嚷道:“算了,算了,道爷倒霉,今天不打了。”说完拉起朱六转身要走。
“二位道友留步!”薛蓉声音不大,但传到已驾遁光走出百丈外的费九耳中却如对面交谈。
费九按下遁光,不耐烦地应声道:“你这女人还有何事?怪不得刘瞎子说老子会栽在女人手里。”
“敝派栖身昆舆山一事请二位守口如瓶。”
“咱兄弟二人不会乱说的,小娘子放心,也不是啥光彩事。我朱六要是乱说,老天让我比费竹竿还倒霉。”朱六对刚才好心贴了费九冷屁股一事耿耿于怀,借机挖苦。
费九反唇相讥,不甘示弱:“朱胖子,你没胆上就别说嘴,那女人的白光你能破解,还有臭小子的烂镜子?你放心,费朱宗……唔,这个,道爷一言七八鼎,对今日之事绝口不提。”
“小女子还有一事相询。”
费九为防朱六又有怪话,抢先答道:“女人就是麻烦,有话快说。”
薛蓉似是随口一问:“近日修道界可有什么大事吗?我这里偏僻,多日不曾走动,消息闭塞。”
费、朱二人好像听到了天大的笑话,报复性地狂笑半盏茶的光景,才由朱六答道:“瞧小娘子修为不错,却忒无知了些,怕是现在修道界的阿猫阿狗也得了消息的。两个月前,离此千里的盛青山着实热闹了番。后来听说正邪两道死了不少高手,更奇的是还有几十人发了癫。嘿嘿,不过他们也没白死人,几十件仙宝出世,千年以来都没这么多好玩意儿啊!比起传闻中的镇星怕是不如,但仙宝啊,要是我们兄弟有一件,啧,开宗……反正传闻正邪两道都有所获,而且正道五派好像还要搞一个诛魔鉴宝会,似乎是抓了个魔道妖孽准备血祭。那请柬我二人虽无缘收到,但盛会定在一个月后由天微派主持是不会错的。”
目送二人远去,清辉面色如铁,厉声狂笑:“诛魔,诛魔,哈哈,魔在何处?哪个是魔?亏这帮人说的出口!心魔不诛,反要夺宝害人,败类当道,天容我亦不容!”一语未尽,泪流满面。
薛蓉闭目无语。方和喃喃重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