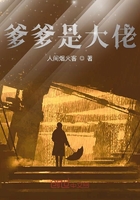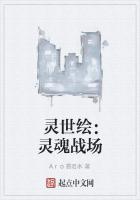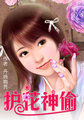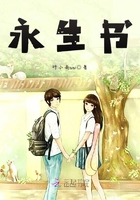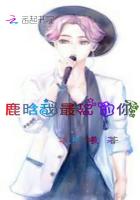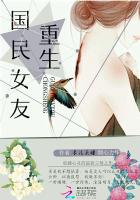外婆睡觉会打鼾,很响很响。有时晚上根本睡不着。半夜被吵醒是常有的事。那时我就轻轻坐起来,抱着腿偷偷流眼泪。而这样的画面一直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中。
刚上高中,外婆就在为我的未来做打算了。外婆希望我可以去做医生。这样家人生了病也能及时避免更为严重的恶化。可我并不是做医生的料,也只好对外婆笑笑:您还是把希望寄托在妹妹身上吧。外婆悠悠地说着,那时我都不知在哪里了。妈妈立刻把话题岔开,可是那句话却依然在我头顶上盘旋,轻飘飘的,就那么不经意地深深印在了心口。有些疼。一瞬间,我真不知该说些什么是好。
妈妈常会和我说起她的童年。她说外婆一直很幸苦。我的外公五十岁时就去世了,我甚至没有见过他。从那以后外婆一个人要带四个孩子,可她从没抱怨过什么。
这让我想起在观音像前深深鞠躬后献上几柱香的外婆。我记得外婆的神情,很虔诚。或许她在祈祷全家都能健康平安,以及祝福那远在天堂的外公一切都好。
逢年过节我们总会齐聚外婆家。常令我称赞的不仅是外婆的手艺,更令我佩服的,是这十几年来外婆做的饭菜的味道总是保持不变并与众不同的。是再高级的厨师也无法烧出的感觉。我想那是一种属于岁月的味道,那是只属于外婆的味道。
现如今,表哥表姐都上了大学。表哥一个月只回来几次,表姐甚至去了外省,一年也见不到几次。我们这一大家人欢聚一堂的日子越来越少了。大家都很珍惜每一次相聚的时光。所以气氛格外温馨。可我总觉得从外婆眼里分明看到了落寞。真希望那是错觉。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对外婆的感觉一直很迷离。毕竟小时候曾有那么一段时间不很喜欢外婆。但我相信对外婆的感情是一点一滴不断积淀起来的。就像这首童谣般,渲染了我的整个生命。
认清你自己
彼得小时候家里很穷,父母又在他刚上大学时相继去世。但是噩运并没有击倒他,反而让他坚强起来。彼得经过苦苦拼搏,好容易才供自己和弟弟加里上完了大学。大学毕业后彼得又凭着他的勇气和才华,在纽约开了一家广告代理公司,事业蒸蒸日上,他自己也成为当地的成功人士。
有一天,彼得来到弟弟加里所居住的城市波士顿,住进了一家旅馆。他没有料到,就在这一天,三个电话竟改变了他的生活和他的一些做人处世观念。
刚刚住下,他就急着给弟弟家拨了电话,电话是弟媳安妮接的,他以命令的口吻要求弟弟加里和安妮一定要来和他共进晚餐,他希望今晚就能见到他们。
“不,谢谢啦。”弟媳马上说,“加里今晚有商务洽谈,我也忙得很。如果他打电话回家,我会让他给你个准信的。”
他听出,她的话中有不屑的味道。他不在乎地耸耸肩,然后给一个大学的老朋友挂电话,请他共进晚餐。这位朋友的回答使他感到震惊:“加里和安妮恰好今晚请客做东,我们一起去,在那里会面?”
他感到非常困惑和尴尬,甚至有些生气。当他刚刚放下听筒,电话铃又响起来。
“哥哥吗?我是加里,你都好吗?非常抱歉,今晚我实在抽不开身,明天一起吃饭怎么样?”
他几乎不相信这是弟弟亲口说的话。他只好咕噜着答应。
为什么他们要对他撒谎?彼得一夜难眠。第二天,他就急急开车来到弟弟家。
安妮一开门,他冲口就问:“昨晚你们为什么不请我?”
“彼得,我对此非常抱歉。加里本来要请你,但我告诫他,我们最好不要把好好的聚会给毁了——你准会把一切给毁了的。”
“你怎么能这么胡说?”彼得生气了。
“因为这是事实。彼得,你为什么就没想到我们迁居波士顿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要摆脱你呢?你是个成功人士,处处要引人注目。只要你在身边,加里就感觉是在你的阴影之下。凡加里要说的每句话、要表达的每个意见、想说的每件事,你都要他符合你的意愿,甚至你对他的每个做法都要提出不同意见。昨晚的聚会,大学校长也出席了。我们希望加里能得到升迁,而你若在的话,总是将自己凌驾在加里之上。这就是我决定不邀请你的原因。”
这件事令彼得很苦恼,但他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几天后,彼得来找他的朋友、心理医生爱德文。
“这件事一直让我不得安宁,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彼得说,“那个女人是我的死对头。我决不能让她离间我和加里,得想个解决的办法。”
爱德文医生看着彼得。“其实,问题出在你这儿,不过解决的办法我有,”他说,“只是怕你接受不了罢了。你的弟媳给你的忠告也许是最好的:要有自知之明。与其他人一样,你不是一个人,而是三个:你自以为你是什么样的人;在别人眼中你是什么样的人;最后,真实的你又是什么样的人。一般说来,那个真实的‘我’,没有人知道。你为什么不试试和他熟悉一下呢?你的生活将会因此而全盘改观的。”
爱德文医生建议他:面对自己,在开口或行动之前,先与自己的最初想法或冲动较较劲。
那天晚上,彼得与几个熟人一起去吃饭。其中一位开始说笑话,而这笑话彼得早就听过,所以他眼光飘移,显得漫不经心。他想到另一个更有噱头的趣闻。他心痒难熬,恨不得那人立刻闭嘴,好让自己开口。突然,他心中凛然一惊,记起爱德文医生的告诫,而安妮的话又一次在他心中响起……
当大家都笑起来时,彼得冲口说:“妙极了,你说得真是太精彩了。”那位说笑话的人投给他感激的一瞥,表示领情。
这小小的经验正是彼得向自己挑战的起点。诸如此类的事,他又在自己身上发现不少。越是深入了解自己,他越感到不能容忍自己的缺点。
两周后,他告诉爱德文,他为自己的行为深感悔恨。“我现在打算再去波士顿一趟,这小包是我给侄儿捎去的生日礼物。我本打算给他买一架价值5000元的照相机,但我立刻意识到,这昂贵的礼物会把他父亲可能给他的普通礼物比下去的,这样不好。而这一包礼物却是金钱买不到的。”
安妮给他开门时眼中露出疑惑的表情,彼得脸上带着微笑。一会儿,他与侄儿坐在客厅的地板上,他的膝盖上搁着打开的礼物:那是一个黑本子,破旧的封面上看不见书名。“这是一本剪报簿。”彼得对孩子说,“我珍存它已经好多年了。我将有关你父亲的东西都贴进去:他在中学时曾获游泳冠军,我将体育的报道剪下来贴进去,这是相片。这里还有一封信,是我世上第二要好的朋友写的。你看,这信上说,‘你’也就是指我,才华横溢,可你弟弟加里却有着温柔的心肠——这是更可贵的。”
突然,孩子问:“那么,这世上,谁是你第一要好的朋友呢?”
“就是窗口前站着的这位太太,”彼得说,“好朋友敢跟你讲真话,而你母亲就是这么做的——当我最需要的时候,她给了我忠告,让我认识到了自己的缺点。我怎么感谢她都永远不够。”
接着,安妮还做了一件让彼得感怀一生的事——她用双臂搂着彼得的脖子,给了他一个姐妹式的亲吻。
手心与手背的另一种诠释
他出生那年,正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母亲只生了这一胎,就做了结扎。按理说,他应该是家中的独苗了,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但是偏偏在他呱呱坠地之前,已经有个和他长得一模一样的小家伙哭声嘹亮地候着他了。于是,他就这样做了弟弟。
两个人长得实在太像了,父母不知谁是谁的时候就解开他们的纽扣。他的胸前有一颗痣,而哥哥没有。
学校里,两个人你追我赶谁也不服输,年年捧回的奖状都是花开并蒂。他们兄弟俩成为村里人教育孩子的楷模,成为父母的骄傲。然而,这种安宁维持到他们初中时出现了变化。那天,父亲在地里被一条毒蛇咬伤,因救治不及时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他们虽然清贫却幸福的天空一下子坍塌了,母亲瘦弱的肩膀扛不起两个孩子的求学路。在父亲的遗像前,母亲流着泪高高抛出一枚硬币。正面代表他,反面代表哥哥。三个人,同时紧张地屏住了呼吸。一道银白的抛物线后,是反面。他急得一脚踩在硬币上,这样不公平!看母亲态度坚决,他突然灵机一动,指着自己胸前的那颗痣,强词夺理地说,你们看我,我与哥哥有什么不同?我胸怀大“痣”,我才是上天注定的读书人。母亲闻言,崩溃般坐在地上自责地哭号,为一个十多岁孩子的绞尽脑汁,为她自己的力不从心。
哥哥主动退了学,挽起袖子和裤腿下了田,他穿得干干净净去了学校。他很开心很快乐。只是,眼前老是不由自主地晃过两个画面,让他的快乐突兀沉下。一个是哥哥退学时的伤心眼神,另一个是哥哥涨红了脸强忍着不哭的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