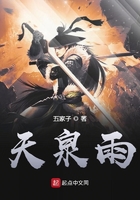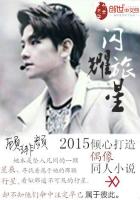不肯举白旗
1928年2月,胡适带着儿子祖望到苏州讲学,这一年他刚满37岁。来苏州前,有一个朋友对他说:“你去苏州,有一个人不可不看,他就是苏州中学的老师钱穆。”一个不可不看的人物,他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胡适没有来得及多想,就在心里记住了这个叫钱穆的孩子王。
来到苏州,正好有一场安排在苏州中学的演讲,一上台胡适就发现,钱穆正在演讲台上陪他而坐。刚一坐定,钱穆就说:“适之先生,《史记·六国年表》我遍寻不着,您知道它吗?”钱穆突然提起很偏僻的史料,即便满腹经纶如胡适者,一时也难以作肯定回答,胡适便当众愣在那里——他认定钱穆是有备而来,故意以此来暴露自己的不足令自己难堪。本来一场双方都很期待的聚会,就因为钱穆劈头一句话令胡适大为恼火。演讲结束后,主人留胡适在苏州停留一晚,胡适坚决拒绝,他说:“实在抱歉,我没有带剃须刀,这一晚会让我十分难受。”他坚持走了,但还是给钱穆留下一个地址,说:“去上海,可以到这里会晤。”
因为一把剃须刀就要连夜赶回上海,大家都认为胡适小题大做,只有钱穆明白,胡适其实是以此为借口而不想与他交谈。后来钱穆分析说:“自念余固失礼,初见面不当以僻书相询,事近刁难。然积疑积闷已久,骤见一天下名学人,不禁出口。亦书生不习世故者所可有。适之是否为戒不与余语。”此后钱穆始终不去向胡适询问。在双方眼里,一个故意刁难,看别人出洋相;一个度量极小,名不副实,这样的开头预示着两个人关系不妙的结局。
几年后钱穆进入燕京大学任教。有一次他与顾颉刚为老子的年代问题来到胡适家——按钱穆的性格,他是不想主动贴上来巴结胡适。但是顾颉刚告诉他,适之先生曾当众提起过他,有人问胡适先秦诸子方面的问题,胡适说:“以后这样的问题不必问我,直接去燕大问钱穆好了。”就因为这一点,钱穆走进了胡适的家,他想得到胡适的认同。但是胡适却沿袭清人的看法,认为老子年代早到春秋晚年,略早于孔子,并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明确了这一点。而钱穆的《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则认定,老子晚到战国,晚于孔子。得到梁启超的赞同后,钱穆认为胡适护着老子,观点不值得一驳。这样一说胡适就火大了,当着学生的面愤愤地说:“老子又不是我的老子,我对他哪会有什么成见呢?”在学术方面,本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时间断代可以多方查证,可是钱穆就是一副得理不让人的劲头,也可能在心里他早就对这个名闻天下的大学者心怀不满。有一次在教授会上,钱穆与胡适“冤家路窄”,钱穆仍然不依不饶:“胡先生,老子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了。”胡适却心平气和地说:“钱先生,你的举证仍不能让我心服口服。如果能使我心服,我连老子也不要了。”张中行在一旁唯恐天下不乱,对别人说:“胡书早出,自然按兵不动,于是钱起兵而攻之,胡就是不举白旗。”
总唱对台戏
钱穆与胡适的矛盾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不久,钱穆调入北大历史系,与胡适有了更多的接触。抬头不见低头见,最初的印象先入为主,以致胡适一直无法更改对钱穆的不良印象。
钱穆到北平,除了仅有的那次外,一直不肯去胡适家走动。有人问是何因,钱穆说:“我想,适之先生既不似中国古代之大师,亦不似西方近代之学者专家。世俗之名既大,世俗之事难免会困扰他,我不愿再增其困扰,只能远避为是。”果真像钱穆说的是“不愿再增其困扰”?周边的同事都认为“非也”,也非钱穆自谓的那样,“性迂直,不能应付现代之交际场合”,大家认定只有一种可能,就是钱穆对胡适的学问就是不服,潜意识中一直有叫板的意思,这种念头从他们在苏州的首次见面就有了。胡适也早就意识到了,但一向开明包容的适之先生,面对钱穆这位饱读诗书的后学,一直没有主动,更缺乏礼贤下士之风,这可能导致钱穆心态越发失衡。有一次,胡适生病入院,同事们都去探望,唯独钱穆不去,有同事责问他:“适之先生生病,访者盈户,你能不去看望?”钱穆答:“这件事与学术上的事显然不是一回事,你合起来这样说,叫我今后如何做人?”钱穆这时候才深深意识到,他进入了北大,仿佛进入一场是非之中。就在他忐忑不安时,又发生了一件事。这天晚上,胡适竟然不请自来,来到钱穆的家,这在钱穆来北平的八年中是绝无仅有的一次。钱穆一时还没有从愣怔中醒悟过来,胡适却开了口,原来,他来到钱穆家,仅仅是为了与钱穆商量解聘钱穆的好友蒙文通的事情。钱穆一听,自然急得跳脚——北大历史系的同仁都知道,蒙文通与钱穆是非常要好的知己,蒙文通最早赏识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并将其发表在杂志上。就是这个蒙文通,来北大任教数年,也没有登过胡适的家门。钱穆当即为好友辩护,胡适说:“文通上课,学生们都说,不知道他在说什么。”钱穆说了半天,胡适一句也没听进去,两个人闹得不欢而散。看着胡适离去的背影,钱穆心里一阵阵发冷,他明白,下一个解聘的就该轮到他钱穆了。于是,他将所有的积蓄全都用来买书,一共买了五万多本书。同仁惊讶地说:“买这么多书,真要做大学问哪?”他笑着说:“我怕是要被学校解聘,不得不提防着。一旦解聘,这些书可以摆一个书摊,不用为生活发愁。”
个人感情上的隔阂、学术观点上的对立,导致钱穆与胡适的关系越来越恶化。那时候在北大历史系,钱穆讲诸子百家,胡适讲先秦哲学,范围大致相同,观点却常常对立,对台戏常常上演,并轰动校园。无数学生包括教授的太太们,上午一窝蜂去听胡适讲课,下午一窝蜂去听钱穆讲课,胡说钱的不对,钱说胡的不是,闹得沸反盈天,成为北大一景。更有胆大的学生起哄,上书学校让胡适与钱穆同堂讲课分庭抗礼,结果两个人都拒绝,毕竟那是令人难堪的事,还有点儿近乎儿戏。后来商务印书馆要编中学教材,找胡适做主编。因为钱穆做过中学老师,有教学经验,胡适便来找钱穆合作,钱穆却一口回绝了,他说:“我们观点不一致,没法合作。要不,你编你的,我编我的,这样对读者或许更加有益。”胡适听着,说不出一句话来。
胡适与钱穆的失和,却一直没有影响钱穆在北大的教学,这不能不说胡适有一定的度量。到台湾后,胡适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在他的有生之年,钱穆一直没能评上院士。李敖为钱穆打抱不平:“他(指钱穆)在古典文学方面的成就,早就该入选院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