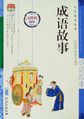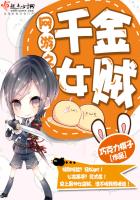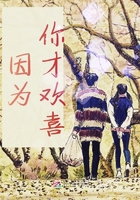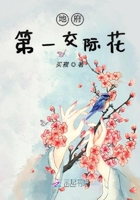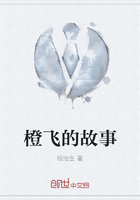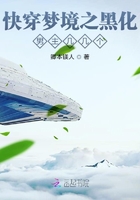一个是米饭,一个是中药
胡适与鲁迅的交往早在1917年便已开始,鲁迅无论是住在绍兴会馆还是在八道湾,胡适都去拜访过。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引起极大反响,被称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山之作。鲁迅十分高兴,请胡适来吃饭,一道放过辣椒的梅干菜扣肉和一道朱安自制的油炸白薯饼让胡适百吃不厌。胡适很好奇,问鲁迅:“据我所知,江浙一带人爱甜不吃辣,先生好像是个例外?”鲁迅说:
“你说对了,我们绍兴人没有吃辣椒之好,独鲁迅有辣椒之嗜。我是用此物解困。”胡适非常奇怪:“用辣椒解困?”鲁迅点点头:“辣椒是最妙的解困之物,夜深人静天寒人困之时,就摘下一只辣椒来,分成几截,放进嘴里咀嚼,直嚼得额头冒汗,眼里流泪,周身发暖,睡意顿消,于是捧书再读。适之先生可以一试,我早在金陵江南水师学堂时,就用此方读书,得过一块金质奖章,我到鼓楼将它卖了,买了几本喜欢的书,还买了一串红辣椒,半夜三更困了,就在辣椒串上摘下一只。”一番话说得胡适哈哈大笑,两个人弃文化谈美食,一时十分投机。
其时鲁迅已在北平居住好几年,适应了北方的饮食习惯,鲁母曾打算请一位北方厨师,鲁迅一问工钱,嫌要价太高而拒绝了。他所住的绍兴会馆提供伙食,可是饭菜很难吃,嘴馋时,鲁迅就自己上菜市场买一只鸡回来炖汤下面吃。鲁迅很喜欢吃鸡汤面,或者到附近的清真馆吃清汤大块牛肉面,这种牛肉面是用原汁牛肉汤加上肥瘦相当、切成方块的牛肉,配以北方的切面做成,售价不高却经济实惠,很得鲁迅喜爱。
那时候朱安、周母和鲁迅一同在北京生活,鲁迅请胡适吃的一道油炸白薯饼便出自朱安之手。鲁迅有胃病,许多食品不能吃,对油炸点心却偏爱。朱安为了讨鲁迅欢心,常常制作白薯饼,将白薯切片,和以鸡蛋、****,然后油炸,香甜可口,鲁迅几乎天天都吃,还常常用以待客。这制法不见于任何菜谱,后来有人戏称之为“鲁迅饼”。胡适有一次在鲁迅家吃到一种点心“萨其马”,这是满族点心,用蜜糖黏合而成,不是很甜,绵中带脆,价格低廉,鲁迅很喜欢用它当夜宵,也喜欢拿它来待客。
这一时期鲁迅和胡适经常在一起吃吃喝喝,两人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的主张是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反对旧道德、旧礼教,提倡科学民主。胡适一直想写一本《中国小说史》,拖了几年也没写成。事隔三年之后,鲁迅写成了《中国小说史略》。胡适对鲁迅的捷足先登不是心怀妒忌,而是报以热情夸赞,认为“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此后两人常常一唱一和,一个说明,一个补充,发表了众多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文章,开启了一代人的心智。比较两人文风,胡适偏向温和,像米饭一样给人滋养;鲁迅偏重激烈,像中药一样直抵病根,两人合在一起,正好是一个治病,一个养命。
一个在谩骂,一个在躲藏
1924年,鲁迅与女学生许广平同居后,他与胡适的关系渐渐开始走下坡路。这是不同的政治观点导致的必然,胡适能宽容待之,而鲁迅则以谩骂相对。
1924年4月12日上午,一艘轮船沿黄浦江缓缓驶进上海汇山码头,当船上红帽银须的印度诗哲泰戈尔出现时,岸上人群发出一阵又一阵的欢呼声,印度人则站成一排唱起了印度歌。享誉世界的泰戈尔应中国讲学社的邀请访华,他自己也按捺不住对中国文明的向往,主动促成这次交流,希望自己的访华行动能使中印两国中断多年的文化交流得以恢复,从而扩大东方文化在全世界的影响。然而,令他始料不及的是,他的到来像一块巨石投进水池,引起轩然大波。据说当时的文化界围绕泰戈尔的到来分成两大阵营,一派是徐志摩、梁启超、胡适的“保泰派”,一派就是陈独秀、瞿秋白、茅盾、鲁迅为代表的“驱泰派”。让人不能理解的是,作为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一个享誉国际的诗人和文化使者,泰戈尔的到来为什么会受到一批中国文化人的驱逐呢?原来一些激进派认为,泰戈尔是西方文明的敌人,是科学思想和物质进步的反对者,是顽固守旧的过时人物;再加上泰戈尔在几场演讲中表现过对中国某些落后、腐朽的东西的赞美,这更让他们不能忍受。于是他们散发传单,干扰演讲,号召大家一起来驱逐泰戈尔。鲁迅还写了一篇文章《骂杀与捧杀》,痛斥保泰派。这一分歧似乎是胡适与鲁迅分道扬镳的开始。
5月10日,泰戈尔在北京进行第二次演讲,正式开场前,胡适慨然登台,对驱泰派提出了最后警告:“余以为对于泰戈尔之赞成或反对,均不成问题,惟无论赞成或反对,均需先了解泰戈尔,乃能发生重大之意义,若并未了解泰戈尔而遽加反对,则大不可。吾尝亦为反对欢迎泰戈尔来华之一人,然自泰戈尔来华之后,则又绝对景仰之,盖吾以为中国乃一君子之国,吾人应为有礼之人。”胡适的警告并没有奏效,泰戈尔的这次演讲仍然受到干扰,这使泰戈尔在离开中国时十分伤心。随后不久,胡适连连“高升”,与鲁迅的关系日见疏远,鲁迅逮着机会就批评胡适,从“新青年》的双簧信”到“整理国故”,鲁迅与胡适越走越远。但胡适不闻不问,一直躲避着与鲁迅交战。
可是鲁迅一直“咬”着胡适不放,从溥仪召见到******召见,鲁迅新账老账一起算,在多篇文章中将胡适骂得狗血喷头,比如《出卖灵魂的秘诀》(《申报》)、《算账》(《花边文学》)、《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且介亭杂文》)等,对胡适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抨击。
不管鲁迅如何痛骂,胡适抱定“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态度,从不回应。但是对于鲁迅的文字,只要他认为是好的,仍然大力肯定。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随感录》,胡适就大为赞赏,感动得“一夜不能好好地睡,时时想到这段文章”,后来在讲演中,还多次提到这些文字。1958年在台湾,谈到鲁迅时胡适又说:“他在我们那时候,他在《新青年》时代是个健将,是个大将。我们这帮人不大十分做创作文学,只有鲁迅喜欢弄创作的东西,他写了许多《随感录》、《杂感录》,不过最重要的是他写了许多短篇小说。”
对于鲁迅在创作上的成就,胡适给予肯定,但他又认为后期鲁迅是“赶热闹的”,是“慢慢走上变质的路子”——这是不同的思想观念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下得出的不同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