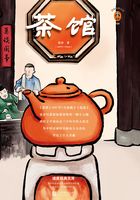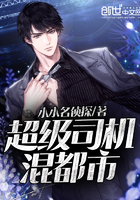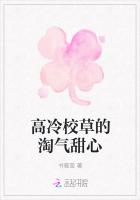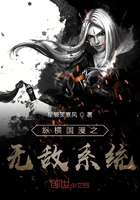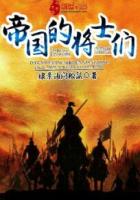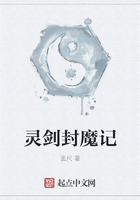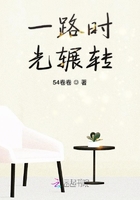一幅古画
1944年,季羡林因二战被困德国,听说陈寅恪先生正在英国就医,连忙给陈先生写了一封信,并附上论文,汇报自己十年来的学习成绩。陈寅恪很快就给他回了信,介绍他去北大工作,校长胡适接受了这个三十岁出头、籍籍无名的留学生。
季羡林有三年时间与胡适在一起,虽然辈分不同、地位悬殊,但是胡适待人一视同仁。胡适是校长,季羡林是普通教员,按说两人见面很难,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在北大孑民堂前东屋那间窄狭简陋的校长办公室里,季羡林有事没事就爱进去闲扯,一扯起来就没完没了。有的老师就烦他,认为他只说不做。胡适并不烦他,总是笑眯眯地看着他,说:“你又来了?”季羡林笑一笑说:“是的,我又来了。”季羡林明白胡适不会烦他,相反,他知道胡适喜欢自己,胡校长多次在教授会议上、文科研究所导师会上,还有在图书馆的评议会上夸奖过自己,还提拔自己当了东语文学系主任。在季羡林眼里,大学者胡适从来不摆教授和校长的架子,也绝不老气横秋。相反,胡适有时候竟然像调皮的小男生一样,行为举止令人捧腹。
有一次,教授杨振声先生收购了一幅名贵的古画,他一时十分得意,拿到办公室来给季羡林看,让季羡林确定是不是真品。那张发黄的画子在办公桌上铺开,上面画了一个披发赤足的男子,画子名为《金蝉脱壳》,署名为扬州八怪之一金农。季羡林只知道金农的书法很独特,仔细一看题款,果然是金农体,综合画面布局和韵味,他本能地有一种直觉:此画是真品无疑。其时正值下课时间,教授们听说杨振声收到了金农的一幅画子,呼啦啦全围上来,有说真,有说假,一时乱糟糟一片。胡适夹着讲义进来,有人说:“校长来了,快收起来吧。”可能胡适平时为人挺随和,与教授们打成一片,并没有人拿他太当回事。胡适听说在看古画,也来了劲,拨开人群:“我看看,我看看。”他挤进来,只扫了一眼,突然出手将画子三把两把卷成一只圆筒,往袖笼中一插,转身就走。教授们见状,哈哈大笑,只当是开玩笑。
可是一连几天,胡适并未将画作交还杨振声。杨振声渐渐坐不住了,莫非校长相中了这幅画子,要中饱私囊?他将疑惑说给季羡林听,季羡林当即说:“不会的不会的,胡校长只是搞一下恶作剧而已,他的人品你还不知道,我绝对可以替他打保票。”杨振声说:“是啊,我怎么会怀疑胡校长的人品?可是,那张画子他为何老不还我?我是用太太的金镯子换来的。”季羡林想了想说:“想必他是忘了,你不好问我帮你去问,我正好有一篇稿子要交给他。”
当天下午,季羡林又来到孑民堂前东屋校长办公室,交完稿件之后,他坐着没走。胡适眉开眼笑地说:“杨教授让你来讨画子吧?”季羡林听到这话也笑起来,胡适胡乱翻着面前的书本,说:“我这里没有,你都看到了,我这里是没有的。你叫杨教授好好找找,我这里是没有的,你让他好好找找,肯定能找到的。”季羡林听到这里,已明白了八九分,径直走到杨教授的办公室。杨振声看到季羡林空着一双手走过来,脸都白了。季羡林明白他的心思,一句话也不说,打开他面前那些永远也锁不上的破抽屉,果然在左边那个抽屉里发现了那幅金农的古画。季羡林抽出来扔到杨振声面前说:“画子是你自己藏起来了,还要找胡校长要。”就在杨振声一阵诧异间,胡适走过来,脸上挂着调皮的笑意。
两件小事
季羡林始终记得胡适做过的几件小事,小事虽小,却可以看出胡适为人处世的一面。可能因为是季羡林亲眼所见,所以他对这些小事一直记忆犹深。
一次是北平即将解放前夕,学生经常举行示威游行,比如沈崇事件、反饥饿反迫害等,大家都知道此类活动的背后是****地下党在组织发动,适之先生焉能不知?但是,几乎每次有学生被国民党宪兵队与警察逮捕之后,胡适都会乘坐一辆当时北平还极少见的汽车奔走于各大衙门之间,呼吁或逼迫国民党当局释放青年学生。他还亲笔给驻北平的要人写信,为了同样一个目的:无条件释放学生。
另一件就是有一天季羡林来上课,先到校长办公室去见胡适。当时胡适正在埋首阅读公文,指了指椅子让季羡林暂时先坐会儿。季羡林就在胡适对面坐下来,正想喝杯茶,却见一个学生大步流星走进来,看了看季羡林,也不避讳,开口便说:“胡校长,昨晚延安广播电台曾对您有专线广播,希望您不要走,北平解放后,将任命您为北大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季羡林一听相当吃惊,而胡适似乎早有耳闻,对那位学生只是非常和气地微笑着说:“人家能信任我吗?”那个学生愣了一下,又说了几句什么,胡适仍然微笑不语,那个学生只得离开了。
学生的身份不用猜测也能明白,但是胡适的态度始终亲切、和蔼。季羡林似乎仍沉浸在刚才发生的一幕中,一直到胡适叫他,他才醒悟过来。后来季羡林在《病榻杂记》中这样写胡适:“我觉得,他一生处在一个矛盾之中,一个怪圈中,一方面是学术研究,一方面是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他一生忙忙碌碌,倥偬奔波,作为一个‘过河卒子’,勇往直前。我不知道,他自己是否意识到身陷怪圈。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认为,这个怪圈确实存在,而且十分严重。那么,我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呢?我觉得,不管适之先生自己如何定位,他一生毕竟是一个书生,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书呆子。”
季羡林后来也承认,胡适很复杂,不是那么很容易归类——对未来,对理想,胡适都有自己的主张,他自己说过,“我一辈子没有写过批判共产主义的文章,而反对国民党的文章是写过的。”在他内心里,他是以美国的尺寸来衡量一切社会制度,所以他离开大陆先去了美国是自然而然的选择。据说胡适离开北平后,曾派来一架专机,点名要接走几位老朋友,并亲自到南京机场去恭候。好不容易等到飞机落地舱门打开,他满怀希望准备拥抱他们,然而机舱里只走出寥寥两位朋友,他一时悲从中来,禁不住泪水滚滚而落……
几篇论文
当年在老北大,季羡林对学术研究相当投入,当时他刚刚回国,手边一时难以找到合适的资料,有一次进图书馆,发现一大批中印文化史的书籍,一时欣喜若狂,决定就从中印文化比较研究入手。三年后,他写出了两篇学术论文《浮屠与佛》和《列子与佛典》。正好不久前胡适与陈援庵教授就“浮屠与佛”的问题吵得面红耳赤,季羡林用吐火罗文解决了这个问题。季羡林不敢将论文交给胡适,怕校长说他卖弄——无论胡校长还是陈教授,他都不敢得罪,他思考了好几天,只是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态度,来到清华园将论文读给老师陈寅恪听。陈寅恪从头到尾很耐心地听完,点点头说:“有道理,很有道理,胡校长和陈教授两个不如你一个,他们争来吵去的问题,你这个小学生不声不响地解决了,真了不起。”季羡林一听老师这么夸他,一时手足无措,他掂了掂手中的论文,说:“老师,那,这个如何处理?要不要给胡校长看?”陈寅恪说:“看不看无所谓,以我对适之先生的了解,他绝不会嫉妒你,反倒会为你这个后学高兴。你将论文给我吧,反正你不给他看,胡校长早晚也会看到。”
陈寅恪老师将季羡林的论文推荐到当时地位极高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上发表。第二篇关于《生经》的论文写成后季羡林马上就交给了胡适。第二天季羡林到学校来上课,桌上就放着胡适的一封信,信中说:“生经》一证,确凿之至!”季羡林相当感动,因为胡校长连夜就看完了论文,并且认同季羡林的结论,这对刚刚踏入学术领域的季羡林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鼓舞。
打这以后,胡适就将季羡林当成一个朋友,经常与他就学术问题进行探讨。印度总理尼赫鲁派著名学者师觉博士来北大访问,此事为当时中印两国一件大事,适之先生委托季羡林接待,季羡林尚有点不自信,说:“我行吗?”胡适很不高兴,说:“怎么不行?你行!就是你了。”有一次,季羡林在图书馆开会,胡适先生匆匆赶到,在台上坐下抱拳作揖:“抱歉,下面还有一个重要会议,我要提早退席。”可那天的会议开着开着就走了题,不知怎么竟然聊到了《水经注》上,这可是胡适一直在研究的对象。季羡林发现,一谈到《水经注》,胡适立即眉飞色舞,还口若悬河,一直到散会,他也没有退席——一帮子北大教授听呆了,私下里咬耳朵:“这个胡校长,一讲起他的专业,这嘴巴可就管不住了。”
季羡林最后一次见胡适是1948年12月中旬,当时北大举行建校五十周年庆典,此时解放大军已包围了北平,城内人心惶惶。胡适一上台,仍然满面春风,作了很简短的讲话,话语里一派喜庆,没有半点愁苦的样子。他的话还没说完,城外就传来解放大军隆隆的炮声,胡适到此时仍不忘幽默,他抬头朝天上看了一眼,说:“这是解放大军给我们北大放礼炮呢!”
胡适晚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某次和研究人员喝下午茶,胡适突然说:“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季羡林那样。”可见早年在北大时,季羡林钻研学问的劲头让胡适记忆犹深,多少年过去了仍未遗忘。或者也可以这样说,胡校长从季羡林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