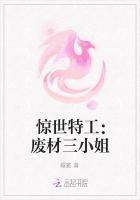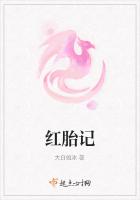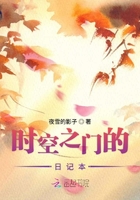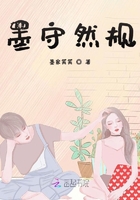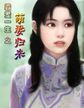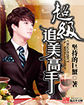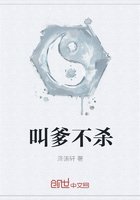亦师亦友的徽州同乡
1919年秋天,苏雪林离开徽州,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院国文系读书,刚从国外回来的胡适给她们开了一门“中国哲学”课程,苏雪林高兴得跳了起来,在心里,她一直把胡适当神明一样供着,当恋人一样爱着。
快开课的那些天里,女生们在私下里叽叽喳喳议论着胡适,说他有才又帅气,得知苏雪林和他是徽州同乡,十分羡慕。苏雪林家在太平县岭下村,与胡适的老家绩溪上庄只隔几个山头。上课的那天,苏雪林提前半个小时到了教室,可是没想到还是迟了一步,整个教室坐得满满当当的,不但是本班同学,别的系别的班的男生女生几乎倾巢出动来听课,连监学、舍监等教务处的职员都端只凳子坐在那里,像听话的学生一样。不一会儿,人越聚越多,一间教室根本容纳不下,好在校长出面,将隔壁图书室的隔扇打开,以便让更多的学生站在图书室里听讲。胡适出现在讲台时,下面黑压压的一片,且鸦雀无声。胡话说话妙趣横生,时时引起哄堂大笑。苏雪林站在离讲台很远的地方,非常着急,想下课后与胡适面对面交流,可是人实在太多,她没法挤到讲台前。
在胡适讲授“中国哲学”这一年里,苏雪林和他当面交流的机会并不多,他甚至不知道班上有一位女生是他的小同乡。上世纪20年代后期,苏雪林从法国留学回来,寓居上海从事专业写作,出版了《绿天》、《蠹鱼生活》,并在《女作家专号》上接连发表作品,算是在海上文坛崭露头角。胡适此时迁居上海,任中国公学校长。这一年的秋天,女作家冯沅君(冯友兰的胞妹)为与陆侃如恋爱一事曾求助过胡适,当她得知苏雪林想见一见十年前的老师,当即就带着苏雪林来到胡适家。
其时胡适住在江湾路,是一处石库门房子。站在黑漆木门前,苏雪林忽然有点胆怯,将冯沅君推到前面,说:“你带路。”冯沅君取笑她说:“你一向泼辣,色胆包天,今天来见你老乡,怎么忽然胆小如鼠?”苏雪林说:“人家是大师,小学生见大师,当然心里害怕。”冯沅君此前已在给胡适的电话中说过了,她牵着苏雪林的手站在胡适面前,胡适看了半天才说:“哦,是你呀,你从前上课是不是总坐在第一排?”苏雪林满脸通红地说:“坐过几次,可是先生讲课来听讲的人实在太多,我一般只能站在后排。”胡适哈哈大笑,当即让座。得知苏雪林家在岭下村,胡适马上就说:“你那个村庄我去过的,去看过抬阁,徽州抬阁想必你是看过的。”苏雪林点点头。胡适又问起她的年龄,得知自己只比她大五六岁,又笑起来:“哦,我哪敢做你老师,你分明是我的小师妹嘛。”
胡适热情好客,苏雪林还是很拘谨。这时候江冬秀走进来,送上一碟徽州麦饼(塌果),笑着对苏雪林说:“苏小姐,这个塌果你一定吃过。”胡适不待苏雪林回答,马上接口说:“那不用说,徽州人出徽州,哪有不带塌果之理?”徽州塌果一下子拉近了大师与学生的距离,苏雪林一连吃了三个,冯沅君吃了两个。胡适向冯沅君介绍塌果:“徽州在深山之中,田土很少,所以徽州人一向有外出经商的传统。徽商之所以有名,塌果功不可没——徽州人外出在路上一走就是一个月,包里的塌果就是他们的干粮。我从徽州出来时背了一大袋,想必苏小姐出来也是如此。”
苏雪林连连点头,她后来在《悼大师,话往事》中这样写道:“对着胡先生,受宠若惊之余,竟有一种如醉如梦、疑幻疑真的感觉。”这种感觉始终伴随着苏雪林漫长的一生。有人曾根据这种描写进行“心理分析”,断言苏雪林有暗恋胡适的情结——当然这只是一部分人的看法。
“脾气不好的徽州女人”
与胡适相识后,苏雪林经常写信给胡适,这种习惯保持了一辈子。在她眼里,胡适就像神明一样,任何人不能说胡适半个“不”字,一说苏雪林就急得跳脚,所以任何人只能说胡适好。对于这样一位偏执的女弟子,胡适当然会高看一眼,每有新作出版,总会寄一本给苏雪林。倒是江冬秀对苏雪林有些微辞,主要认为她“性子急躁,脾气不好”,江冬秀的话当然并非空穴来风。
1936年11月,苏雪林写了一封长信给胡适,攻击左翼文坛和鲁迅。胡适回信规劝她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他不赞成苏雪林行文太动肝火,用“旧文字的恶腔调”咒骂批评对象。苏雪林收到信后一时不太舒服,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她将此次与胡适的往返信件发表于武汉出版的《奔涛》半月刊,一时在文坛激起很大波澜。江冬秀得知后非常生气,认为苏雪林太蛮撞,这么大的事都不和胡适说一下,就冒冒失失捅到媒体上,更何况这样的内容公之于众也有损于胡适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胡适却说:“只要是事实就好,苏雪林并没有虚构,事实就是这样,让世人知道真相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苏雪林也没想到信件发表后会产生如此大的反响,有人说她高攀名人,也有人说她自我炒作,苏雪林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好长时间不敢给胡适写信。
不久,胡适突然来到苏雪林任教的武汉大学,与校长王世杰会见,苏雪林想去看望老师,又怕被胡适拒绝,一时颇为难。胡适却当什么也没发生过,两度请苏雪林吃饭,而且吃的是徽州馆子,让苏雪林开心不已。到台湾之后,两人交往增多,胡适多次请苏雪林到南港寓所吃饭,每次都少不了徽州一品锅和塌果。苏雪林给胡适写信,抬头称谓也由“适之先生”改为“适之老师”,她多次这样说:“听胡先生讲话,不但是心灵莫大的享受,也是耳朵莫大的享受。”
但是这一对亦师亦友的同乡却一度差点翻脸。那是1961年,苏雪林想凭借她研究《楚辞》的成果竞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结果失败,她将这样的结果归咎于当时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在这之前,“中央研究院”就传出“苏雪林研究《楚辞》为野狐外道”之说,还加以“不科学、无根据”之评。苏雪林一气之下,将《舜的故事》、《大禹以后之夏史》等诸篇寄给胡适先生,并附信一封,大有向“中央研究院”抗议之状。信寄出后她对友人说:“若胡先生恶我无礼,从此断绝师生关系,不许我继续取得科学会补助费,亦无惧,我将远走南洋,老死海外,不向人乞此嗟来食也。”后来她申请“中央研究院”院士不中,疑为院长胡适“报复”,将一肚子牢骚告诉了老校长王世杰。
王世杰曾在******面前帮苏雪林说过好话。几年前,苏雪林在巴黎研究神学,生活难以维持。当时王世杰担任台湾总统府秘书长,炙手可热,他对******说:“苏雪林今流亡海外,生活潦倒,理应救助。”
******问明了情况,马上从特别款项中划拨了500美金给苏雪林,解决了她的燃眉之急。王世杰与胡适是好朋友,依胡适的人品,胡适绝不会有“报复”苏雪林的念头,更何况两人还是徽州同乡。王世杰给胡家去电,原来胡适久病新愈,刚刚才看到苏雪林的“抗议信”,他在电话中笑起来,说:“我的这位小同乡啊,好冲动、好偏激,脾气又不好。不要紧,我马上写信去说她。”
胡适当即在病榻上写了一封信,抬头便是“敬爱的老朋友”,劝苏雪林平心静气地做学问,“而不可轻易发脾气”,要容忍不同的意见。胡适的态度让苏雪林感到无地自容,多次致函胡适“谢罪”,并说她冲撞胡适是由于“老师平日太爱护我了,让我不免有点恃宠而骄”。次年胡适去世,苏雪林悲痛万分,为胡适编撰了一本书,名为《眼泪的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