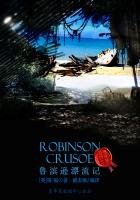如今,每当我们地方上的人哀叹这里没出过什么显赫的人物时,大家仍会冷不丁地想起樊家苟这个名字。因为外面有人,是多么的好办事啊,打官司,求职,提升,扶贫补助,各种救济,等等。在这方面,我们一直处于劣势。一条著名的铁路,也因此绕开了更近的我们,而折到了相邻的一个县。他们那里的一个人,在京城里做着很大的官。有人叹息道,这地方,怎么就出不了高官呢?于是另一个人会说,要是,要是樊家湾的家苟不那么短寿,那情况就肯定不一样了。
当时,樊家苟就读的是我们县城的第三中学。学校地处郊区,那里汇聚着许多家境贫寒而成绩优秀的农家子弟。与他同班的四十五个同学,如今有的做了企业的老板,县乡级的领导,不过大部分还是做了学校的老师。在我们这里,处理有知识的人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去教书。除此之外,人们想不出还有别的什么地方需要他们。当然,也有的回家种田去了,但那毕竟是极个别的例子。谈起樊家苟,他们都咧着嘴笑。一副返老还童调皮捣蛋的神气。他们回忆起了美好的学生时代。然后樊家苟就从他们记忆的门洞里跑出来。在他们越来越空洞了的嘴唇间若隐若现。他穿着蓝卡叽褂黑线布裤,强烈的阳光照得他睁不开眼。他严肃地站在那里。他的头发天生地有些卷曲,上面有两个好看的漩涡。而很多人,都是只有一个的。他面色苍白,略呈菜色,显得营养不良。他的眼睛却像两个幽暗遥远的灶膛,有什么在里面一刻也不停地燃烧。他的手却很小。又软又白,完全不像贫寒人家子弟的手。它们阴柔地插在口袋里,平时默不作声。也从不和周围的事物产生不必要的联系,比如扯一片树叶,扔一块石头,往塘里打水漂,等等。他的手独来独往,惟一感兴趣的是象棋。就是睡觉,手也和象棋呆在一起,就像马和草原一样。指尖的罗纹和棋子磨擦得互相发出了光辉。很快,他就在学校找不到下棋的对手了。跟他下棋,几乎让人丧失对人生的信心。他三招两式地,也不吃你的子,但你很快会发现,你的将领已经动弹不得了。双方人员性命保存完好,但输赢已判然分明。这简直是有邪气了。他的手,似乎有一种天生的、对弈技或权术的迷恋。是的,他不喜欢追杀和动武。他喜欢的只是包围、软禁、精确的计算等软手段。这正是政治家的手段。他不会自己动手,一等你活不下去,自然会自杀或狗急跳墙。这样,你就没有理由责备他不仁慈。这是他的同学们对他的一个抽象性的印象。如果你想知道得更详细一点,还是去找在金溪中学教书的叶茂芳老师吧。他们说。
现在金溪中学教书的叶茂芳老师虽然看起来不大乐意,但终于还是接受了我们。叶老师取下老花眼镜,放下正在改作业的红笔,沉吟了一会儿,说,樊家苟,那都是几十年前的人了。早死好,早死才能永远年轻。那时,樊家苟和我都是班上年龄较小的学生(他大我十八天),我们还是同桌,但是全班的人,没一个及得上他的聪明。你简直不知道,他又矮又瘦,但他的脑袋,大得像一个斗,过去地主向农民收租的斗。他的额角,宽广得可以建立一个国家,他的后脑勺,方方正正,让人想起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名言。樊家苟的聪明是无边无际的,他的内心是深不见底的。他坐在我的旁边,有时候,我产生了幻觉,以为他是一个不动声色的老人。我从没见他露出过孩子的一鳞半爪。他很会读书,每次考试都是全班第一。但是他从来也不用功。他从不挑灯夜战。他像大军师庞统在做小小的耒阳县令时那样,随随便便,漫不经心。除了象棋,他还有个嗜好是睡觉。仿佛他的睡觉才是工作。上课也不例外。但怪就怪在,你问他,老师讲了什么,他知道得一清二楚,连老师打了几个喷嚏,擤了几回鼻涕,也包括在内。如果是老教师(不指年龄),他会听之任之,不管他。学习成绩是明摆在那里的,老师还能说什么?打个比方吧,他就好像是一条蛇,现在,他不过是在冬眠。他的整个学生时代,不过是他的冬眠。现在想起来,这句话是越来越正确了。你看古今中外的许多大政治家,都是有一个冬眠期的。后来,他头脑一时发热,过早地从冬眠期跃了起来,结果,他就死于非命了……
我们在叶茂芳老师家住了一个晚上。因为整个晚上谈的都是樊家苟,以致我产生了一个恐怖的错觉,以为樊家苟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他像一枚钉子,扎在人们的心脏里,然后引起了溃烂、感染、高热。正如生物学所说,一个人死了,他还以细菌的方式活在别的生命体上。我知道,人们乐于谈论樊家苟,是因为他已成了一个象征,就像他当年谈论别的象征一样。有时候,即使是谈论他,也会让人得到满足。我们都是一些没有头脑、趋炎附势的家伙。叶茂芳老师说,家苟当年在校园里挥斥方遒,也是粪土万户侯的。他的方头大脑使人害怕。他们像望着一个未知的王国一样打量着他的大脑,而且,它还在不停地生长,谁知道里面还有多少稀奇古怪的东西呢。它又像一口深井,有一回,叶茂芳老师试图站在旁边,想看看它究竟有多深,结果,先是通向它的路途忽然柔软起来,像棉花或陷阱一样,使人不知道下一步还能不能落到实处,接着,有一股飓风从里面冲了出来,打了人一个趔趄,而且,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眼前还是白光闪耀,令人晕头转向。年轻的叶茂芳哭丧着脸,此后,就断了这个念头。不过叶老师又说,等等这些,也只有和家苟交往密切的人才知道。因为在很多同学看来,樊家苟除了会读书、睡觉、下棋,在其他方面是平淡无奇的。他们见识到樊家苟的厉害,要等后来的事情发生之后。叶老师说,樊家苟很早就是一个稳重的人。他极少说话。要说,也是很中性的、合乎规范的语言。他像是回答你了,又像是没回答。本来,语言是最容易使人暴露的,可对他来说,语言反而保护了他,使他隐藏得更深。若干年后,叶茂芳老师在电视上看到了某著名领导人主持的记者招待会,便一下子想起了老同学樊家苟的音容笑貌。樊家苟也从不像其他或愤激或浅薄或勇敢或莽撞的同学,经常在各处抒写自己的远大抱负和人生志向,比如在桌子上刻上一段座右铭,或在课本的醒目位置抄几段哲理,或发出诗人般的叹息一一啊,人生!啊,理想!有史为证:少年项羽在人群中看到出游的始皇,壮言道:吾可取而代之!唬得叔父项梁急捂其嘴。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项羽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热血青年,有些匹夫之勇罢了。许多大政治家都是不露声色、不声不响冒出来的。项羽做梦也没想到他会败在一个市井无赖、浑浑噩噩的刘邦手上。前车之鉴,樊家苟不可不察。他不写日记,不作惊人之语。他的桌子干干净净,课本也干干净净,抒情作品,他更是瞧也不瞧。假如谁在路上丢了一本文学作品,他会毫不犹豫地从上面跨过去。从外表看上去,他简直是一个平庸的人,不思上进的人,自私自利的人。很多人不知道,只知道睡觉和下棋的人,要么果真庸庸碌碌,要么,就不得了,是大阴谋家野心家。种种迹象表明,家苟将来必定是一个政治上的大手笔。——叶茂芳老师忽然意识到自己的话有些混乱乃至前后矛盾,比如,一个沉默寡言一声不响的人怎么能挥斥方遒粪土万户侯?叶老师停顿了一下,说,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很多具体的事情已经忘记了,我可能把自己的臆想当成了事实,或者说,把他的内在当作了表面。因为找不到对手,家苟已经发展到了跟自己下棋的地步。他津津有味地吃着从家里带来的咸菜,从未表示过对生活的不满。而作为一个政治家,没有对生活的不满,又哪里有上进的动力呢?稍有线索可寻的,是他曾私下里跟我评论过一个很有名的历史人物。那个人在教科书上是一个反面角色(我已经记不清他为什么跟我讲这些)。他说,那个人,如果跑江湖,当黑帮的老大,可能是一个好手,但要打江山,他显然还有些文质彬彬。他的手腕,老是在关键时刻优柔寡断,犯鸿门宴式的错误。这话像雷声一样吓了年轻的叶茂芳一跳。叶看着他,好半天说不出话来,后者却镇定自若,像是在谈着他家的某一位邻居。
行文至此,我们也很困惑。究竟是挥斥方遒(自然少不了高谈阔论)的樊家苟真实,还是谨行慎言、不声不响的樊家苟真实?实际上,第二个樊家苟也许是我们的设想和良好的愿望。我们想以这种方式于事无补地作些补救,就像我们喜欢在想象中不断地用橡皮和铅笔修改少年时的天真。然而不管怎么说,随着季节的转换和事情迫在眉睫的发展,樊家苟的隐藏着的巨大天才必定水落石出,他不得不从后台走到了前台。
樊家苟作为一个天才政治家的真正的初露端倪,还是在我们小县城里。这使得我们有幸能窥见他的一鳞半爪。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追求县委书记的女儿柳咏絮的。那是高中时代快结束的时候,樊家苟和柳咏絮突然手拉手出现在操场上。他们一人手里拿了一只羽毛球拍。黄黄的太阳光从西边斜射过来,樊家苟眯了眯眼。一只不大不小的喉结已经爬上了他的侧面的剪影,就像一只蝉在树荫里嘶鸣。不过他的胡须还没有长出来,这使得那只蝉鸣叫得有些孤独。县委书记的女儿柳咏絮穿着蓝色运动服,胸前有两根白杠杠,马尾巴辫子一摔一摔的,或许她比别的县委书记的女儿更漂亮。她走到哪里,那里便成了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这句青春风格的话,使叶茂芳老师略略有些难为情。叶老师是—个慈祥的人,对于老人,我们常忽略其年龄和性别,就像我们忽略孩子的年龄和性别一样)。有必要补充一句,柳咏絮之所以在地处郊区的第三中学就读书,而不在官宦人家的子弟云集的第一中学,是因为她父亲一直在主张她“到群众中去,到农村去”。他希望咏絮和农村的孩子建立起深厚的感情。可以肯定,当时班里的男生都在暗恋着柳咏絮,但谁也不敢付诸行动,只有樊家苟“狗胆包天”(叶茂芳老师笑着说,当时,大家就是这么形容樊家苟的,以至后来,这个词汇成了同学们之间的一个特指或暗语)。柳咏絮的过于美丽使大家感到了压力。假如她不是县委书记的女儿,或者说,她是县委书记的女儿,但不那么漂亮,或许会有人愿意一试,但偏偏,两者她都具备。谁也不知道樊家苟是怎么征服柳咏絮的。随着事情的进一步发展它已经永远地成了一个谜。反正,事实就是这样的,出身贫寒之家的樊家苟把县委书记的独生女儿柳咏絮搞到了手。更让人气愤的是,他一点儿也不沾沾自喜。如果他沾沾自喜,同学们的心里也许会好受一些。但他仍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一样,这使得部分同学的忍耐力受到了挑战。假如不是木已成舟,樊家苟可能会付出一些身体上的代价的。因为据说,县委书记在和樊家苟作了一次极为严肃的谈话之后,已经默认了这件事。从此,樊家苟在柳家(即县委大院)度过了几个愉快的周末。他们在一起学习,听广播,榨蕃茄汁。柳咏絮越来越被这个贫农的儿子迷住了。他的谈吐显示出了足够的魅力和远大的前程。在某一个适当的时机,樊家苟很笨拙地吻了她。
虽然别人不知道樊家苟是怎么追求柳咏絮的,但我知道。叶茂芳老师说。你简直不清楚他是哪里来的胆量和勇气。他没有直接向她发动进攻(以她的高傲和优越,他这不是以卵击石么),而是出人意料地去见她的父亲。他自称是贫下中农子弟的代表,有事要和县委书记面谈。那时的领导,都很接近群众。至少表面上是如此。这给了他攀援的机会。奇怪的是,他和县委书记交谈得十分成功。县委书记称他是一个有宏伟抱负和远大前程的人。尤其是在得知他和自己的女儿是同班同学时,他更是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到后来,县委书记打量他的目光开始从职业的范围内斜逸出来,有了某种别的妩媚性的联想。其实,他一直是个走基层路线的人,不太看得惯大院里的那些官宦子弟。总之,樊家苟凭着他的口才抑或还有其他的什么,彻底地打动了县委书记的心。一提起这个年轻人,他就干劲倍增。他挥挥手,打断咏絮母亲的唠唠叨叨,说,妇道人家,只看在自己的脚尖上。柳咏絮对这个被父亲赏识的貌不惊人、镇定自若、甚至还有些阴郁冷漠的同学产生了好奇心,她没来得及拒绝他的一同去打羽毛球的邀请。
他的打羽毛球和他的下棋一样好。现在想来,作为一个政治家,仅仅喜欢用左手和右手下象棋是不够的,他还必须热爱某项公共性和观赏性更强一些的体育活动。樊家苟具备了这个素质。但作为一个农家子弟,他什么时候培养出了那么卓越的打羽毛球的能力,并且一直深藏不露呢?要知道,在当时,羽毛球还是个比较贵族化的玩艺儿,就像现在的高尔夫球一样。这要等柳咏絮到了樊家苟家里才知道。今生今世,她只去过樊家一次,正因为如此,印象才特别深。看得出,樊家苟的父母对他不无抱怨。他没有他的弟弟勤快。他的房间布置得不像是在农村里。墙上贴着报纸(柳咏絮还记得报纸上有篇文章题为《喜看稻菽千重浪》)。桌上铺着玻璃板,下面是几张伟人握手的照片。煤油灯的罩子擦得很亮,上面还用一只经济牌香烟盒套住。靠床的那边摆着一本红色封面的《毛泽东选集》。床上方有一张自裱的横幅,上面写着:学以致用。虽然房间是那样的阴暗(只有一扇很小的木格窗子)、窄小(在陈旧的家具间并排坐两个人都显得困难),散发着一股乡下的霉味,但樊家苟使它焕发出了有志青年才有的光辉。柳咏絮隐隐觉得这些和他在学校时很不一样,这更激起了她的好奇心。但他的父母并不因为来了城里的小姐(他们还不知道她是县委书记的千金)而对他有所收敛。他们抱怨他不劈柴,不挑水,都快分不清韭菜和小麦了,衣服还要穿好的。这真是贫寒出娇子啊。他们后悔送他读书了。读书有什么好,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知娘。万一考上个北京上海的大学,还不知道到哪儿找路费呢。樊家苟不愿听了,把房门关上。就这样,柳咏絮看到了挂在门背后的羽毛球拍。
樊家苟说,他一拿起羽毛球拍,就仿佛提前进入了将来。
他和柳咏絮在家里饭都没有吃,就从坛里舀了一罐辣子酱返回学校了。
他对父母说,别着急,你们的好日子快来了。
没多久,樊家苟果然不负厚望,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柳咏絮则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学院。樊家苟打破了小县城无人考上北大的记录,县委书记为此召开了热烈隆重的表彰大会。他拉着未来女婿的手,和他平起平坐。父亲的过于霸道甚至使做女儿的都有了意见。上学前夕,樊家得到了县委书记可观的物质资助。家苟的父母这才知道了儿子的厉害。他们吃惊得说不出话来,忙到祖坟上烧香,以及朝着县城的方向磕头。和县委书记攀上亲家了,他们走起路来就好像腾云驾雾。不过,县委书记在高兴之余,心里还是不那么踏实。凭着猎手的经验,他觉得这个年轻人有些深不可测。为此,他决定叫他来下一盘棋(当他考验一个下属的时候,也是这么干的)。在这方面,他和未来的女婿有着共同的爱好。
关于他们下棋的具体情况,如今已不可考,反正,县委书记非常满意。他告诉年轻人,他马上会调到市里去担任重要职务。至于两个年轻人的未来,他也有了初步的设想。等他们一毕业,他会作出相当妥善的安排。他拉着年轻人的手,说,孩子,你放心地读大学去,家里的一切,你都不用操心。
叶茂芳老师呷了一口茶,说,年轻人,你们终究会明白,向我来打听樊家苟的事,是极合适的,也是极不合适的。别着急,先听我把话说完。
后来发生的事,其实众所周知。家苟到北大后,一改在小县城读书时的内向、隐蔽的性格,开始疯狂地向外扩张起来。他认为时机已到。一方面,他继续给县委书记和柳咏絮写文体不同的信,一方面,开始追求和他同系的一个高级干部的女儿。不,不仅仅是高级干部,简直可以说是国家领导人了。这时的樊家苟个子高大,皮肤黝黑,眼窝深陷,鼻梁尖挺、笔直。颌下的蝉鸣叫得更加热烈。领导人的女儿读过许多俄国的小说,她很快被他的俄国式的风度迷住了,私下里叫他“我的小保尔”。后来,她送给他一双俄国式皮靴。他和她的恋爱关系已经确定下来,他很快被允许了进入她的家庭。他在她家里见到过毛泽东和周恩来。毛泽东一支接一支地抽着为他特制的加长“大中华”,周恩来的左臂极少动,看起来不太灵活。还有一次,他见到了林副主席的夫人叶群。后者还以长辈的口吻勉励了他几句。那段时间,樊家苟像害了热病似的,身子在打着抖。他满手是汗。后来,大字报和游行批斗开始了。那是一个海洋。它使得许多看似遥远的事物之间一下子有了联系和可渡性。樊家苟迅速地投身其中。但是,但是他经常出入的那个家庭的主人,竟首先遭到了批斗!他上错了船。那只船,不是开往中南海,而是开往纽约或旧金山。洪水滔天。完了,一切都完了。他被抓起来了。然后是审讯,毒打。再然后,一颗子弹使他的满腔热血得到了凝固。
一个天才的未来的政治家,就这样夭亡了。
叶茂芳老师说,后来,家苟虽然得到了平反,他家里也拿到了一笔可观的抚恤金,但这对于一个家族或一个地方上的政治损失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总之,像家苟那样有大名堂的人,三十多年来,我们这里是再也没有出过了。
她轻声说,你们是否知道,柳咏絮就是我。
叶茂芳老师说,我们当时根本不知道他的变心和他遭受到的厄运,因为同样的厄运也降临到了我们的头上。父亲被造反派揪下了台,革命群众占领了县委大院。县委会被改为县革委。我和父亲划清了界限。可悲就可悲在,作为一个人,或一个人的女儿,我竟然不知道,父亲是否真的是反动派。即使后来不给父亲平反,我眼里也是一片茫然。你说不是么?父亲后来死在农场里。没多久,母亲也去世了。落实政策后,我不愿回城,就改了名字,一直在这乡下中学呆下来了。
一晃,就是几十年了。
我问,樊家,现在还有什么人么?
叶茂芳老师说,樊家苟还有个弟弟,在我们相邻的乡中学当校长。
当天下午,我们就赶到了叶老师所说的那所乡村中学。我们向一位老师打听樊校长的住所,他朝操场上一努嘴,说,喏,那不就是。
我顺着他的所指望过去,见操场上有一男一女两个人在打羽毛球。那男的身材高大出手敏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