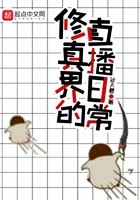她的第一次给人留下了印象的哭泣发生在她十岁的那一年。
她生长的地方是一个水边的村庄。南港湖的水很肥。有一段时间,水边的村庄曾和湖里的鱼类一样繁密如星,村里的男女也和湖里的鱼类一样肥硕健美。但是,他们都没注意到一种叫钉螺的东西的危险。村庄迅速地小了下去。到她出生的时候,只剩下十几户。还有很多村子仅剩下了村名。她五岁那年,正值壮年的爷爷得大肚子病,死了。本来有一条官道穿村而过,从坝桥直通县城,后来由于公路的兴建,自然也就渐渐被废弃了。水路已然寂寞,加上水灾经常呲牙咧嘴地爬上岸来,村子也就愈来愈偏远、愈落后了。她在村子里捉迷藏、过家家、放牛(村下首就是湖滩)、看狗打架、启蒙、识字。热闹。寂寞。更多的时候她其实不像一个女孩子。她疯跑,饭量大,上树掏鸟窝,网蜘蛛丝粘知了,和男孩子摔跤,打架,脸和手总是藏在灰尘里面。就这样一直到了十岁。
十岁这年的某一天,爹跟她说,你嫂嫂刚生孩子,身子虚弱,你送点鸡蛋去吧。她有一个堂哥,爹娘早没了,她爹娘就把他当成自己的儿子。后来,堂哥去当了兵,又提了干。从排长一直当到了营长。那时候,没爹没娘的孩子都混出名堂来了。出息了。堂嫂在县城一文化部门工作。他们的孩子,一生下地就吃上了商品粮。县城,她也是去过几回的,和比她大好几岁的人去卖从湖里扳上来的虾子。他们笑她是黄片鱼上鲤鱼的串,但他们也丢不下她。她走得飞快,用劲就像鱼吹气一样。也没迷过路。小小的脑瓜子看来很好使。从村子里到县城有近二十里路,她提了鸡蛋就跑。她很喜欢上街,喜欢闻汽车跑过留下的气味,喜欢街道结实宽阔的样子(多好啊,即使是下雨天,也不用穿又破又旧、姐姐穿不下了才给她穿的靴子,或者那又笨重又难看的木屐)。还喜欢街上有很多吃的、玩的东西。有一种油炸的面饼,薄薄的,泡泡的,甜甜的,她仅仅吃过一次,就永远也忘不了它。它悬挂在日常生活之上,引得她直流口水。她的脸红红的。像冬天、像过年那么红。她脚上的球鞋,干干净净。到了堂嫂住的地方,堂嫂很惊异于她的胆大和自立,作为奖赏,堂嫂以在文化部门工作之便,给了她一张票,让她去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
这是她第一次在电影院看电影。在乡下,电影只在晚上才能放映。大家把一张脸仰在那里,看得如醉如痴,涎液流下来了,眼屎爬出来了,也不知不觉。半路上下雨,央求放映员让他们拿又厚又重的油布伞遮了放映机,依旧仰了脸看。有时去晚了(路远,或者信息不准确),好位子被占满了,就去看反边。这样一看,就看到那些好人坏人都成了左撇子。但现在是白天,白天也能看电影么?她真有一种白日做梦的感觉。她的小学老师在形容不切实际的人和事时,总要说:白日做梦!所以她觉得新奇,紧张,还有些奢侈。她小心地找到了自己的座位。开始,她把前排椅背上的座位号当成了这一排的,结果等人多了,一个四十来岁、戴眼镜的男人指出她坐了他的位子,她才惊慌地发现自己弄错了。
人坐满了(走廊里还站了不少人),窗子忽地暗下来,她这才发现窗子上都遮了厚厚的红布。
四周就和夜晚一样了。
电影开映了。那银幕比乡下的要长,要大,要干净。她那个公社里的放映布大概是放映了大多战斗片的缘故,即使是风和日丽,也显得枪林弹雨。声音很响,吓了她一跳。像是湖面或衣绸的波浪,她感觉到了那优美的纹路。人物的话,也像是从人物的嘴里说出。不像乡下的电影,话和嘴老是有一段距离。像耳朵在说话,像那人衔着的烟杆在说话。放的是一部外国片子。她一眼就看出来了。黑脸膛,深眼睛,卷发,眉心还有朱砂痣。边走路边唱歌跳舞,也只有戏台上的人物或少数民族才做得出来。反正,她那里的人是不会这样做的。她很快就看进去了。她好像跟着那里面的人物奔跑。这时,放映布没有了,电影院没有了,其他的人也没有了。电影向她推近,推近,一下子把她吸了进去,她看清了他们衣服上的纽扣,听到了他们砰砰的心跳。她也紧张起来了。爹爹曾经赞扬了她的这种看电影的能力,说她不管是什么电影,一看就懂。还有戏,那些在乡村戏台上咿咿呀呀半天唱不完一句话的老戏,她却站在板凳上看得津津有味。
的确,她喜欢电影或戏曲这种东西。它们和繁冗拖沓的生活本身是那么的不一样。它们使她小小的脑袋从没有营养的地方、从童年里伸出来,眼睛一眨不眨。它们是公开的白日梦。是她小小胸怀盛不下的情感溢出来的必由之地。就像她每天早晨拿水浇灌院角落那棵栀子花一样,希望它每天都开出又大又白的花朵。
电影在进行。这是一部浪漫的、充满了浓郁抒情气氛的影片。但它的现实和叙事也同样结实有力。它一下一下地敲打着她,她的眼前越来越模糊。终于有一个很厉害的情节像一把刀子把她的心猛地划了一下,她再也控制不住了,大声地啜泣起来。
那是一种已然成熟的哭泣,那么富于表情,那么有张力。它和她以前的哭泣有着绝然的区分。然而它又是那么的不可抑止,不顾一切。仿佛不哭不如死掉。泪水,她小小的身体里竟然蓄积了那么多的泪水,它的流速和声响惊人。两边的人转过头来看她。前面的人也转过头来看她。泪水使她既窒息又舒畅。她在泪水里第一次到达了她的情感高潮。
她十四岁还不到,就辍学了。只读了初中二年级的一个学期。不是爹不送她读,也不是家里拿不出学费。是她不想读了。她对读书没有了兴趣。事实将会证明,她的弃学的选择是极端错误的。现在,她的身份还是一个农民。她曾在一个私人作坊做过糕点,后来又在村小学做代课老师,但哪有当年坚持把板凳坐穿了的同学好呢?他们现在都饱暖终日,衣食无忧。所以认真听讲、努力读书真的是一件好事啊。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她开始听不进老师的讲课了。她喜欢胡思乱想。想什么呢?想窗外的那只鸟为什么叫得那么欢,想家,想家里的柿子树上挂满了灯笼似的柿子,想背后山上的红薯马上可以挖了(把它沤在灶里的热灰里,过一两个时辰拿出来,掰开,又鲜艳又香甜),想湖里可以钓蟹了,想再过几个月就是新年,有新衣服穿。还有,还有,她开始想男孩子了。一想起男孩子这种健壮有力、奔跑如飞的动物,她就目光迷离魂不守舍了。她喜欢用眼的余光掠一掠他们,就像在家里看到碗里有什么好菜,便会忍不住抓一根丢在嘴里。她希望老师把男女同学错开,而不要像现在这样男同学一堆女同学一堆,一点意思都没有。除了同坐一个教室,其实她和男同学并没什么接触,一个学期也没超过说三句话。所以在她的心思里,并没有哪一个具体的男生。他们是一团模糊的、与她们不一样的空气。她幻想着,幻想着什么?其实她并不能明确地说出。反正,她喜欢她的幻想。像没有玻璃的年代里,忽然有了一件玻璃容器,她感到了新奇。她也喜欢这新奇。这种种幻想分移了她在课堂上的注意力。她惊慌地发现自己读不进书了,读书没意思了。她有些害怕。这可是没完成爹爹交给她的任务啊。村子里,就她一个人能读上初中。爹爹说,一定要好好读书,我不重男轻女,只要你读得上,我一定送。她开始排除杂念。但收效甚微。就像拿棉花条去地上打洞,怎么也钻不进去。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了。老师也觉察到事情的“苗头”了。老师把她叫到办公室,狠狠训了她一顿,用了一些诸如三心二意啦、一落千丈啦、痛心疾首啦之类的词汇。但等等这些仍无济于事,上课的眼睛仍是茫然,明明坐得斯文工整,两眼向前,老师指着黑板提问,她却不知道老师问什么。老师说,心无旁骛,不要望窗外,她懵懵懂懂地:我望窗外了吗?不是她狡辩,她是真的不知道自己走神了。谁能有意让自己走神呢?完了,老师在心里叹道,这个女孩子读书算是没指望了。想让她把心思收到读书上来,比把孵出的小鸡还原为鸡蛋还难。
后来她把这些告诉了丈夫,丈夫就笑她,刮她的鼻子。
她的不愿读书还有一个好笑的原因就是,从家里到学校太远。而且周围的村子里也没有一个女孩子读中学。每次上学,都是她孤零零一个人。遇上大风大雨、闪电打雷,她就胆小得很。还有惊惊涌涌一望无际的油菜,棉花,还有幽深的树林和起伏的茅草,是最适宜于掩藏豺狗、歹人、疯子等令人恐怖的事物的。每星期回两次家,换衣服,拿米,拿菜,放学晚,刚走出校门,天就暗了。男同学有伴,他们吵吵闹闹你追我赶,一会儿就没有了踪影。她赶不上他们,也不能和他们在一起走。夜色就从四面八方挤过来了,她喘不过气。村庄那么遥远,灯光那么遥远。书包上的金属搭扣扑打着,发出细微的、寂静的声响。她奔跑起来。一切都被淹没了。她张大了嘴巴。她哭了。她的哭声在幽暗里发出亮光,照着她跌跌撞撞地往前走。她走到哪里,哭声就先于她到了哪里。它像是一条小鱼,在夜色里惊慌地游动。在那些月黑风高的夜晚,很多人闻声而动,静耳谛听,但他们什么也没有看到,只有不绝如缕的童声。他们或许在想,是谁,能够这样一往直前地哭个不停?他们不认识她,但都认识了她的在暗夜中的哭声。它无所顾忌,疯狂生长。
爹爹似乎也听到了她的哭声。一到星期三,爹爹的耳里就灌满了这种哭声。他抽着烟,站在村上首的坡上喊她的名。他是大队的一名会计,噼里啪啦打得一手好算盘,写得一手好毛笔字,还吹得一手好笛子。年轻的时候,有月光的晚上,他会让那些月光飞起来,柳絮一般,落在人家的院荡、房顶,还有脸上。他的笛子,把水边的人都引出来,站在门槛上,望月亮。他们还不知道月亮有这么好。爹爹十四五岁的时候,就在武山共大管全校师生的伙食帐目。那时他还是学生。但后来,他被取消了学籍,打发回家了,原因是1949年以前,他家里有自己的田地。
她听见了爹爹的喊,接着望见了爹爹手里的烟火一闪一闪。她哭得更凶了。她老远就对着爹爹喊:我不读书了。
这话她说了不止一次,爹爹也不把它当真。但这一次,她是真的不肯去上学了。礼拜天下午,姆妈把菜和米都准备好了。做事回来一看,见她还没走,很奇怪:怎么还不到学?天都暗了。她说,反正是夜了,明日赶早去。第二天一早,姆妈说,我去洗衣裳,菜已经热了,装在玻璃罐里了。姆妈洗完衣裳,见菜罐和米还在,便问。她说,我不读书了。
姆妈吓了一跳。不读书,这可不是个小事。姆妈是童养媳,凡是童养媳所能吃的苦,她都吃过了。她做不了主,忙如实向爹爹作了汇报。爹爹正在坂头上耕地种菜籽,牛欺他不是种田的狠手,走得慢慢吞吞。他心软,舍不得鞭打,万一气上了头,就丢开牛绳坐到地坝上骂自己。闻讯,二话不说,提着赶牛的鞭子就回了屋。
爹爹像一头发疯的牛在屋里跳了很久,末了把她绑在门口的槐树上,高高举起鞭子,问:到底读不读书?她说:不读。爹爹说:为什么不读?她说,读不进肚。爹爹说,别人都读进了,你为什么读不进?她看着爹,乐了:我不是别人,当然就读不进了。你!爹爹把鞭子一扬,唉一一!抽在了树身上。爹爹说,不读书,你将来要吃苦哇。她哭了:爹,我情愿吃苦。
后来,她长大了。嫁人了。丈夫是她的小学同学,一个师范毕业生。在中学教书。爹爹说,本指望她考个学堂什么的,但她不肯读,现在能找个学堂里毕业的女婿,也中。她问:他戴眼镜了吗?媒人忙说:戴了戴了,好大的一副眼镜呢。她说,那不是近视眼嘛,在路上可看得人清楚?媒人说:看得清看得清,近视眼有学问。她还想跟媒人开开玩笑,但爹爹把脸黑下来问了她一眼,吓得她伸伸舌头,一溜烟跑了。
其实她并未走远。她靠在门外的石墩上,望那湖。湖像一张阔大的荷叶,风把边沿吹得微微卷起。她在想那个小学同学。矮矮的个子,白粗布褂,黑粗布裤。他母亲会织布。他长得也黑,尤其是颈后一段。她忽然有了一种好奇:他的后颈,还是那么黑得发亮吗?还有一个别人也许已经忘记了的事情是,小学五年级时,班里的同学“骂”他们是一对。原因是,当时老师按成绩安排座位,他们老是不相上下,被安排坐在一起。那是一种甜蜜的感觉,它使得他们更愿意上学,读书更认真。但表面上他们装得像是对头。有一次,他捉弄她,把她刚从商店里打的一瓶煤油弄倒了,她哭着到隔壁大队里告诉了爹爹。她爹爹边走边鼻子里嗯哼,仿佛在通知肇事的小孩快跑。他吓得钻进了桌子底下,但那桌子实在藏不住人,结果他看见了未来老丈人的脚却不知道对方也看见了未来小女婿的脚。她后来问他是否还记得这些往事,他说怎么不记得,那时我脸上虽然着恼,其实心里巴不得同学们多“骂”两句甚至永远这么“骂”下去。
出嫁的那天,很多人来看。因为她父母的好人缘,也因为这里有着看人哭嫁的习俗。这时,她的爱哭已经在四乡八邻有了名气。附带说一句,爱哭在我们的生活中并不是什么美德。一个人,到了十几二十岁,还动不动就抹眼泪,会遭人笑话的。她(他)呀,就知道哭!他们会这样说。高兴了,她抹眼泪,难过了,她也抹眼泪。这孩子,姆妈表示了忧虑和不安,担心她如此的丰富敏感,将来怎么受得了生活的苦。她仰起了脸。虽然两眼红肿,泪痕未干,但她的脸是明朗的,圆润的。仿佛那灼热而清凉的泪水,是她必不可少的营养。她的脸上有一种光辉。
现在,人们站在院子里或扒着墙头,想看她的哭嫁。她的哭嫁一定是团近四方多少年来最精彩的一次。锣鼓准备好了,大地红的鞭炮也准备好了。迎亲的队伍浩浩荡荡,彩旗招展。她洗了澡,换了新衣,新绞了眉脸,还淡淡的敷了胭脂,涂了唇膏。红盖头已经放在了梳妆盒上,已经映红了她的脸。总之,她十分地像一个新娘。而人们不知道,一个时辰前,她还在一个女伴家里玩耍。她们说说笑笑。还是女伴的母亲忽然想起来:哎呀,你今天要做新娘子了。她才一溜烟跑回来。她从门缝往院子里瞅了一眼,见她的新郎官披红挂绿工工整整正忙得团团转。
她问牵娘娘:是不是一定要哭?牵娘娘说,一定要哭,这时候你的眼泪是财,哭得越凶娘家就越发达。她扑哧笑了,心想眼泪还有这样神圣的作用。她又问,该怎么哭呢,总不能乱哭一气吧,我以前看人哭嫁听她们念念有词呢。牵娘娘说,依照习惯,你可哭:姆妈啊娘,女儿嫁到人家去心悲伤;想起家来家好远,想起路来路又长;锣鼓热闹人慌乱,绣花虽好不闻香;娘啊娘,从今后,我要叫别人的爹爹别人的娘。
牵娘娘是过来人,哭嫁自然有一手。而且,她的眼泪还真的出来了。她拉着新娘的手,要教她。这哭嫁歌,就是通过她们,一代代口口相传的。
新娘觉得好玩。这时她一点都不悲伤。她只想快点和她的新郎官在一起。他们已经有差不多一个月没在一起了。她想他。热乎乎地想。早在八月月圆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在一起了。生活是多么的好,男人和女人是多么的好。所以她听着牵娘娘唱的歌有些心不在焉。她想起那提前做了新郎的他在她耳边唱的另一首歌:吃蔗就要吃中心,讨亲就要讨远亲;一年一度去一次,好比新官去上任。
这家伙,看起来一本正经,不知从哪儿学来了这些歪词,越来越不像是一个读书人了。
她忍不住笑了。
牵娘娘说,等上了轿,看你还笑。
她问:要是上轿,万一哭不出来,怎么办呢?牵娘娘说,你放心,一定哭得出来。要不要放点辣椒粉什么的?她听说演员拍戏时,眼泪到不了位,就这样做。牵娘娘也笑了:你这孩子。
锣鼓终于扯心扯肺地敲打起来了,屋里屋外哭得一片模糊。娘,姐,姑,婶,姨,还有老一辈的,奶,姑奶,姨奶,一个个泪水纵横。爹爹躲在灶下,也哭。因为按照习俗,女儿出嫁时,做父亲的不能照面。新娘蒙着红盖头,手拉着布角,由一个族兄抱上了“轿”一一其实是一辆扎了红花贴了双喜字的自行车。
热心而好奇的人跟在“轿”后面,想听她是怎么哭的。但跟随了很远,也听了很久,却见红盖头下一点动静都没有。她们很纳闷。在她们的预想中,她的哭应该像雨后林中饱满的水滴,轻轻一碰便会洒满一地。她的哭嫁应该有着辣椒一般的热烈和歌声一般的悠扬。像六月天的暴雨一样没头没脑。真是一个孩子啊,居然不知道哭嫁的重要性。有的女娃子,这时哭不出来就是干嚎也要嚎两声的,就是万分愿意出嫁也要把身子扭两扭。她们摇摇头,叹了口气。
后来上了大路,新郎抱她上了车,和她并排坐在一起。透过她带着女人体香的呼吸,他惊讶地发现她其实一直在啜泣。泪水打湿了脸颊,打湿了衣襟,打湿了红盖头。她的面容浸泡在湿润的红光之中,鲜亮丰满,哀艳动人。
是啊,她已经是一个女人了。她仿佛一下子懂得了大音稀声的道理。懂得了女性的滋润是无声的。
之后,她怀孕,生子,和丈夫小别、重逢、赌气、又和好如初,和公婆处理关系,和小姑团结友爱,为那份并不稳定的工作而尽力,为孩子的营养和健康而操心,还有农事的播种、栽苗、插秧、除草、杀虫、收割。十多年过去了,她已经是一个三十岁出头的妇人。她的脸还是那么的饱满,她的腰肢还那么的柔软有力,她的泪腺还是那么的敏感丰富。她丈夫说这真是一个奇迹。她已渐渐脱离了繁重的农事,在小镇上做些生意,相夫教子。同时,她也在丈夫的引导下读些书,文学,自然科学。丈夫说她的感受力很好。时间长了,她倒真有些丢不开这些书了。书有一种光辉,使她的生活从平庸中上升。每当她在激烈的情感里流泪啜泣的时候,丈夫便走过来,把她抱在怀里,轻轻地握她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