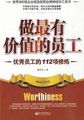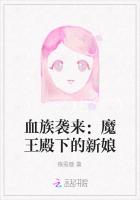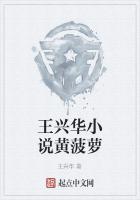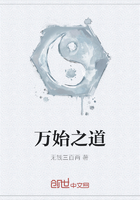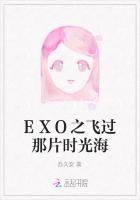首先是汉景帝的同胞弟弟梁王刘武和周亚夫结下梁子。在周亚夫主持平叛七国之乱时,他把主力部队开到河南一带,而吴、楚联军正在猛力攻打梁王刘武的人马,当时,梁王向汉景帝求援,景帝让周亚夫驰援,可周亚夫认为吴、楚联军锋头正健,不如先避其锋芒而谋后动,只派骑兵阻断了联军的粮道,迫其有后顾之忧,只得返过头来找汉军主力作战,而周亚夫以逸待劳,养精蓄锐,一举攻破了吴、楚联军的防线,大败其主力而获全胜,但此举使梁王大为不满。
周亚夫只知谋国,不知谋身,终使梁王怨恨。因此,梁王每逢入朝,都会寻找一切可以挫伤周亚夫的机会。时间一长,假话也成真话,何况梁王只是对事实的理解不合实际而已。
景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53年),立长子刘荣为皇太子,但因其母栗姬逐渐失宠,景帝就想废掉太子,另立王皇后之子刘彻为太子。然而在封建社会废长立幼一般是不允许的。周亚夫初登相位,认为太子并无过失,随意废立,会引起混乱。周亚夫秉性直爽,不懂劝谏艺术,为此事与景帝发生了争执。后来景帝说废立太子是家事,不需外人插手,周亚夫这才无奈罢休。周亚夫的劝谏不仅未能说服景帝,反而使景帝觉得他太过张狂,太蔑视皇帝,深为恼怒。
公元前147年,即汉景帝中元三年,窦太后要景帝封王皇后的哥哥王信为侯,封外戚为侯是违反祖制的,为此,景帝找周亚夫商讨此事,果然,秉性耿直的周亚夫以高祖皇帝刘邦的“非刘氏而王,非有功而侯,天下共击之”来回击汉景帝,只因周亚夫据之有典,言之有故,让景帝也没有理由发火,以一国之尊,在下属面前碰了一鼻子灰,景帝对周亚夫的成见更深了。周亚夫此举不仅失宠于景帝,又得罪了王信,梁王和王信来往很密切,又都视周亚夫为仇人,皇帝身边两位最有影响力的人,联手内外夹攻,一起来构陷周亚夫。
此事过后不久,匈奴部酋有六人来降,汉景帝认为这是他文治武功的结果,心中大为高兴,便决定将这几人封为列侯,但其中一人是汉朝叛将的后人,周亚夫认为他的先人背汉而降匈奴,如今他又背匈奴而归汉,是反复小人,不可封为列侯,景帝认为从大局出发,便断然拒绝周亚夫的建议,将六人都封了侯。周亚夫屡屡碰壁,心结难开,于是上书请求告老还乡,是帝依允。
由于周亚夫乃一代名将,颇有名望,汉景帝对他心存猜忌,经常以各种方法试探周亚夫。
一天,汉景帝以赐食为名,召周亚夫进宫,想摸一下他的底,周亚夫虽已免官,尚居都中,见召即到。周亚夫趋入宫中,见景帝兀自独坐在那里,行了拜谒之礼,景帝跟他随便说了几句话,就命摆席。
景帝让周亚夫一起吃饭,周亚夫也不好推辞。只是席间并无他人,只有一君一臣,周亚夫就感到有些慌恐,等他到了席前,发现自己面前只有一只酒杯,并无筷子,菜肴又只是一整块大肉,无法进食。周亚夫觉得这是景帝在戏弄他,忍不住地就想发火。转头看见了主席官,便对他说:“请拿双筷子来!”主席官早受了景帝的嘱咐,装聋作哑,站着不动。
耿直的周亚夫并没有多想,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这是景帝的计谋。这时景帝忽然插话道:“这还未满君意吗?”
周亚夫一听,又愧又恨,被迫起座下跪,脱下帽子谢罪。
几天之后,突然有人来通知周亚夫,说有人把他告了,让他入廷对质,周亚夫一听就知道大事不妙,他的大限已经来了。果然,对周亚夫心存忌恨的汉景帝,以一件小事诬周亚夫谋反,情知百口莫辩的周亚夫,只好长叹一口气,就此罢休。汉景帝派人把周亚夫押到大理寺审讯,查来查去事情没有真正的原委,但汉景帝一心要置周亚夫以死地,大理寺卿虽无话可说,但又知皇上欲置其于死地,必须找个借口,于是发出了石破天惊之判词:“你就是不想在地上谋反,也想死了以后在地下谋反!”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周亚夫被关入狱中后,他五日不食,绝食而死。一代名将竟落此下场。过于耿直,过于坚持原则而不需时度势,察颜观色,就必然会触动他人心中的痛处,造成彼此间的尴尬。这样的人很难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生存。
直言敢谏,行正义改邪恶
自古敢谏必敢犯,这种性格的人不多,他们都正直无私。古今第一谏臣,魏征可算其一,如果说魏征敢谏是他遇上了英明之主唐太宗,那比干谏纣又当怎论呢?后者明知所侍之君昏庸残暴也谏了。
“谏”为何意?“谏”是规劝、行义事、改邪恶。从做人的原则来讲,“进谏”与“纳谏”应该是一种美德,无论如何,听得进别人的忠意劝告总比一意孤行好得多。
但进谏也要看对象,如果是英明君主还能纳谏,如果是昏庸之辈,轻则丢官,重则家破人亡。但有些谏臣生来就直言敢谏,天威龙颜在他们眼中大不过原则、大不过法度。
唐代的魏征出身于书香世家,他胸怀大志,总想干出一番事业来,于是就刻苦读书,勤奋学习,在学问和政治才干方面打下良好基础。当时正值隋炀帝荒淫无道,天下英雄豪杰纷纷起兵反隋,魏征先是参加了元宝藏的起义军,但又觉得看不清楚天下大势,心中茫然,不知所从,便出家当了道士,以避一时之乱。
后来,魏征出山,在太子李建成手下做一个管理图书经籍的小官,叫做洗马。在这一阶段,魏征虽有文名,实际上并未发生多大的作用,只是给李建成提过一个建议,让他带兵去攻打不堪一击的刘黑闼,既可建立军功,又可暗结豪杰,太子听信了他的建议,结果取得了圆满成功。
李唐政权把握了天下大势之后,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了哥哥太子李建成、弟弟齐王李元吉,自己当了太子。李世民也知道魏征既是李建成的心腹,又非等闲人物,就立刻召见了他。责问他说:“你为什么挑拨我们兄弟间的关系呢?”魏征没有巧言机辩,而是据理回答,他说:“各为其主。如果太子早听信了我的话,就不会有今天的下场,我忠于李建成,又有什么错呢?管仲不是还射中齐桓公的带钩吗?”
李世民听他说得既坦率又有理,尤其他举出了管仲射小白的历史故事,自己不能显得没有气度,就赦免了他,并封他为主簿,至此魏征结束了不得其主的生涯。
李世民即位为皇帝不久,就提升魏征为谏议大夫,这真是得其所哉!唐太宗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成就了魏征的名声,魏征敢于犯颜直谏,促成了唐太宗善于纳谏的性格,魏征的进谏和唐太宗的纳谏同样名垂青史,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谏议大夫的职责是专门向皇帝提意见,这是个很奇特的官,它既无足轻重,又重要无比;它既无尺寸之柄,但又权力很大,而这一切都取决于谏议大夫的意见,皇帝听还是不听。唐太宗任命魏征为谏议大夫,表现了唐太宗对他的才能的认可和对他本人的信任和尊重,后来又把他提升为尚书丞,就更能使他随侍左右,时时处处提醒规劝皇帝了。
在治理国家的方略上,魏征主张轻徭簿赋,休养生息。魏征认为,隋朝灭亡的教训在于扰民太多,国家赋税极重,徭役繁多,以至民不聊生。“静之则安,动之则乱”。因此,在整个贞观年间,朝廷的赋税和徭役不算太重,这是贞观年间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基本保障之一。
在治理国家的整体方略上,尤其是在大乱之后拨乱反正,魏征主张宜快不宜慢,宜急不宜缓。
在执法方面,魏征主张宽缓明确。他坚决反对像秦朝那样实行严刑酷法,把人民当作鱼肉来宰割,但同时又坚决主张明正典刑,反对徇私枉法。
魏征还主张取信于民,不要朝令夕改,让人无所适从。
明知天威不可犯,但魏征却偏犯,这是由其耿介刚直的个性所决定。如果说考虑到天下长治久安的大计可谏,那皇帝个人的起居生活应该属私事了吧,但在魏征眼里,皇帝的一举一动都关系着社稷的安危,黎民的祸福,所以他的谏议涉及了许多方面。
在使用人才方面,魏征主张在不同的时期要对德才有所取舍。他对唐太宗说:“在天下未定之时,用人的标准是重视才能,不可过多地考虑他的品德操行;天下平定以后,则非德才兼备不可用。”在魏征的影响下,唐太宗“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有一次,他还主动地对魏征说:“选择任用官吏,是不能轻率马虎的。用一个君子,那么君子就会纷纷而来;用一个小人,那么小人也就会钻营投奔而来。”
尤其在个人享乐方面,魏征紧紧跟踪唐太宗,经常犯颜直谏,不让他大兴土木。有一次,唐太宗想去南山打猎,车马都准备好了,最后还是没敢去。魏征问他为什么没有出去。唐太宗说:“我起初是想去打猎,可又怕你责备,就不敢出去了。”
贞观十二年(638%)年,公卿大臣都请太宗登泰山封禅,只有魏征认为现在举行封禅仪式不妥。太宗对魏征说:“我希望您把自己的想法都说出来。难道是我的功劳不高吗?是我的德行不敦厚吗?是国家还没有平定吗?是远方的异族人不仰慕大唐的高义吗?是吉祥尚未降临吗?
是农业没有丰收吗?为什么我不能封泰山呢?”魏征说:
“陛下的功劳虽然是极高的,可是百姓并未感受到陛下的恩惠;陛下的德行虽然是敦厚的,但陛下的德政尚未传及全国各地;全国虽然安定,但并不能为兴办事业提供足够的资财;远方的部族仰慕陛下的高义,但朝廷却没有能力满足他们的要求;吉祥的征兆虽然出现,但法网仍然密集;虽然连续几年农业丰收,但粮仓仍然空虚,这是我认为目前不宜封禅的原因。我不能用遥远的东西打比方,姑且用人作比喻。现在有个人患了十年的重病,到将要治愈时,已经瘦得皮包着骨头,马上让他扛起一石米,每天走一百里路,他一定不可能做到。隋朝天下大乱已经不止十年,陛下平定了全国的混乱局面,虽然现在天下已经平定,但国库尚不充实,在如此情况之下,向天地报告事业已经成功,我暗自对如此作法持怀疑态度。况且陛下若东封泰山,各国的使者都要聚集到那里,周边各国人,无不奔走相告。现在西起伊水、洛水流域,东到泰山、东海、荒海滩、沼泽地,苍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之声不闻,道路萧条,行进艰难,岂可招来域外部族之人,把我国的虚弱状况展示他们?即使我们用尽财物赏赐他们,也不能满足远方之人的愿望;即使连续两年免除徭役,也不能抵偿百姓的劳苦。如果遇到水旱灾害,风雨之变,服役的民夫横加议论,即使后悔,也无法挽回损失。岂止是我一个人恳请陛下免去封禅之事?成千上万的百姓都乞望陛下恩准。”太宗听了魏征的一番话,也深感国家虽然初步安定,但生产远未恢复,国库仍然空虚,如此严峻的形势,有何功德以告慰天地?遂将封禅泰山之事搁置了下来。
最著名的是魏征关于忠臣和良臣的辩论。有一次,唐太宗听信了其他人的谗言,批评魏征包庇自己的亲戚,经魏征辩论,唐太宗知道自己错了。魏征趁机说道:“我希望陛下让我做一个良臣,不要让我做一个忠臣。”唐太宗听后很吃惊,就问:“难道良臣和忠臣有什么区别么?”
魏征说:“区别很大。良臣身享美名。君主也得到好声誉,子孙相传,流传千古;忠臣得罪被杀,君主得到的是一个昏庸的恶名,国破家亡,忠臣得到的只是一个空名。”
唐大宗听了以后,十分感动,他连声称赞魏征的话很对,并送给了他好绢五百匹。
当然,唐太宗是人不是神,对魏征的劝谏并不是每一次都能愉快地接受的,有时是既恨又怕,甚至还想干脆杀掉他!有一次,唐太宗得到了一只好的鹞鹰,自己非常喜欢,就把他驾在手臂上玩。远远地看到魏征来了,十分紧张,赶紧把鹞鹰捂在怀里,怕魏征看到或是听到。其实呢,魏征早就看到了,他为了不让唐太宗贪恋声色犬马,就故意没完没了地禀奏公事,估摸着鹞鹰差不多憋死了,他才离开。等魏征走了,唐太宗赶忙从怀中取出鹞鹰,拿起一看,早已闷死了,这使他觉得十分窝火又说不出来。
魏征年老病重,太宗遣医送药,使者相望于道路,来往不绝,并和太子一起去他家探望,把衡山公主许配给他的儿子魏叔玉。魏征去世后,太宗命朝中九品以上的官员都去吊唁,悼文刻于石上。太宗对他思念不已,他跟左右的大臣说了如下的名言:“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殁,朕亡一镜矣!”这恐怕是历代大臣中所享受的最大的殊荣了!
人言“忠臣不事二主,好女不嫁二夫”。以这种观点来看,魏征自然不是“忠臣”,然而,他却是千古良臣!
因为在他心目中有一个准则就是上安君国,下报黎民,正直耿介的个性让他“大忠”而不是“小怨”。孟子说:
“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就是说忠国不是忠君,忠民不是忠人。魏征之忠,实是性格所致矣!
精细敏锐型性格的做人
拥有这种性格的人往往想像力极为丰富,具有创造性思维和敏锐的洞察力。他们的应变能力超人一等,善于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有认准目标决不放弃的韧性,最终取得竞争的胜利。因此在做人方面常表现出稳定而成熟的神形。安稳开朗,性格也相对豁达,能面对现实,忍耐力也较强。行事、言谈方面也较谨慎,思考周全、三思而后行,他们往往虑人先虑事,进可攻,退可守,始终思考得尽善尽美,这种人责任心较强,办事多精明,如以大事相托,可万无一失。
当然任何一种性格有缺点也有优点,精细敏锐的人也不例外。他们心思过于缜密,事事前思后想,不敢冒险,容易失去很多机会。这类人警惕性太高,对所有人都不太信任,持怀疑态度,要么事必亲躬,要么有猜忌心理,容易封闭自己。
完美做人,难成完美绩业
诸葛亮是中华大地老幼皆知的人物,上通天文,下晓地理,饱读诗书,奇谋备出,又宽厚仁爱,终于助刘备建立蜀国,三分天下。诸葛亮无疑是智慧的化身,正是他这种一叶知秋,精细敏锐的性格塑造了他传奇的一生。
东汉末年,诸侯混战,诸葛亮在襄阳城西二十多里的一个叫隆中的地方隐居。所谓“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在隆中,他努力学习儒家经典与前代史书,并博览诸子百家,他读书“观其大略”,最注意的是总结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寻找治国治民的有效方法,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观点,并留意全国形势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政治抱负。诸葛亮读书学习之余也没忘了宣传自身,因为他胸怀大志,想有一番作为,于是,在隆中“隐居”的十年里,他或是通过交往,或是通过亲戚关系,与襄阳一带的名门大姓有了往来,尤其是和各个名士的密切交往增加了自己的学识,扩大了政治影响,使他逐渐成为荆州地区名士中的知名人物。
汉室后裔刘备一心渴望在乱世中建立功业,为此他遍寻人才。此时,颖川名士徐庶向他推荐诸葛亮。刘备比诸葛亮大20岁,但他相信诸葛亮是位了不起的人才,就带着关羽、张飞亲自到隆中去请诸葛亮出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