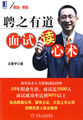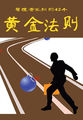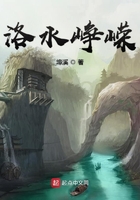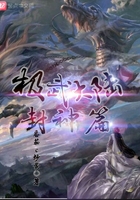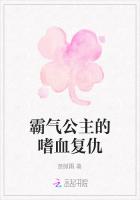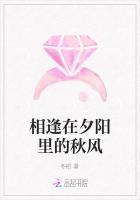慈禧是清朝最后一个拥有实权的统治者,影响并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的进程。
慈禧进宫之初是一个小小的贵人,但她不甘寂寞,用心等待、想方设法接近皇帝,同时又颇费心机地笼络周围得力的小太监,用为心腹。渐渐地,梳头房的小太监安德海和她熟悉起来。“奴随主贵”,他使出浑身的解数来博取慈禧的欢心,同时也想方设法替主子打听皇上的行踪嗜好,为贵人创造沐浴龙恩的时机。不久,还真让主仆俩逮到一次机会。
这一天,咸丰皇帝带着几个贴身太监到御花园中散心,忽然,一阵悠扬悦耳的江南小调若隐若现,歌声婉转清柔,如同南国扑面而来的春风,足以使人心旌摇荡。咸丰帝不禁圣心欢悦,循歌追去。不用说,唱歌的人正是入宫不久的兰贵人。兰贵人自幼随父亲在江南,熟悉南国的丝竹音韵,加上她颇有心计,便精心安排了这次邂逅相遇。果然,这次得幸后,兰贵人的身影便牢牢嵌在年轻皇帝的心中。
没过多久,她为咸丰生了个儿子——载淳。母以子贵,再加上慈禧的用心周密,短短六年间,她由一个普通秀女连升数级,成为后宫中地位仅次于皇后的贵妃。
工于心计的慈禧不满足于每天后宫闲逛,就把目标转向了国家大事。
咸丰皇帝的颓废消沉,为那拉氏干预朝政提供了契机。此时是懿贵妃恩宠独邀的一段时间,那拉氏原聪慧过人,对政治有着超乎常人的敏感。最初,她见咸丰皇帝为应付奏章而忙得焦头烂额,有心体恤皇上,便替他在大臣们的奏章上圈点,也好让皇上有选择地看,皇上不但不怪,还颇为赞赏,渐渐地,她胆子越来越大,开始对朝臣的奏章签署意见,评断是非长短,甚至在咸丰帝遇到难以判断的大事时也参与决策,提供意见。
没多久,英法联军进北京,咸丰病死热河。6岁的载淳继位,由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输弼幼帝“赞襄一切政务”。赐给皇后钮祜禄氏和载淳“御赏”印和“同道堂”印各一枚,作为发布谕旨钤用,那拉氏以皇帝生母身份代行小皇帝的职权。当时人称辅命大臣与两宫太后、皇太子间互相牵制的局面为“垂帝辅政,盖兼有之”。
对于这种安排,慈禧且喜且惊。喜的是自己手中掌握着“同道堂”印鉴和皇儿载淳,又有皇太后的封号,不致于立即招致杀身之祸;惊的是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八大臣凭借先帝遗诏辅政,随时会对自己孤儿寡母发难。尤其是肃顺一向专横霸道,看不起女人从政,对那拉氏的限制、反对最多,今后怕是羽翼更强,难以对付。此时慈禧野心急剧膨胀。她不甘心眼睁睁地看着肃顺成为“多尔衮第二”,而自己成为别人刀下任意宰割的羔羊。她要孤注一掷,通过政变来铲除政治道路上的一切障碍,把大清国的政权牢牢抓到自己手里,热河行宫的一片悲戚之声中,隐约透露着点点杀气。这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野心颇大,又诡计多端的慈禧使出千般手段维护自己的利益。
慈禧最终争取到了慈安太后和恭亲王的支持,发动北京政变,除掉了以肃顺为首的八位大臣,排除异己。她又露出阴险、残酷的个性,使反对她的人一个个消失。
经历了北京政变之后,慈禧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做人上都明显成熟起来。她争取到垂帘听政,无疑将国家大权的一半抓到了手中,另一半,还得暂时留在恭亲王手中,而狡猾的慈禧只是借恭亲王之手存放一下。
慈禧并不在意比她名份还高的东宫太后慈安和她共同执政。慈安太后性情温顺、善良,为人厚道,对政治没有太多主见和热情,对慈禧的举动也听之任之,一向把慈禧当作自己的姐妹看待,所以两宫太后在执政初期相当和睦,慈禧诸事还要依赖东太后的尊贵身份。
对恭亲王,慈禧更加倚重。恭亲王在洋人当中声望良好,又助慈禧完成政变,在朝中也如日中天。慈禧内倚太后声望,外借精干小叔的鼎力协助,开始实现个人政治抱负。
两宫太后听政之初,朝廷内外并非人心顺服,不少官员心存观望,要看一看这两位年轻寡居太后的手段。此时,农民起义峰烟四起,腐败的朝庭大员却一味退却,为震慑百官,树立威德,慈禧下令将两江总督何桂清革去从一品官,就地立斩,以戒军心;随后,她又下令将平日里跋扈骄蹇、藐视朝廷的兵部左侍郎、护军统领胜保捉拿进京,以“冒功侵饷、渔色害民”的罪名处死。斩了何、胜两人之后,的确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朝中大臣看到西太后的威仪,再也无人敢怠慢朝事,统治秩序得以初步恢复。此时,权欲熏心的慈禧把目光又放回了恭亲王身上。
当初她重用恭亲王,是为了替自己铺平登上权力宝座的道路,一旦实现了这一人生目标,她便不能容忍别人染指她的势力范围。而两人间的冲突和矛盾,更使慈禧的决心有增无减。
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三月,御史蔡寿祺参劾恭亲王贪污恣肆,兼有慈禧宠信的太监安德海从旁谗毁,触发了慈禧的新仇旧恨,于是亲拟谕旨,称恭亲王“从议政以来,妄自尊大,率多狂傲,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看朕冲龄,诸多挟制,往往谙施离间,不可细问。
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多取巧,满口胡谈乱道……”据此,“恭亲王著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轻而易举,这个惟一能够挟制慈禧专权独载的人就被踢到了一边。
慈禧对恭亲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整治,使朝廷中再无一人敢单独站出来同西太后抗衡,她成了一个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集权女性。这一年,慈禧31岁。
狡诈和权力集中在慈禧身上,使她越发专断独行,即使是对自己的儿子也不例外。同治帝17岁时,到了该成婚的年龄,在选婚上,母子二人意见发生了摩擦,慈禧选了富察氏,而同治却自己看中了举止大方、雍容华贵的阿鲁特氏,到了册封那天,同治帝还是将象征皇后身份的信物羊脂玉如意交给了阿鲁特氏。婚后,同治帝与皇后的感情很好,两人相敬如宾,常互相答和诗词为趣。皇后阿鲁特氏生活严谨,相夫持重,在同治眼里和后宫中有较高威信。看到儿子媳妇夫唱妇随,慈禧太后怒从心起。她无故责难阿鲁特氏,还背地里挑拨皇帝与皇后的关系。慈禧甚至公开告诫同治帝少与皇后亲昵,应专宠慧妃,这使婆媳关系变得非常紧张。这种情形下,同治帝与皇后见面,常有西太后派出的小太监在暗中监视,使得小夫妻俩的来往及温存大受限制。同治帝反感母亲对他私生活的粗暴干涉,便采取消极抵抗方法,负气一个人独居乾清宫,后妃们一概不去召幸,只与身边的太监们相伴取乐。这就种下了他日后行为不轨、梅毒缠身、青年早亡的悲剧祸根。
同治的梅毒病发时,来势汹汹。慈禧出于顾及名誉的考虑,让太医按天花之症诊治。十二月初四,同治病情有所稳定,适逢皇后阿鲁特氏前来探视,夫妻相见,不免泪眼朦胧,拉着手说些体己话。阿鲁特氏见皇上病体沉重,联想起自己入宫以来屡受婆婆的刁难,不禁痛哭失声,向皇帝诉说所受的种种委屈。两个人正在窃窃私语时,不料西太后亦蹑足潜踪来到窗外,偷听到皇后的哭诉。她怒火中烧。冲进宫来,揪住皇后阿鲁特氏就是一掌。皇后受辱后,为求自保,朗声抗辩道:“我乃堂堂皇后,系由大清门抬入宫中的,你不能打我。”这句话正好触动了慈禧当初地位卑贱的心事。她大为恼火,索性撒泼耍刁,令宫人传杖,要对阿鲁特氏施以杖刑。这边婆媳打得不可开交,急坏了躺在病床上的同治皇帝。气急之下,他一句话都未喊出声,便昏厥过去。当晚,同治帝病情骤然加重,延捱一日,便病死在床。
同治死后两个半月,皇后阿鲁特氏也绝食身亡。佳儿佳妇,就在慈禧的折磨下死去了。
慈禧用卑鄙、阴险的手段搬掉了一个个对手,然而她还不满足,又把魔爪伸向了与之共同执政的东太后慈安。
慈安的存在,对慈禧根本算不上威胁,但终究慈安与自己平起平坐,抢了一份光芒,更重要的是慈安手上还一份决定自己命运的诏书。
慈禧骄蛮专擅的行为,慈安有所耳闻。为了规劝这个任性的妹妹,她请出了先帝咸丰留下的遗诏。咸丰预见到慈禧将来掌权后霸道成性,难以制服,故留下遗诏一封,称:“西宫援母以子贵之仪,不得不并尊为太后。然其人绝非可倚信者。即不有事,汝亦当专次。彼果安分无过,当始终曲全恩礼。若其失行彰著,汝可召集廷臣,将朕此旨宣示,立即赐死,以杜后患。”
一天,慈安派人把慈禧请到自己宫中,递给她一份藏在锦盒中的诏书,对慈禧说:“自从先帝去世后,我们姐妹二人携手辅佐幼主,维护大清基业,不敢有半点差池。
如今你我手中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为人处事可要三思而后行呀!这个锦盒中的诏书本是先帝文宗留给我的,我看咱俩共事二十余年,应该彼此信任,留着这个诏书也没用啦。今天我就当着你的面烧毁它,希望妹妹别辜负先帝对咱们的厚望!”说完,慈安太后缓缓地把诏书取回,放在火上烧掉了,经历了这一幕,慈禧心中比当年北京政变时还要紧张。遗嘱在一日,套在头上的紧箍就束缚一日,慈安太后的善良,无疑帮了她大忙。于是慈禧连忙装出十分痛心与惭愧的样子,涕泪横流,感激不已。慈安劝慰她一番,派人送她回宫。
慈禧觉得慈安一日不除,则后患无穷,于是派人在膳食中下了毒,把慈安毒死了。慈安一死,宫中再无可与慈禧并驾齐驱享受特权之人,她的统治开始进入极度专制转而衰败的时期。
慈禧镇压了维新变法运动以后,与光绪皇帝间的矛盾发展到水火难容的地步。她辛苦“培养”了20年的皇帝,竟公开违忤她的旨意,慈禧对此感到异常震怒。按照她的想法,应该立即废除光绪,另立一个听话的小皇帝。但她一贯我行我素,引起了洋人不满。慈禧接受了荣禄的建议,于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立端郡王载漪之子为大阿哥,作为合法的皇位继承人,将其正式接入宫中抚养。
此时,中华大地上又兴起了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起自山东,势力迅速蔓延至直隶、京津一带。他们在各地设立“拳场”,极度不满清朝政府统治,仇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胡作非为,多次指挥教民焚烧教堂。以此为借口,英法俄等国公使相互纠结,联名照会总署,声称“各国之兵现已决计入京,我等无力阻止,深为贵国惋惜”,遂爆发了八国联军侵华的战争。统治集团内部围绕着对义和团是剿还是抚,对帝国主义是战还是和,斗争相当激烈,慈禧连续四次召开御前会议,以载漪、刚毅为代表的顽固派和以奕勖、张之洞等人为代表的抗战派展开了激烈论争。情急中,端王载漪精心炮制了一个所谓“太后训政立即结束,将归政于光绪皇帝”的照会,促使慈禧决心利用义和团势力来抵抗洋人的侵略。
当然此举她也别有用心。西方列强一再要求归政于光绪,引起了她极大的愤恨;另一方面,义和团声势浩大,威胁清朝的统治,她想利用这个机会,以求“一石两鸟”,坐收鱼翁之利,其阴险狡诈的性格再次得到发挥。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六月二十一日,慈禧以光绪的名义发布宣战诏书,正式对八国联军开战。慈禧称义和团为“义民”。并令各省督抚,将他们“招集成团,藉御外侮”,由攻剿改为招抚,寄希望于用义和团的力量打败八国联军的武力入侵。此时的清廷,既无御敌的武装设备,也没有御敌的坚决斗志,宣战仅四天,慈禧便派荣禄前往各国使馆慰问,表达议和的愿望。随着战事日益激烈,慈禧一方面继续声称“现在中外业经开战,断无即行议和之势”,要求各省督抚将军,“务将和之一字先行扫除于胸中”,认真布置守战事宜。另一方面,她却分别致书于俄英日三国君主,请他们出面负责“排解纠纷”。最初,她拿出白银十万两,发给在天津浴血奋战的义和团以示奖励;没有多久,她又分别致国书于德皇和美法两国总统,请他们“设法维持,执牛耳以挽回时局”,同时令荣禄停止攻打使馆区,派总理衙门官员给各使馆送去西瓜、面粉、蔬菜、水果、冰块等物以示安慰。在慈禧投降主义思想指导下,清军不堪一击,义和团赤手空拳也难抵挡洋枪洋炮的攻击。7月中旬,八国联军的部队已攻近北京城。
7月20日,北京陷落。万般无奈,慈禧带领光绪帝、后妃和大阿哥及王公大臣十二三人,在二千余名兵勇的护卫下仓皇出逃,经昌平,出居庸关,进入山西太原,后转道至西安。
慈禧离京西逃的同时,委派李鸿章和奕勖等人为全权代表,负责与八国联军谈判媾和,媾和的前提不外乎是加倍的出卖国家主权。
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七月二十五日,李鸿章在慈禧授意下,与各列强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最不平等的一个条约——《辛丑条约》。
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在西安避祸一年多的慈禧太后看到外患平定,决定摆驾回京。一路上,她仍不忘大摆皇太后威风,派人整修道路,张灯结彩。回京途中,她下令革去大阿哥的名号,放逐出宫;又赐死多名在这次反帝斗争中积极抗战的大臣,以取悦洋人;严令各地镇压义和团运动的余波。
清朝此时已支离破碎,破败不堪,正是慈禧本人将大清送上了毁灭之路。
大凡残暴、贪婪的统治者都是愚昧的,她们生前追求富丽堂皇的生活,死后也幻想到另一个世界继续过穷奢极欲的生活,慈禧也不例外。她的墓穴修建,前后历时二十余年,且一度因建得不合她的口味而拆掉重修。新建的陵墓,内部工艺高超,用料讲究,极其华贵。慈禧从去世到下葬,共花了近一年的时间,耗费白银127万两。她的陪葬品数量之多、质量之精,难以用语言描述。民国年间,军阀孙殿英挥兵盗掘了慈禧的陵墓,盗得珍宝价值连城,将西太后墓地践踏得一塌糊涂,连尸首都未得保全,这种结局,恐怕是富贵一生、跋扈一生的慈禧万万没有预料到的。
工于心计伴随慈禧的一生,为了使太后的宝座坐得安安稳稳,她排除异己,利用各种可利用之人,甚至不惜卖国求荣。作为一国的实际统治者,她没有使国富民强,反而适得其反。作为一个母亲,她干涉儿子婚姻,粗暴无礼,独断专行,造成了诸多人的不幸。而她自己,虽万人之上,众星捧月,也难免流离失所,几度逃亡……
狡诈近于奸,玩弄两面派手段
吴三桂是明清之际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他手握重兵却引清入关,遭到无数人的唾骂。也有人说他审时度势,情非得已,加快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然而史实如何,只能说明历史如何前进,人的性格也是其中不可估量的因素,也是人们常常忽略的,吴三桂的性格改写着历史,也改写着他自己的做人。
吴三桂祖籍江南,后流寓辽东。父亲吴襄是武进士,因守辽东有功,被封为总兵。正所谓将门无犬子,吴三桂武艺高强,智勇双全。又兼有南方人的俊秀,神清气爽,玉树临风。他长得不高却匀称,天庭饱满,瞻视顾盼,尊严若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