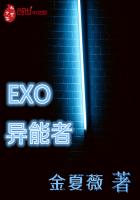小时候,最喜欢做梦,而梦的主题归纳起来似乎也只有两个:捡鸡蛋和找厕所。梦见捡鸡蛋自然是因为饥饿,饥饿是孩子们最惧怕的,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乡下又是必然的,所以,为了应对饥饿,孩子们往往都很自觉,很勤劳,也很团结,比如夏天顶着烈日光着脚四处捡拾废铜烂铁或玻璃瓶,卖给废品收购站,换回几毛几角,再换成大饼或糖果,即使谁不小心被碎玻璃或尖石子划破了脚掌,也照样忍着痛低着头继续寻找;再比如几个人一起分工合作,有计划有组织地偷人家院子里的鸡蛋,搞得鸡飞狗跳,骂声四起,有时不巧被人家抓住,也一定守口如瓶决不交代“同伙”。晚上累了继续做梦,在梦里是不需要再偷的,鸡蛋就躺在田埂上,白晃晃的,圆滚滚的,捡起来,握在手心里,自己能把自己笑醒。而找厕所就惨了,它注定是一件让人焦虑、难堪的丑事,往往是因为晚上喝多了稀粥或是多吃了几瓣西瓜,刚睡着就开始漫山遍野地寻找解决问题的地方,而四处好像都有人,于是只好翻山越岭地找啊找,心急如焚,终于找到一个僻静之处,稀里哗啦,好一阵畅快淋漓,然后突然就觉得屁股底下凉飕飕的,心下一惊,梦便醒了,大错已经铸成,悔之晚矣,即使忍着潮湿和刺鼻的气味用身体焐干,还是少不了天亮后母亲的一顿责备的。整个儿童期就在这断断续续的梦境中悄然过去,只有极个别的会将这样的梦一直延续至青少年吧。
现在想想,其实这两件事都跟身体密切相关,前者是因为明明白白的饥饿,而后者则是因为潜在的无法克制的欲望,而且都是在现实中无法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满足,只能迂回到梦境中才能达成,而即使有悖于道德或年龄,那一瞬间的快感,却是那么真实,又是那么诱人。多少年以后,做了无数的梦,而能够回想起来依然充满快慰的却还是那样的梦。梦是不会重复的,正如那些一去不复返的时光,正如那些离我而去只能在梦中与我相见的亲人,而我可能在这中间也早已成为别人梦中的风景吧。一天半夜,妻子忽然醒来,坐在床上,不声不语,突然又紧紧抱住我,向我描绘她刚做的一个噩梦,她说梦到我有了外遇,不要她了,她痛哭流涕,伤心欲绝,在梦里哭着哭着就哭醒了。我心里觉得有些好笑,可搂着她,却笑不出来,我只能为梦中我的“外遇”向她道歉,为她的担心和流泪而感动。
转念一想,其实一个个梦又何尝不是超越现实生活的一次次“外遇”?从懵懂的青春期开始,那些暧昧的梦总缠绕着成长中的身体,我甚至能在梦里听见自己压抑的呻吟,听见骨骼抽穗的声音,我无端地陷人醒来的回味、欣喜、羞愧和自责之中,就好像自己的隐私被别人窥探了似的,害怕夜晚,害怕邪恶的梦随时随地像幽灵般冒出来。后来“遇到”精神病医生西格蒙德?弗洛伊德((FreudSigmund,1856—1939),他在《梦的解析》(1900年)中说梦是一种精神活动,“其动机常常是一个寻求满足的愿望”,梦是因愿望而起,它的内容是“愿望的达成”,我终于明白自己为何当时以及此后都恋恋不忘那些荒诞不经的梦,正是因为在愿望的满足中获得了超乎寻常的感受,那感受一点也不比“外遇”逊色。成年后的梦似乎更透露了不少违反道德的愿望,虽然可能潜意识使它们以改头换面的形式冒出来,但每一个梦境背后其实都暗藏着一种隐喻或象征,无论如何伪装,梦终归会泄露内心的某些真相,只不过在生理的萌发之上似乎更多了精神的启蒙,正好似那些热衷于外遇(外遇=身体的外求精神的遭遇?)的男男女女,无论如何小心,总会让自己沉进无法自拔的灵肉交战的深渊。
然而,即使事先预料到那深不可测的深渊,依然有成群结队的现代男女心甘情愿地沉沦,饮鸩止渴,即使牺牲也是毫不畏惧的。我知晓许多有关“外遇”的故事,大都以身体的复活开始,而以精神的受难结束,无论在影视剧或文学作品里,还是在活生生的现实世界里,每一个都仿佛精心虚构的小说,情节平淡或是生动,都映照出现代人空虚又浮华的内心。比如我所知道的一对自由恋爱而结婚的男女,相互爱得深沉,女人舍弃稳定的高校教师的职业,到男人工作的城市努力打拼,风雨里奔波,日渐憔悴,她说她就是想挣更多的钱,给男人换一辆新的汽车,然而没有等到她的这个心愿实现,另一个更年轻更漂亮的女人就替换了她的位置,男人和女人很安静地离了婚,此后女人便仿佛从城市中消失了,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关心她下落不明的生活,据说有人在另一个毗邻的城市曾见过一个很像她的女人,疯疯癫癫的,在人潮汹涌的马路上横冲直撞,像在自由自在的梦中。她把一生的爱都给了男人,而男人却在一次偶然的外遇中把所有的爱都给了别人。是否注定世间的每一次外遇背后,总会有一个孤苦悲伤的魂灵?是她被男人拋弃,还是她拋弃了整个世界?
我不得不想起我的表哥。据说他在生意挫败之后的一个夜晚,被一只乌黑的鸟雀惊吓,从此不得不依靠镇定药物才能正常生活。我曾见过他犯病时候的样子,要么连续几天面无表情,一声不吭,偶尔又会一个人突然痴笑起来,要么一个人自言自语,大话连篇,完全沉浸在一个我们所不知道的“世界”里,甚至容不得别人靠近。他的母亲为他而放弃了自己原先的信仰,改信基督,并尝试了许多治疗的方法,西医,中医,民间偏方,甚至驱魔巫术;他的妻子是异乡人,一直寸步不离地跟随着他,即使在他犯病的时候也从未想到过拋弃。他的病时好时坏,据说前不久在一次偷偷地喝了啤酒后再次犯病,还动手打了人:他就这样在正常与非正常之间过活。我一旦想到那个曾经性格老实、常微笑着给我们讲故事的大哥,就忍不住心生悲凉,他是他“梦”里的主角,而我们已经在他的精神之外,我们能感知他疾病的隐痛,却难以治愈他精神的创伤!
于是,很羡慕那些能够平平安安白头到老的人,或是那些没有梦也没有外遇的人,虽然单调庸常,却也独享一份平静平淡的安稳人生。作家或许知道,“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张爱玲语),飞扬是梦的底色,梦如飞沫,匆匆易逝,正如无论多么精彩多么浪漫的外遇,也少不了以眼泪和无奈作为终结,所以飞扬人生一如柳絮桃花,难逃癫狂随风、轻薄逐水的命运,而人生的安稳虽比不得梦的玄幻、诱惑、神秘、难解,却有着踏踏实实的质量和重量,有着永恒的意味。然而事实是,人们大都渴望并追逐绚烂的飞扬,可又有几个人能忍受得了寂寞的安稳呢?
弗洛伊德曾把富于想象力的作家比作“光天化日之下的梦幻者”,把作家的作品比做白日梦。一篇作品就像一场白日梦一样,是幼年时曾做过的游戏的继续,也是它的替代物,哪怕是神话,也很可能是所有民族寄托愿望的幻想和人类年轻时代的长期梦想被歪曲之后所遗留的迹象,而“自我”是每一场白日梦和每一篇故事的主角。我不知道在这里我是否也是在作为一个梦幻者,完成一个光天化日下的白日梦?我只是越来越清醒地明白:幼年时的那些梦像曾做过的那些游戏一样,早已远离了我,此后恐怕也不会再见;妻子梦中的担心和悲伤恐怕也很难实现,因为我深深地爱着她,以及她正在孕育着的我们的孩子(他/她是我们的梦想的延续和遗留);只有精神疾病的隐患,它可能预伏在我的道路上,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突然跳将出来,俘虏我的灵魂和身体,这倒是难以预料的。弗氏认为,艺术家与精神病人是有相似之处的:精神病人往往对现实不满,便离开现实走向幻想的世界,而艺术家也从他所不满的现实中退缩下来,钻到他的想象力所创造的世界中去,他和精神病人的不同在于,他仍然有清醒的意识,他知道如何去寻找那条回去的道路,去再度把握现实。
对于来时的路,我还能看得见清晰的轨迹,而对于那条回去的路,我却禁不住疑惑甚至恍惚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