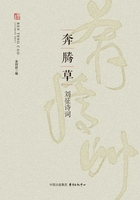刀口看起来很深隐约地能看见身体里内在的殷红却并不流血已忘了痛或者已经麻木了我把小刀藏起来床底下抽屉里枕头下还是不放心于是一甩手扔出窗外刀光一闪便无声无息了彻底放下心来随手拿起书架上的一本书很厚黑色的书皮布满灰尘从中间翻开啊赫然在目还是那样鲜亮一把小刀!
1
猛然坐起身,环顾左右,黑暗的,什么也看不见。这个时候醒着的人,要么彻夜失眠,要么像我一样,被噩梦惊醒。被噩梦惊醒的人,一定口干舌燥,精神恍惚,譬如我,四处找水,然后,整个下半夜就抱着杯子,在屋里走来走去,一边走,一边喝水,一边自己宽慰自己。
在这个感觉漫长的过程里,我首先仔细端详了我的手指,干净,痩小,平滑,有着忽左忽右的螺纹。它们中的几个,曾经不止一次地被崭新的打印纸割破,仿佛从锋利的茎叶上滑过,过了几秒,才感觉到辣辣的疼,血迹却非常的淡,放进嘴里,吮吸,便没有了。可是现在,我再次感受到隐隐的疼痛,是这疼痛让我从梦中惊醒,让我心神不宁,然而,我找遍手指以及全身,却找不到正确的伤口。
2
带着伤口的梦,在我看来,无疑预示着身体的疾病,预示着某个零部件的缺损或锈蚀。对病痛的敏锐,长久地蛰伏在我的心底,这是比睡莲冬眠的时间更为久长的一段时光。我不敢掉以轻心。记得1999年6月的某一天,我躺在宿舍的铁床上,东倒西歪地写下如下的文字:
我仿佛处在一种迷乱之中,这一段时间。
胃痛的折磨,我已习惯了。想写点什么,却不知能写些什么。百无聊赖中,翻着博尔赫斯的小说,常感到无比羞愧。
日子在不经意间溜走,四分之一的时光快要过去了,我到底学到了什么?我不知道。总觉得如此地过活,简直是慢性自杀!
回想以前的日子,紧张而辛苦,为了一个遥远又切近的理想而追求,如今呢?不敢想以后,却又分明感受到压力的存在。仿佛无形的手,撕扯我,推搡我,让我担心,让我畏惧:这是比胃痛更难以忍受的痛啊!
我仿佛厌倦了一切。唯一可以安慰自己的是一点随时都可能崩溃的友情,笑容也只有在夜晚的时候才绽放,一如回到童年,没有疼痛没有失眠的童年。
我在狭小的空气里生活着,想得很多,又忘记很多,好像在咀嚼一枚青叶,在品味苦涩的同时,却忘了把它的香味揣进衣兜。
我已无法还原当时的天气或是心境,正如我再也无法返回“没有疼痛没有失眠的童年”一样。然而,我还是能从潦草的笔画当中寻得一些蛛丝马迹。在写下这些迷乱的文字之前,我已在胃痛的折磨中挣扎了大半年。我的床头堆满了各种各样的胃药,一天之中,我至少要吞下三十粒大小不等颜色各异的药丸,闭着眼睛,我都依然能感受到那些或长或圆的小东西滑入咽喉时的停留和苦涩。枕头下是城市当中几家重点医院的病历,不同封面,不同的诊断结果:十二指肠溃疡,慢性胃肠炎,胃溃疡。总之,我的胃或肠正在发炎,或者正在一点点地溃烂,一点点沦为隐痛弥漫的药罐。
对此,我有着清醒的认识:我的胃正渐渐老去,它消化不了任何食物,它只能按部就班地将食物承接,然后,再向下一个环节慢慢传递。吃过一点东西,隐痛会短暂消失,然而很快到来的“饿”,又会提醒我它依然存在。舌头渐渐丧失本色,味觉迟钝,整日神情恍惚,度日如年。1998年9月之后的很长一段日子,我都在这样的疼痛、失眠和迷乱中紧张度过。
甚至,在十八周岁生日那天,我突然地就想到了死,想到了离开。一想到这些,全身立刻变得冰凉。
1999年的夏天,我不得不接受家人的建议,做胃镜检查。而此前,钡餐,透视,我都已一一经历过。躺在病床上,任由一个医生捏紧我的嘴,一根细长光滑且前端带着微型探头的管子,就径直钻进我的嘴里,我的咽喉里,直至我千疮百孔的胃里。我本能地想要打嗝,反刍,或许还包含着想要咬断管子的念头,然而,我的舌头已被提前麻醉,它僵硬着,一动不动,我只能张口结舌。整个过程并不长,可是管子拔出之后,我依然感觉从嗓子眼到胃还悬挂着一根绳子似的,令人作呕。我不停地清嗓,咳嗽,然后,一个人,默不作声。
不幸的是,西医再次对我的胃失去信心。疼痛依旧持续。由此,我的母亲更坚定了中医治疗的信念。她终于找到镇上唯一的一名老中医,开了药方,每天用药罐为我煎药。我的胃再次浸泡于苦涩的中药之中,苦苦度日。夏去秋来的时候,果然好了些,又少吃多餐小心调养大半年,真的好了。我记得母亲称那位老中医叫“大气”,我不知是不是“大器”,无论如何,我都感谢他,感谢来之不易的健康,至少,感谢母亲,她不用再起早摸晚地为我煎药了。
3
就让母亲多睡一会儿吧!然而,此刻的母亲,或许还在忙碌着,她在遥远的异乡,给亲戚打工。就在昨天,她告诉我她睡得很少,只有四五个小时,其他的时候都在站着,洗碗,收拾。“站着都能睡着”,她说,她的胳膊肿了,很痛,已经举不过眼睛。母亲四十九岁了。她的手已经很久没有抚摸过我的头顶了。她不知道她的失眠的儿子,今夜在千里之外的梦里醒来,想她。当然,还有一个最想她的人,此刻正在乡下空荡荡的新房子里打着呼噜。他是一个有着三十多年工龄的小学教师,他会唱歌,弹脚踏琴,拉二胡,打乒乓球,他还会将倒塌的院墙重新砌起来,一个人侍弄菜地和家禽。他已经习惯了没有母亲在身边的日子。他做得比我们都好。只是,他不再写诗和散文,他把这些都毫无保留地传递给我们兄弟,现在,他读我们的诗和散文,更加高兴。就在去年,家徒四壁的老屋被我们齐心推倒,我不用再担心雨季的来临,他也不必再手持竹竿,对着屋顶指指点点了。村庄注定是属于他一个人的,他虔诚地守候在那里,像个称职的稻草人,守护着清香四溢的田野。我知道一个人的村庄,总会显得孤寂,尤其是在漆黑的夜里。而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都在异地,劳动,工作,或在夜里惊醒。一家四口,竟分作四处!我一直弄不明白:是他选择了那个叫“罗岭”的村庄,还是村庄包容了他坎坷不幸的一生?值得庆幸的是,他,我日渐苍老的父亲,终于可以安稳地睡觉了。我依然难以入睡。总是有比胃痛更难以忍受的痛,在折磨我,比如空虚,比如无助,比如无边无际的寂寞。胃痛,吃点药,缓解一下,或者中西结合,休养生息,终能看到健康的光芒,仿佛不小心划破的伤口,终抱着早日愈合的希望。可一个人的寂寥却是巨大的刀口,它敞开着,甚而渐渐扩张开来,仿佛要将一个人完全反裹。没有药,或者还没有见到为我敷药的人,只能等待,并独自忍受。
我再一次生病,重感冒,发烧,39.2°C,吊水,三天。我坐在输液室的长椅上,护士小姐的高跟鞋敲击着水泥地面,远了又近,近了又远。四壁雪白,竟然没有第二个人,只有头顶两盏日光灯将“日光”撒下,仿佛我苍白的脸。头顶二十七个吊钩已被我数了三遍,然后,开始数滴答的液滴,一滴,两滴,再接着数不规则的心跳和脉搏,感觉就好像握着夜的手。巨大的“静”,出奇的静!甚至可以听见葡萄糖在静脉里丝丝游动的声音。生病的人经常伸着头望向窗外,其实窗外是一堵斑驳的墙,遮挡我的视线,压在我的心上。凌晨的鸟在墙外鸣叫。没有人在我身边,除了我忠实的影子。我孤独地来,孤独地坐在这里,又将孤独地返回,只有手背上的六个红点,以及冰冷的长椅,证明我曾经来过。
4
我不知道这世间让自己痛苦的方式到底有多少种。至今,我已体会到的有这样的四种:
1、自我解剖。一把铁锹,它在奋力地向下挖掘。钢铁碰撞硬石,火花在黑土里飞溅。痛苦是呻吟的声音,挥动着优美的力的弧线。目标是有的,它取决于你的勇气和胆量将坚硬的石头分解,或者将它消融,像水一样。
2、醉。心脏游动在血液里,酒精冲刷着它的表皮,仿佛惊涛拍岸,乱石穿空。身体语言只剩下两个苍白的字:虚空。倾倒,成为它唯一的姿势。
3、病。我说的好像已经很多了。
4、爱。勇于自我解剖的人,都心甘情愿地让自己精神痛苦。自己将自己灌醉的人,都隐藏着无可告人的秘密苦痛。生过病的人,都自以为更懂得健康的意义,正如渴望爱情的人,都充满蹩脚诗人的自信。正如那时候的我,开始学着写诗,卧在宿舍的铁床上,伏在公共课的课桌上,写下断断续续的句子,仿佛经历断断续续的阵痛。由宇宙缩小到个别事物,再由个别事物扩大到神,这就是爱。我不可避免地要成为蹩脚的诗人,为爱情而歌唱,在执著中日益脱离自我的执著,在清醒和沉睡中体味甜蜜的痛。而更多的时候,我是在个别事物和神之间,徘徊不定吧。
窗外,树叶开了几朵?沁人的清香,也只是空气罢了。路灯在一旁冷笑饥渴的马路,喘着气,吐着舌头。夜行的人和飞虫踩着失眠者的头顶,从黑暗中走来又向黑暗走去。当我伸出手去,时光就轻而易举地从指缝间穿过,且渐行渐远了。就在前几天,我刚过完我的又一个生日,我很高兴,我的身边是我的爱人,我的身体看起来还非常健康!
夜将尽。杯水将尽。只有杯子,透明的,明晃晃的,仿佛一把圆满而又暗藏杀机的刀子。我已无力去回答这样的问题:谁把谁划伤?谁又成为谁的刀口?我只是一天比一天清醒:被刀割伤的人,从此以后处处提防刀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