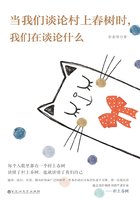◆我像处身于另外的城市,我像处身于旅行途中。这儿没有繁华、拥挤,这儿没有秩序、提防。宽敞的道路只为我一个人延伸。路灯散发橘黄色的光芒,滑向不知所踪的远方。
四周都是边缘
我至今仍无法忘记读一位尊敬的老师诗作时产生的激动情绪。那是一个冬日的午后,在空寂无人的七人居室中,花色窗帘将阳光挡在窗外,唯的一抹明亮闪进来,照在我的床头。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钢琴曲静静地流淌,快要流成一条河了。她的诗句跳跃着:
打开手帕
我们终于为难地发现
我的内心受到了强烈的激荡,“四周都是边缘”六个字突兀于我的眼前,我知道,这是一种生命的状态,它强烈地抵达了我的存在和行进方式中。我知道自己生命的凝重、焦虑、困惑和左冲右突,就是因为这种边缘状况。它无处不在,无法避脱。它决定了一种轻巧的生活方式无法在我的生命中容身,又意味着我在荆棘丛中前行时脚尖指向的晦涩性。
没有人会给我道路,没有人能够。因为四周都是边缘。我所阅读的,只是一页;我所记下的,只是一个明亮的光斑,并且它正在黯淡。只有我一个人,回到自己的内心,正视寻求路上的彷徨和突进、幸福与忧伤。同时我的这些所为,肯定位于某一时境的边缘,因为没有一种持久的方式让我长时间地感到快乐。我在否定之时,却发现肯定的不确切性;当我把某一事物当作一种结果、一种理所当然来接受时,发现前提却是个假设的条件。我无法真正回到自己的内心,去听天籁的声音,将一切杂物抛出体外。
人,其实立于生命的边缘。有时候拥有无限的话语权利,却不及一个人静处时,灵魂的突然闪现将生命照亮。有时候你位于某种深刻的思想边缘,于是变得讳莫如深,但你同时又位于迷乱的边缘,变得十分的可笑和幼稚。就理性的存在而言,四周正是非理性的存在边缘。
因为四周都是边缘,人无法在某一边缘处作静观状。这种年轻的生命中青春的可感和恍惚、诱惑和抗拒,折射于思想中,于是,遥远的地方飞鸟的轨迹与羊肠小道交错而过,雷鸣和开山的炮声同时进入耳中,礼花和光环一左一右……四周都是边缘。四周都是边缘,又促使你努力去开拓,上下以求索。在生命的天空,人就如一个太阳升起和降落。
日常的消解
文明的发展和尘世的喧嚣使现代人归隐山林的愿望成为梦想。对现实世界依赖的有增无减,使“采菊东篱下”的皈依成为一种无法企及的捷径。我们不能否定的一个事实是:日常的消解使人们陷入一种巨大的灾难之中。由于繁忙、无序和无所适从,于是在万籁俱寂中的片刻休憩会使人激动不已,灵魂的偶然闪光会使人欣喜若狂。这时候伍尔芙所说的“独立房屋”就会闪现,它不仅是物质上的,更是精神上的。只有在这间“独立房屋”内,你才是你自己,人才有了还原和正视的可能。
在这个放弃灵魂的世界中,媚俗的大众不会也无能去辨别日常带给我们的巨大消解在挥也挥不去的飘浮着的一地鸡毛中,人丧失了锐气和意识,处于一种蒙昧和痴呆状态。在一片繁忙中,越来越多的人丧失了反思的可能,蔑视内心,无法回到内心中去,使灵魂黯淡无光。大众的流行式的生活和思维方式,貌似有条不紊无可指责,实际上消磨大量的时光,使有棱有角的行进被水滴石穿。
“人类的忘性,日益加深加剧。人们在轻薄的生活中轻巧游走,太需要被敲击和唤醒了”(王小妮《时光日常的消解的隧道》)。伟大的诗人告诉我们,“皈依于你自己日常呈现给你的事物,你写你的悲哀与愿望,流逝的思想与对于某一种美的信念——用深幽、寂静、谦虚的真诚描写这一切,用你周围的事物、梦中的图影、回忆中的对象表现自己……别人的喧扰只远远地从旁走过”(里尔克《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
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说:人是需要无限反思的。
日常呈现给我们的消解因为反思的丧失而愈显巨大。走向内心,内心世界的奇大无比与灵魂的浩渺无边,正需要无限的反思。因此抵达你的内心,牵制你的内心,就有了一种良好的反消解可能。
独行的火车
几年前读土耳其诗人塔郎古的诗:这么晚了,你要去哪里/美丽的火车,孤独的火车?读出一种凄凉无助的美丽,仿佛在寒风飘雪之中,只有他一个人拉紧风衣的领子向前走去。其实这里有更深的一种精神祈向,除了肉身之外,思想也是一位独行者。这让我想起了一种说法:意识的灯熄灭了之后,他的肉体要奔波万里,去寻找和会见他的思想。
但我们越来越发现栖居的思想犹如树枝在摇坠。在你我的守望之中,独行的火车声音越来越弱了,甚至迟迟不来。当现实生活呈现给我们比想象中要复杂得多的生存境遇,在滚滚的烟尘和熙攘的人群中,思想在羽化,日常细屑的消磨,把它推向围墙之中。
据说以前的大学伙食中,一块肉是闪着光芒的。但那个时候,具有更强光芒的,是灵魂的饥渴。比如为了一本油印的小册子,一篇新的译文,借着灰暗的灯光,思想会乘上灵魂升华的飞行器,谁也不会为短期的享受去贪恋一块肉。这种景观越来越少,离我们也越来越远了。这样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每个人都很忙,忙得像到处开会的华威先生。可以独行的火车热烈地去关注各种潮涨潮落,跟它们的脉搏一起跳动。
可以去哭别人的哭,笑别人的笑,却把自己抛出自己的体外。脑袋只剩下了一双耳朵,并且长在了别人的嘴上。努力所要抵达的,正是使思想结伴而行和获得共舞。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去关注自身、审视自己,甚至根本没有想到这么做。于是达成了共识的大众思想。幸好还有斯宾诺莎之类的人,会冷酷无情地说:我希望那些怀有大众思想感情的读者不要读我的作品。
时代变得贫乏了,是精神价值变得贫乏了。一群读书的人,像卡夫卡的老鼠,感觉天地越来越小了。他们是孤独的火车,在夜晚会问:“去哪里?”
当音乐响起来
一个人走在旷野之中,突然与天籁之音不期而遇。
一根心弦被拨动着,温润、醉心,而后是四顾茫然,乐音阒寂,心境枯索。这与一个人正襟危坐在大剧院内,听一场交响乐是不同的。虽然后者也会使你感到绝世独立,甚至热泪无声,但毕竟少了一些自然的风骨,少了一些气象阔大的境界。
天籁之音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交响乐团的现场演奏也非时时可以享受。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坐在室内,听听自己喜爱的乐曲。我自己有这样的体验:当我喜爱的音乐一占据我的空间,其他的一切就显得不太重要了。
即使我片刻前还是思如泉涌,现在已荡然无存,我也不懊恼。当然,很多时候我在背景音乐中静静阅读或写作,这种状态非常好。几年前,我对作家格非的话还有些不理解,他说:“能够从事音乐工作就不必写小说了。”现在我觉得他的话讲得很对。持相同观点的还有李杭育,他曾写出了《葛川江系列》等名篇,但当他竖起倾听音乐的耳朵,着手梳理经典唱片后,就将写小说的事业忘得差不多了。所以我们也不难理解罗曼?罗兰在《约翰?克利斯朵夫》中的话:“音乐,你曾抚慰我当音乐响起来痛苦的灵魂。音乐,你曾使我的心恢复宁静。”音乐作为一种无需翻译的语言,最大地丰富了人类的生活和内心世界。
托马斯?曼在《魔山》里写道:“音乐不但鼓动了时间,更鼓动了我们以最精妙的方式去享受时间。”他讲的是一种精妙的音乐和理想的状态。余光中这样理解道:“这当然是指精妙的音乐,因为精妙的音乐才能把时间安排得恰到好处,让我们恰如其分地去欣赏时间,由时间形成的旋律与节奏。相反的,软弱的音乐——就算它是音乐吧——不但懈怠了时间,也令我们懈怠了对时间的敏感。”然而,我们缺少的并非是精妙的音乐,而是倾听精妙音乐的耳朵。好在,音乐并不因此而撤走它的馈赠。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能要求有这样的耳朵:
它倾听着精妙的音乐,并且获得了博大的情怀。我们即使只要求有愉悦——在音乐响起来的时候获得快乐,音乐已能显示出它的伟大来了。
音乐暗合着人类的心境。在我们悲伤的时候,可以有悲情勃拉姆斯;在我们暴虐而疯狂的时候,听听莫里森;在沉入不醒的睡眠之前,可以听——蝴蝶在(标本上)尖叫……我们可以亲吻气象阔大的西贝柳斯,也可以拥抱温柔敦厚的德沃夏克。在音乐响起来的时候,我们不觉得孤单:因为你在倾听的同时,这一个声音正缓缓地说出你自己。
月光下的徜徉
在我们所生活的城市,一个人要想在既定的环境和生活习性中脱离开来,在他处获得内心的安定和需要,并非一件容易的事。且不说工作、财力、时间不允许,单就克服人们本身固有的一种惯性而言,也是困难的。
在这个城市像模像样地生活之前,我是这个城市某大学的学生。现在想来,大学最大的好处在于给我提供了一种平静的内心和随意的生活。年轻的教师并不介意我逃他们的课去图书馆写作,校内外的报刊不间断地发表我的大小文章,并不丰厚的稿酬为我并不奢侈的生活提供了有力的支援。
当然,最大的乐趣是因为拥有两个假期。我记得每个暑假开始的时候,在日见空荡的寝室和教室里,我总是认真地完成自己的创作计划,余下的时间,我则回到自己的家中度过,有时候还带着同学。
我的家在海边,属于那种仍然开阔、逐渐富裕起来、变得愈加美丽的乡村。因为有海,因为有月光,夏夜是美丽的。时常在皎洁的月光洒下一片片碎银的时候,我们便踏着月光的小路出发了。穿过原野,在洁净的海堤上坐下,面对无边的夜色下显得更加神秘的大月光下的徜徉海,真有点举世皆忘的感觉。对海陌生的朋友往往被这种场面吓住,我却感到无比的亲切。那在茫茫的大海中微弱而又顽强的灯光,让我感到生命有一种真实的感觉。
我们还坐着小船出海,当然在风平浪静的夜里,还多一些人。船里装着一些煮熟的海鲜,一些自家的梅酒。船开到离岸不远的地方,停了机器,便任它漂流了。我们有节制地喝酒,感受着海风、涛声的无穷覆盖,时而变得微小,时而变得强大,时而变得渺小,时而变得伟大。
在我们这一代人贫乏的生活中,这样的体验恐怕也是极少的。在月光下这样徜徉的朋友,内心往往受到一次真实的战栗,以后的生活便难以忘却这样的经历了。
而我作为一个在海边长大的孩子,往往也在这样的感受中获得对海的认识,她的平静,她的愤怒,她的浩渺,她的博大。
一个人不能同时踏入两条河流,一个人何以诗意地在两地栖居?在一个地方工作、生活,逐渐稳定和平静下来后,当人已经难以独自一身而更多的为生活所累时,月光下的徜徉变得何其遥远!或许在多年以后,记忆的画布中,“月光下的徜徉”已褪色为某本书的封面,拿起来翻一翻,页页尽是空白。
漂泊的声音
住在临江的七楼小屋,听的最多的莫过于黄浦江上轮船的汽笛声了,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这样的声音透过尘埃落定薄雾弥散的夜空,便能够在耳边清晰地回荡了。我夜夜在这样的声音中入眠,也会因为它,久久难以睡去。
这是一种漂泊的声音,然而我喜欢。与城市中种种喧嚣得令人烦恼的声音不同,汽笛声里充满了生命的质感。远行的船只回来了,将要泊入平静的港湾,汽笛声里便带着风尘,然而又是明亮而欢快的;远航的船儿要出发了,汽笛声便沿着蜿蜒的黄浦江,先行远去了,仿佛正是开路的号角。
那些个船儿,我见过,漂泊的声音从那里来。停泊永远是短暂的啊!人的生命,多像那一只只航行的船儿,要历经无数次的征程。但愿每次出发时,会有一个庄严的宣誓,而归来时,能给自己一个响亮的回答。
很多年以前,我的父亲还是一位船长,他的船到过这个城市,他鸣响的汽笛声,肯定在这里的天空回荡过。然而多年以后,我在江畔听不到哪一次的声响会是当初,也许两个世界的人永远无法相会,每一声相似的漂泊的声音汽笛声里,唯留了空空悠悠的怀念。
那些个忙碌的人,那些个奔波着的晚归的都市人,不知是否在这声音里听到一点恋曲、挽歌和悼词。窃以为,在城市中也许只有望天和听汽笛声才可以让人的心灵拥有驰骋的空间。然而城市的天空被切割得太细,灰蒙蒙只落满脸愁云,还好剩下这漂泊的声音吧,一声声,让人的思绪飘去了又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