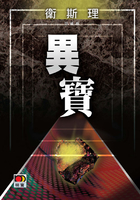三人一看,果不其然,皱纹纵横,布满了沧桑的大脸上,左侧的太阳穴下边,从眼角到颧骨,粗糙的皮肤,都还在虚肿着呢!红中透紫,甚是不轻。野蜂不像家蜂,凶猛善斗,个头大,耐力强,不怕寒冷,毒汁还特多。不管人类还是牲畜,一旦发现,都会恐慌地远远躲开。百十斤重的野猪崽,撞了蜂窝,十有八九,都被蜇死。山里有三种蜂子,除了蜜蜂、黄蜂之外,再有就是那种既黑又毒的大马蜂了。马蜂跟毒蛇一样,许微不慎,就有葬送性命的可能。宋希山被蜇,不是黄蜂,也不是马蜂,而是家养逃走后又适应了大自然的小蜜蜂。适者生存,年复一年,代代变化,这种蜂子除了采蜜更为勤奋,在自卫和进攻方面,其野性、顽固和残忍,早已远远胜过家养的蜜蜂了。
雪地上,边往回走,边听宋希山慢声慢语,有滋有味地继续说道:“蜇了一家伙,我也一巴掌把它送了命。可转念一想,不对劲儿呀!这死冷寒天的,小鸟都不飞,哪儿来的蜂子啊!低头一看,胳膊上又落了两只,子弹袋,还有我孙子的背包上,还有好几十只,恋在那儿,嗡嗡叫着,就是不肯飞走。我哪,也就犯开了寻思,越琢磨,就越觉着不太对劲,不是迷信,年轻的时候,跟日本鬼子,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这把年纪土埋到胸膛,还讲什么迷信哪!可是,这儿是黑瞎子沟,有些现象,专家教授还没有弄明白呢!再说啦,吃狩猎这碗饭,事事处处,脑袋瓜子,都得多根儿弦啊!啊?小伙子们,是不是这码事儿?这么一想,我就觉着,这些蜂子,肯定是有来头儿的了。为什么蜇我?是提醒我,也是在告诉我。可是我,竟一巴掌把它给拍死了!这事儿干的,唉!真的是,要多晕头有多晕头啊!吃这碗饭,是不能说后悔的,提到后悔,不就得饿死啦!“明白过味儿来,我就跟它们说道:‘噢!你们是来送信哪!好吧,我知道啦!你们前头飞,我后面跟着。’说完了,蜂子,足足有二三十只,从我们爷俩身上飞起来,打着旋,一到沟口,我就彻底明白喽!是陈忠实的人马,主人遭难,喽啰们送信来了,就这样,跟着蜂子,一步都没有停呵!没到近前,你们仨就嚷嚷上啦!这一嚷不要紧,再看蜂子,就统统没了!……
吉林他口锈,不愿意吱声,听我念叨,你们仨,这一会儿满意了吧?裤兜子捉蛤蟆,少说也得有二十里啊!直线儿拉过来,跟头把势的,可真是累屁喽!忠实呢?忠实这小子,一次又一次可真的是命大啊!也兴许,是山神猎种,都在保佑着他吧!”听宋希山说完,对蜜蜂、对棕熊、对孤猪、对黑瞎子沟,三个人也就犯上了寻思。踩着积雪,脚下发出来一连串的咯吱声。哈气呼出来,自己都能看到,一股一股的轻雾,挂在胸前,变成了白霜。刘建民放慢了脚步,侧脸用敬佩而又疑惑的口气向宋希山道:“爷们!我刚到林场来,第一次见面,您说这些,是我闻所未闻的。可是,我还是有点儿不明白,陈师傅三天多啦,汤水没进,身上还是下雪前的服装,但没有冻坏。如果换另一个人,手脚胳膊腿,冻不掉,也得冻青冻黑,冻成冰棍儿呵!可是人家,愣是没事。昨天小夏师傅说,身上不冷,抗冻,是跟常年喝黑瞎子沟里的水有关。宋大伯,您老人家在山里见多识广,黑瞎子沟里的水,人喝以后,免疫力真就这么强吗?”宋希山认真听着,听完了,却没有及时地回答。青山对此也深感兴趣,他放慢了脚步,用期待的目光,边走边在宋炮手的五官上观察着。
宋希山没有正面回答,矜持了很长时间,才胸有成竹、毫不含糊地回答他道:“没错!是那么回事。不信,你们自己去看!黑瞎子沟内,那条鸡爪子河,常年不冻,老那么哗啦哗啦地淌着!还有,死人湖的中心,天气越冷,喷出来的热气越高。这不稀罕,也不用我说,回去以后,自己去看,你不就相信了吗!几百年啦!谁也没有见过,鸡爪子河冻住了呀!可是,什么原因,也兴许是,湖里头的白垩龙,在起着作用吧?我琢磨着!还有,沟里头的蜂蜜,也不一样,一样的花粉,都是椴树,黑瞎子沟搅出来的蜂蜜,多冷的天,零下三十度,也不见凝固,跟刚搅出来的一样。不然的话,中央政府,能红头文件把这儿定为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吗?小伙子,你们哪,赶上了好时候,从今往后,真就应该好好地动动脑筋喽!”
三个人迎出去有半里多地,返回爬犁旁边,也许是闻到了香味,还是熟悉了的原因,没到近前,三只小狗熊,就提前匆匆忙忙地迎了上去。歪着脑袋,盯着宋吉林的背后,嘴上还不约而同地一齐哼哼着。宋希山看在眼里,乐呵呵打趣地说道:“饿了吧!别着急,一会儿就慰劳你们,拉爬犁有功。一会儿呀,还得靠你们三位,把我也拉回去呢!老喽!这两条腿,比灌了铅,还觉着沉哪!”时近中午,四周和头顶上的云彩,先是一点儿一点儿地由厚变薄,露出了一缕缕、一丝丝湛蓝的——水洗一样的天空;继而是匆匆忙忙地奔走,奔着东南方向,阳光露出了笑脸,西北风就吹来,雪地上、山谷中,也就时不时变幻着黑云彩的影子。影子忽然爬到了山坡上,山谷下面,人和动物,也就猛然间感受到了一阵明快和亮丽,尽管刺眼,却非常舒服。陈忠实下身还是不能移动,半躺半坐地靠在爬犁板子上,听见抗联老战士的朗朗说笑声,心头一热,鼻孔发酸,不知不觉中,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劈里啪啦地滚落了下来。不是疼痛,全身似乎是失去了感觉;也不是后悔,后悔又有啥用?而是有点儿委屈,有点儿痛心和感动,见到了自己的长辈,众人走到眼前,他竟然呜呜地哭出了声来,孩子一样,难以克制……
看见影子,听到哭声,宋希山悬着的那颗心,才彻底地放了下来,一屁股坐在雪地上,嘿嘿笑着,幽默地说道:“哟唷唷,不赖呀,忠实也会哭鼻子,这可真是大姑娘生孩子——头一回哟!不错,还行,有腔有调的,换个人,还真就达不到这个水平哪!你们大伙儿听听,是不是有板有眼的哪!家里头老伴,练习了这些年,不见长进,早知道说啥也得把她领来,也好总结总结经验哪,啊!我咋就没有提前想到呢!……”陈忠实“噗哧”笑了,笑了又哭,好一顿折腾,才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和感慨。见他冷静下来,宋希山才板着面孔,严肃、认真、冷峻地告诉他道:“忠实哪!这话,本来不想,现在就说,可我又憋得心里头难受,你哥哥陈大局长,是死心塌地,要把黑瞎子沟的椴树,都砍光的,走吧,赶紧地回去!他这么干,不是诚心的……等着坐笆篱子吗,啊?鸡爪子河林场,咋就出了这么个败家子呢!”宋希山气哼哼、一脸愤怒地大声说道。
宋吉林的背囊中是二十多斤,在家提前就烀熟了的野猪肉。炮手出门,所带给养,除了白酒就是猪肉。方便省事,抗饿耐寒,补充透支性的体力消耗,野猪肉是首选的营养食品。野猪再胖,膘子也不会超过一指,肥肉极少,瘦肉特香,与家猪比较,野猪肉的肉丝较粗,食用再多,也不腻歪。离家以前,把凉透了的肉块切开,肉缝中塞进去辣椒油、各种佐料和盐,即使站在风雪中,一手抓肉块一手攥酒壶,一口烈酒一口熟肉,脚踏雪原,面视苍穹全身发热,剽悍无穷。白酒的胆量,野猪肉的动力,不管豹子还是群狼,即使孤身一人,交战时也不会怯手的。炮手交谈多为刀枪,林海雪原,力气和胆量尚是炮手们的立命之本。宋吉林把袋子打开。人和狗熊,同时吞咽,伴着风雪,沐浴着阳光,忠实情绪较好,食之不多,不感到饥饿,也就没有多少食欲,数日无食,腹中空空,为啥不饿?连自己也觉得非常奇怪,人是饭铁是钢,为啥就感觉不出来饥饿呢?小夏拿肉块来安慰“花子”:“吃吧!香着呢!不吃?傻子!给谁置气啊!”“花子”摇了摇尾巴,有所表示,但最终还是拒绝了主人的施舍和诚意,闭着眼睛,懒洋洋地谁都不看,往事的回忆,使它增添了痛苦;现实的无情,又使它进一步感到了绝望。
人吃饱了精神倍增,狗熊饱了温驯听话。刚要起步,宋吉林小声儿对爷爷说道:“爷爷!您还忘了一件事!“啥事?”宋希山莫名其妙地看着孙子。“您不是说,搜山的规矩,谁找到了谁打枪吗!”说完,吉林盯着忠实,脸上洋溢着亲切和激动。宋希山猛地拍了一下自己的大秃脑袋:“哎唷唷,您看看!您看看!吃屎的记性,多他妈的臭啊!林子提醒得对!鸣枪三声,告诉他们,别再找啦!这是规矩。可是,这些日子,硬是让陈忠财这小子,把我给气糊涂了,唉!人老屁股松,干啥啥不中喽!”吉林对空开了三枪,“咚——咚——咚——”枪声在山谷中久久地回荡着,亲切、洪亮,带有颤音,半天才消失,林海才重新恢复了它的宁静和深沉。
在吃饭的时间,小夏、建民、王青山你一言我一语,争先叙述着这两天一宿的所见、所闻和感受。从飞机残骸到金钱豹的围攻;从“长毛”的死亡到王青山的挂彩;从大孤猪的光环到老母狗的抗议;从山狗子的光临到三只黑瞎子的恐惧;从小蜜蜂的安慰到陈忠实的冷静,七嘴八舌,毫不顾忌。有了猎枪又填饱了肚皮,在青年人的心目中,上帝就是自己,世界由自己主宰,什么山神猎神加土地神,统统不在话下,统统在接受着自己的征服和改造,什么豹子、孤猪,再凶也凶不过火药,再硬也硬不过铅丸啊!如果早有猎枪,火烤豹子肉是最有风味的美餐;身体下面,理所当然地铺上一张豹子皮吧!人性是贪婪的,贪婪使他们产生了遗憾和惋惜。王青山甚至满不在乎地问宋希山道:“宋伯!您吃过豹、豹子肉吗?豹子皮,也有老虎皮暖、暖和吧?……豹皮吊褥子,听说好、好着哪!”山谷寒风凛冽,林海涛声轰鸣。宋希山眉头紧蹙,半天无语,本想训斥几句:“脸盆扎猛子——真不知道深浅啊!癞蛤蟆打哈欠——你可真是好大的口气哟!”但话到嘴边,又摇摇头咽了下去。
异想天开,是说明他们经得太少;胆大妄为,证明都还没有吃着这方面的苦头。说浅了,不解决问题,一身朝气,他们怕啥?说得太深,脸上挂不住,心里不服气,思想上也肯定不会接受的。年轻人,毕竟是时代不同啦!因为在场的人,除了自己,谁也不知道,这头孤猪,就是传说中的那尊猎神,山林中,除了山神,就是猎神;山神是山虎,人所皆知,但山林中的猎神,在大、小兴安岭,除了职业炮手,一般人是知之甚少了。忠实遇到了猎神,体会自然深刻,三位小青年也看到了猎神,但仅仅是目睹,是新奇,也许是一种趣味,怎样说服教育?看来最好的办法就是身体力行,用行动,去改变他们的意识,避免再吐狂言,也好使今天顺顺利利地不再发生意外……想到这儿,宋希山一声不响地站了起来,整了整猎装,严肃、虔诚地望着大石砬子方向,卸掉了腰间的子弹袋,随手扔在了背囊上。以军人的步伐,往前还出了十多步远,停住弯腰,用双手推了一个不大的雪丘,插草为香。别人大眼瞪小眼地还觉着纳闷,就见宋希山两腿一弓,“噗嗵”一声就跪了下来,闭着双眼,默默地祈祷……寒风卷着雪雾,在山谷中东一头西一头地旋转着。天空变暗,阳光被遮。一块浓云也一瞬间从山谷中徐徐地升了起来,悬在空中,久久不散……
宋吉林也在爷爷身边默默地跪了下来,双手合掌,默默地祈祷着……风力加大,速度变快,旋起来的雪雾,始终在人们的周围一圈圈地旋转着,乌云继续变浓,由灰变黑,悬挂着不动,尽管没有遮住阳光,却在雪地上投下来一块暗暗的影子。刘建民、夏立志、王青山,也恐慌不安地在宋希山左右跪了下来,盯着空中,盯着那块继续变幻的云彩。在云彩上端,三人又再次清清楚楚地看到,还是在岗顶上看到的那只大孤猪,悠悠晃动着,稳坐云端,居高临下,正用红红的小眼,咄咄逼人地盯视着他们。他们没有祷告,也不会祷告,只觉着全身冰凉,冷汗从额头上一滴滴顺下巴颏滴落了下来,刚才还贪婪无忌的王青山,此时此刻,竟然跪在那儿差一点就晕了过去……无声的劝说,也许就是最好的忠告吧!“呜——呜——呜——……”是风声还是涛声?是海啸还是闷雷?空中的乌云在缓缓地运动,越来越近;雪地上的影子已把众人统统罩住,远处银光刺眼,周围东一头西一头的雪雾,突然停了下来,原地不动,旋转的速度却越来越快,挖起地面上的积雪,旋走了所有的树叶、枯草、树皮和兽类,与乌云衔接,天地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