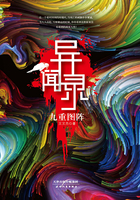陈忠实愣愣地站在那儿,看着眼前这位德高望重气度非凡又面色铁青的老抗联战士:秃顶、络腮胡子,气宇豪迈,皮肤粗糙,目光炯炯。凸兀的颧骨让人欣赏到他年轻时代的英俊、刚烈和暴躁,而颧骨下面纵横着的皱纹和醒目夸张的老年斑,又在向人昭示着他的固执、秉性、倔犟。他的后面是蔚蓝的天空和涛涛的林海,以及林海与蓝天中盘旋着的鹰鸢和秃鹫。冷不丁一瞅,既像一尊凝固了的雕塑,又仿佛影视剧中的特写和重彩泻染成的人物肖像。陈忠实知道,就宋希山的人品、威望和阅历,哥哥的升迁和贬降,他是绝对不会动心、游说和奔走相告的。众所周知,老人的感情和灵魂始终是跟党的事业、民族的利益、国家的盛衰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既然骑自行车已经走远,又蓦然间的匆匆返回把自己喊住,在老人的内心深处,肯定会有相当重大的事件想与自己通报和叙说。果不其然,老人把自行车支牢在哗啦啦流淌着的桥头上,背着双手,目视黑瞎子沟内踌躇了很长时间,才沉重地说道:“我返回来,要告诉你的是:你哥哥陈忠财他,已经组织了突击队,进黑瞎子沟,砍伐沟里的椴树林子,加工成半成品,卖给日本人……”说着,老人重重地叹了一口长气:“唉!造孽啊!”“啊”字出口,老人仿佛突然地衰老了好几岁,全身微颤着,语调也似乎是特别的酸楚,“造孽啊!黑瞎子沟,是当年北满临时省委机关所在地啊!也是抗联三军、六军最后的大本营噢!如今,这些孽种,又在沟里面打主意,和当年满洲国的大汉奸,又有什么区别哪!啊!赵将军,当年是在小兴安岭,为国捐躯的,如果知道了,日本人来毁他的老窝,九泉之下,也不会安宁啊……”“啥?他敢砍这沟里的椴树林子?”陈忠实不假思索地大声说道。
林场采伐砍树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正常生产和本职工作。无可非议,让他感到心疼的是:椴树是蜂子的蜜源,砍了椴树,势必会影响蜂蜜的产量,一旦砍光,蜂子上哪儿去采蜜啊!毁掉了蜜源,黑瞎子沟蜂场,不也就名存实亡了嘛!蓦然间,那天喜田和铃木启久的嘀嘀咕咕又在脑海中浮现出来。夏立志当时就说:“妈的,小日本,不会放过咱黑瞎子沟的!”事态的发展,真就让他给言中了。考察团没走,就盯上沟里这片椴树林子啦!另外还有,哥哥提升,与砍伐椴树林子有什么关系呢?他对宋希山说:“宋师傅,您听错了吧?前两天,申局长亲自进沟里传达了省政府红头文件。黑瞎子沟是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别说是伐树砍木头,就是割架条、拾合草,也是一律禁止的。您老是不是耳朵背,听错了吧?”“啥?我耳朵背?听错啦?”老宋头气哼哼地驳斥他道,“‘夜特’一会儿就来!先把油锯手送上来,就住在小日本的帐篷里面,你哥哥他,在大喇叭上公开布置的,说是什么‘抢在下雪前放倒,运回场部加工’,你侄子,陈小宝,开车一会儿就上来了……红头文件?林业局,不是也有红头文件吗?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又能怎么样?还不都是,一个和尚一个令?他们代表政府,上下嘴唇一碰,就是行之有效的政策啊!陈忠实,你啊你啊!你让我说啥好啊!唉!罢罢罢!闲吃萝卜淡操心!河里冒泡——多余啊!走你的吧!走你的吧!咱们就别磨着舌头——废唾沫星子啦!”说罢,宋希山无精打彩地再一次调回了车头,冲着分水岭方向,晃晃悠悠,趔趔趄趄,疲惫而愤懑地、吱吱嘎嘎地往前滚动着。忧国忧民的老抗联战士,此时此刻,有多少牢骚和怨言在心里头憋闷着啊!
陈忠实原地不动地在桥头上呆愣了很长时间,直到宋希山和孙子的身影在视野中彻底地消失,才掂了掂肩膀头儿上的猎枪,舒一口长气,紧皱着眉头步下了公路。边走边沉重地思索着,哥哥提升副局长,与黑瞎子沟砍伐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背景和关系,仕途升迁,皆大欢喜,况且,以哥哥的资历、年龄、知识和气魄,当个副局长还是绰绰有余的,军官转业,老党员,年轻力壮,勇于开拓进取,“文革”期间又是造反派的批斗对象。蹲了“牛棚”,也坐了“飞机”,如今“四人帮”打倒,拨乱反正,全国上下抓经济,在各林场的基层领导中,提升哥哥为副局长,恐怕是组织部门再合适不过的最佳人选了。副局长,与进黑瞎子沟砍伐,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因果关系呢?自然保护区,是国务院审批,省政府明文规定的,大面积的砍伐,别说是副局长,就是局长、市长也没这么大的权力啊!走到河岸,夏立志看着他问道:“老宋头说啥?你们俩都愁眉苦脸的?”“唉!宋师傅说,林场要进沟采伐,采伐这片椴树林子?”“你哥哥来传达文件,不是说,黑瞎子沟是自然保护区了吗?还是国家级的?”夏立志不以为然地顺嘴说道。“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
刚传达完了文件就砍,这不是在跟自己过不去嘛!”陈忠实头不抬,眼不睁,目光紧盯着脚下的河面,水流湍急,深不可测,一步滑落,淹不死,也得变成只落汤的鸡。小心翼翼,不敢分神,嘴上应着,内心却想:回来背着猪肉,可怎么走啊?“操!当官的嘴,那叫屁眼子!朝令夕改,一天三样。唉!你们俩也是,干啥吃的不知道,半斤四两还不知道嘛?管那些鸡巴事哩!砍光了才好呢!不是你家的,也不是俺家的!闲吃萝卜淡操心,操白了头发,你老婆都会跟你俩心眼啦!小日本一来,我就知道,准他妈的没有好事!我也曾经多次说过,过去是军事侵略,目的是掠夺财富。如今呢?也是外甥打灯笼——照旧。科技侵略、文化侵略、经济侵略,跟军事侵略一样,都是为了掠夺财富。只不过是前者野蛮,后者文明,手段不同,目的却是一样的。陈大哥,这一会儿,你算是服气了吧?我敢保证,砍伐沟里的椴树,肯定与田井五木他们有直接的关系,不信呀,骑驴看唱本——咱哥俩就走着瞧。”夏立志洋洋得意,非常自信地晃着膀子说道。“你猜得很对!”陈忠实佩服地说道,“加工半成品,出口日本国,跟五木他们,能没有关系吗?小鬼子手段是真厉害啊!”爬上半山坡,听见了猪叫唤,俩人才终止了议论和交谈。
忠实顺手摘下来猎枪,提在手上,侧着耳朵,迎风听着沟塘子下面的风声和猪叫。顺嘴儿小声说道:“上来了,这帮傻家伙!别动,藏好,听见了吗?最少也有个二三百头!”夏立志说:“我就在这等着了!上去也没用,倒碍事巴拉的!”陈忠实说:“也好!可别乱跑呵!”说完,就拎着枪一个人悄悄地爬了上去。晴天,微风吹来,漫山的柞树叶子哗啦啦地山响。与夏天相比,尽管视野开阔了许多,但密密匝匝的枝头,不到近前,仍然是很难发现目标的。忠实机警地瞅了瞅山形,这儿与前次来找大棕熊的地方不很远,南北沟,混交林。阔叶树种多,针叶树种少,与大石砬子是同一条山脉。石砬下面,沟系的后堵,往往是猪群聚居的老巢。下雪后,猪群也不肯离去,躲在朝阳的地方拱贝母,啃扫条,生儿育女,调情寻欢。就是猎人和其他猛兽光顾,它们暂时逃走,过两天还会来的。这是群猪的活动规律,而孤猪就不同了。孤猪独居松穴中,嗑松籽、嚼塔子,三分天下有其二,除了狗熊,其他动物,是绝对不敢轻易造次的。
狩猎也有一定的规矩和说法,别说猎人,就是山里人也都知道:迎头不打猪,顺腚不打熊,群猪满山窜,孤猪守穴中。狍找窝风地,鹿卧岗鼻丛……忠实知道,这条沟系的周围附近,群猪成帮,孤猪分散。尽管回避孤猪,不到万不得已,是绝对不去招惹它们的。群猪不怕,越多越好,越多越有机会接近,越多越丧失了群体的战斗力和凝聚力。没事时忠实就常常琢磨,小兴安岭的野猪,跟中国人的性格差不多,群体好对付,一盘散沙,一击就破。而孤猪一人呢,则像亡命之徒一样,生死不怕。四万万多人口的泱泱大国,让小日本就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十多年。没有共产党的浴血奋战,小兴安岭,不还得是满洲国的疆土啊!正思考着,庞大的野猪群从上风头沟子的那边,像洪水一样,浩浩荡荡地蔓延了过来,“哄!哄!……吱!吱!吱……”打斗声、脚步声、拱地声、大嘴巴子的吧唧声、撞击树条子的哗啦声,在密林下面,铺天盖地般地往这边涌动着,声势浩大,势如破竹……迎头不打猪。
顺岗脊,提枪猫腰一步步地后退着。避开锋芒,从侧面击中,迎头开枪,前面的目标发现自己向两旁逃窜,后面的不知内情和底细,继续前涌,像战马一样,被其中一只撞倒,后面涌来的猪群,会把人活活给踩死的。这些经验和教训,都是前一辈猎人,用生命和鲜血总结出来的。迎头打猪,是猎人的一大忌讳啊!后退了有二三十步,躲在一棵粗大的桦树后面,既小心翼翼地端枪观察着。一头、两头、三头……十八头、二十三头……猪群庞大,最少也得有四五百头,哼哧哼哧的喘息声,仿佛闷雷一样,几里之外都能听得清清楚楚。走在最前面的排头兵是几十头小眼尖耳大嘴巴黑褐色毛眼发乌乳房擦地的老母猪,先锋官足有四五百斤,一马当先,齐头并进。边走边拱,边拱边吃,边吃边屙,腥臭味刺鼻,臊膻味打眼。后面的队伍不纵不横,乱糟糟地齐往前涌。大小不等,胖瘦不均,胖者屁股溜圆,毛眼贼亮;最小的像一只只大耗子,不知是饥饿还是疲劳,边跑边吱吱地拼命叫唤着。忠实知道:家猪一年两窝,猪五羊六。
而野猪呢,因为漫长的冬天太冷,体力消耗太大,身体只能维持而得不到补充,所以说母猪一年仅生一窝,入冬后发情交配,四五月生崽,当年的小猪,最大的也就是七八十斤,一般的四五十斤,赶上一胎十几只崽,最后的几个落渣儿,抢不上,受欺侮,到秋天时也就是二三十斤,活像大森林一只只奔跑着的大耗子……陈忠实手端猎枪,冷静地寻找着目标。老母猪不打,一是猪肉太老,半天煮不烂;二是猎人都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尽量不杀母性,留它继续繁衍。从飞禽到走兽,不撞在枪口上,是不主动猎杀它们的,当年的猪崽也统通放过,最大的七八十斤,除了头蹄下水还有啥呢?母猪保留,小崽不杀,而最理想的最佳目标是二三年的小猪。三四百斤,肉丝的味道鲜美也是离群成为孤猪最佳的前夕阶段。一旦离群,就不敢轻易去伤害它了。因上述种种原因,作为成熟的猎手,猎取目标是轻易很难选定的。而二三年的公猪,多数都紧围在即将发情的母猪后面,争风吃醋,时不时就会爆发出一场惊天动地的血肉大拼杀。去年秋天他曾经亲眼目睹过,两头五六百斤重的公猪在黑瞎子沟后堵决斗。脑袋对着脑袋,獠牙对着獠牙,皮开肉绽,血肉横飞,决斗从中午开始,一直到夕阳落山,厮杀中的哀叫声听上去震耳欲聋,而赶去围观,场面惨不忍睹。天黑返回,第二天再去一看,其中一只肠子流洒满地,早已停止了呼吸;而另一只呢,遍体鳞伤,全身血红。听见动静,才挣扎着吃力地爬了起来,冲自己晃了晃獠牙,眼睛是血红血红的,见忠实没有伤害它的意图,才吧唧了两下大嘴巴子,晃了晃尾巴,蹒跚着、趔趄着,像醉汉一样,歪歪扭扭地退回了大森林。
从此以后,在黑瞎子沟后堵,这头猪,就是独霸一方的首领了。猪群的运动和迁徙历来都是旋转式的,但不管哪一个猪群从此路过,所有发情期的母猪,交配权统通地归这只大跑卵子所有,而日夜跟随在母猪后面的小公猪,在这种公猪面前,只能眼巴巴地咽唾沫,要取得交配权,就得一次次地玩命拼杀,直到独霸一方的时候,过往的母猪,才能变成自己的妻妾,随心所欲,任意挑选。野猪跟其他动物一样,雄性只有占领了山头,夺取了领地,交配时才能取得公认的资格和权威。有不少年富力强的公猪,就是在一次次的搏斗中丧生的。所以说,经验丰富的猎人,就是枪法再厉害,见到独霸山头的大公猪,也要尽量回避,而绝不主动招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