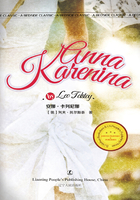但自己今天的所见所闻,是绝对不能让白大嫂知道的。不是陈静和夏立志的胡来,而是房后密林中的那条金伦蛇。他怕吓着白大嫂,还有她的女儿小囡囡。也许这条金伦蛇是在这儿暂住,或者是迁徙性地从黑瞎子沟路过。女人胆小,让白大嫂搬走她又没有路费,也没有条件。为了生活,就得在这儿苦熬着。一旦知道了实情,她和孩子,睡觉也不会踏实啊!想到这儿,忠实抓着她的胳膊,小声、又略有惭愧地安慰她道:“嗬!看吓得你!多贪了两杯,坐车又过了头。翻山过来,又迷了道,衣服就给刮碎啦!”说着,目光与目光就撞碰在了一起,“怎么?看把你吓的!陈静呢,陈静这两天还好吧?”他明知故问。白大嫂停止了哽咽,全身有些克制不住地颤抖了起来。三十似狼,四十如虎。作为寡妇,如果没有陈静,她早就投身到忠实的怀抱中了。特别是近两天她发现,陈静和那个小氓流,白天黑夜地纠缠在一起,隔着墙壁,就那么样的放肆和放荡。看得她眼珠子生疼,听得她耳膜都起了茧子。既然公开了,她白大嫂,也就没有必要为他们捂着盖着了。
开始她还有点为陈忠实难为情,替陈忠实抱屈。进而她又想,你陈静既然和夏立志乱来,给丈夫戴上了绿帽子!我白大嫂,比你还先来一步,为啥就不能做你们俩的第三者呢?明着不结合,暗中做个情人总是还可以的吧!想到这儿,她反手抓着对方的大手,气哼哼地既同情、讨好,又柔情万种地用颤音大声说道:“哎呀!你呀,可真是的!人家心里没有你这个大老黑,可你还处处想着人家呢!热死啦!快起来吧!赶紧进屋。我有老多秘密,等着向你传达呢!”说着,一用力,就把陈忠实拉了起来。自从白大嫂丧夫进沟,两人相识后,肉体的触摸,这还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尽管是手与手的接触,但异性之间,彼此也感觉到了对方的意念和情欲。
忠实的冷静和理智,并没有浇灭白大嫂全身上下刚刚燃烧起来的激情和欲火。刚一进屋,白大嫂就把那扇厚厚的木门给闩上了,动作敏捷,手脚利索。然而,她并没有奔扑过来,而是像小兔一样的绵善,羊羔一样的温柔,脸红如霞,目光似火,全身微颤,其眼神和表情,同时都在诉说着自己的迫切和渴望。半天,才自卑乞求又动情地喃喃说道:“我,给你,送来了!半年啦!我,时时刻刻地都在等待着……我,知道自己是个寡妇,没有权力跟人家竞争,可我心里头,却百分之百地爱着你呀!今天,我不想给你们俩制造矛盾,也不想说陈静和夏立志的坏话,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早晚有一天,你都会知道的……还有,你和陈静的事隔着墙壁,我也都听清楚了。不能怨她,可是……你,你也不能太苦了自己啊!”说着,她主动松开了裤子的纽扣,然后,她两眼微闭,把后背靠在了门板上,等待中,全身的皮肤,都像通电般麻酥酥地跳动着……奉献与牺牲,同时在一位母性身上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白大嫂的目光、语言和行动表露出的感情,作为同龄人的陈忠实早就感觉到了,不仅仅是现在,而是在他跟陈静举行婚礼前的一段时间。
从感情上说,相比之下,作为男性,他更喜欢和钦佩这个白大嫂。白大嫂朴实、贤慧、热情而又诚恳,生活讲究实际。实际上,在黑瞎子沟,白大嫂才是自己真正的意中人。志同道合,年龄相当,行动默契。再有,自己的性生活,也适应生过孩子的寡妇。可是,阴差阳错,加上陈静的主动出击,使自己就跟这个白大嫂擦肩而过了。事态的发展,不仅使白大嫂感到茫然和无奈,那些日子,遗憾中,自己也有点儿心酸和愧疚。但生米煮成了熟饭,婚姻可不是随随便便的儿戏呀!在黑瞎子沟这个特殊的环境内,陈静和夏立志的胡来,难道还用自己去制止和教训他们吗?一旦那条金伦蛇玩儿腻了……
反过来说,宇宙间所有事物都是平衡的,假若自己跟白大嫂胡来,难道说周围就没有其他的眼睛在窥视和观察吗?想到这儿,忠实冷静从容地思索着踱了过去,抱住了迫不及待的白大嫂,安慰她道:“你尊重我陈忠实,我陈忠实也真心喜欢你白大嫂啊!我喜欢吃你做的饭,更愿意看你出出进进、忙忙碌碌的身影。在黑瞎子沟蜂场,只有你白大嫂,才是我陈忠实的主心骨啊!可是,我,不能对你无礼,不能对不起死了的白大哥!咱们都是同行,都是靠蜜蜂吃饭的呀!大嫂,有陈静在,在我们没有解除婚约以前,我陈忠实,没资格,也没权力对您怎么样!”说着,他强忍住欲火,轻轻地躬下身子,为白大嫂提上了裤子。但他却又控制不住感情的闸门紧紧地抱住了白大嫂并俯下头去亲吻她。在亲吻中,两颗善良的心,又进一步靠近了。“您像一尊菩萨,对您的玷污,就是我陈忠实的犯罪!白大嫂,你,你就原谅我吧!为了放蜂,为了在黑瞎子沟常住……”
罪恶的深渊与幸福的陶醉,在生活中,往往产生在一念之间。久阳必暗,久暗必阳,月缺月圆,都是宇宙中的自然规律。这是康跃先在世时的一句口头禅。忠实牢记在心,尽管他是这一地区的最高统治者,他也要严以律己,来不得丁点儿的懈怠和放纵。白大嫂依偎着陈忠实,呼吸急促,目光茫乱,两手抓着他的胳膊,好半天,焚烧着的欲火,才一点点地控制了下去。对忠实的话,她似懂非懂,朦朦胧胧,但对他的人格和品质,从内心深处,还是非常的敬仰和信赖的。“也好!你,既然尊重我,我呀,也得好自为之啦!”好半天,她才喃喃地气喘吁吁地小声说道,“你,能理解我,我也就知足了!
能爱着一个人,不是缘分,也是福分噢!”“汪汪汪!汪汪汪!”听见狗叫,陈忠实知道是陈静和小夏回来了,往日,他们俩也是这个时辰进屋的。白大嫂略显尴尬和遗憾地笑了笑,迅速地吻了一下忠实,才含羞而又甜密地开门返回了自己的家中。她神态安静,脚步轻松,尽管没有得到忠实这个人,但精神上似乎是拥有了更多更多……刚刚进屋,就又被隔壁的声音牢牢地吸引住了。忠实的声音非常的严肃和冷静。“干啥去了!大热天的,又是晌午头子上?”忠实坐在炕沿上见陈静进屋就问。后者手上还攥着一把盛开着的野百荷花。陈静满脸的幸福和兴奋,步履轻盈,像跳舞一样,只是腰身有点儿滞钝。她像蝴蝶一样飞了进来,抓起了窗台上的一只空瓶子。听见声音,先是一愣,竭力掩饰住内心的恐慌,把头发一甩,笑着打招呼道,“哟!回来了,你?我姐咋没来呢?你们去伊春了吗?”“我问你呢?”忠实严肃地看着她,继续冷静地大声问道。陈静服装整齐,表情愉快大方,若不是忠实亲眼目睹她和夏立志苟且的那一幕,只看她从从容容的神态和口气,作为丈夫,还真就让她蒙骗过去了呢!
陈静毕竟是受过教育的人,从口气中,她很快就意识到了对方的无礼和冷峻。毫无疑问,肯定是隔壁的白大嫂走漏了消息或者干脆把她给出卖了。想到此,她略一沉吟,漂亮的眼珠子翻了两翻,内心迅速地拿出了主意和措施。来而不往非礼也,既然有人通风,秃头上的虱子——明摆在那儿,我也就没有必要跟你弯弯绕了。想着,她把手中的罐头瓶子“咚”一声重新墩在了窗台上,左手掐腰,满不在乎地歪着脑袋大声地反击道:“你审贼啊!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告诉你吧!采高粱果去啦,小夏我们两个!怎么的?干啥去了还得向你汇报啊!”喊着,也许是觉着自己理亏,喊了两句,底气就不再那么足了,但仍然是气哼哼不依不挠地,“这是我的人身自由!你是不是管得有些太宽了?你别以为,结了婚我就是你的私有财产了!封建的老脑筋,也该到换换的时候啦!”
见对方不语,就又继续把手上的野花漫不经心地插到了瓶子里面,爱美是女人的天性,但善于狡辩,也是女人的天赋。“采高粱果?哼!还采野花了吧?”忠实看着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的妻子,一语双关地反问道。“当然采野花啦!”陈静心安理得,不糊涂愣装糊涂地敷衍他道,“你不是已经看见了嘛!阴阳怪气的!干啥呢这是,野花家花的!散散心,溜达溜达!一天到晚,都快把人给寂寞死啦!憋闷死啦!采花还得受着你限制呀!”说着,又委屈般地突然把声音提高了八度,并摆出了一副理直气壮、破罐子破摔的泼妇劲头,“回来找碴儿打架呀!我该你的,还是欠你的啦!你这样对待我!”喊着、嚷着,也许是为了震住对方,也许是为了掩盖自己的恐慌,她忽然抓起瓶子,连花儿一起,“吧嗒”一声就摔在了地上。然后又扭扯着自己的头发,有声无调地号啕了起来:“这日子没法儿过啦!天老爷!我咋就这么倒霉啊!呜呜呜……”白大嫂过来了,站在门口,表情平淡默默无语,不是劝架也不是看笑话,而是用她含有特殊感情的目光,在期待中诉说着什么……
夏立志压根儿就没有进屋,而是在门外逗弄着三只小熊崽。此时,他的心情是复杂的,但也是阴险的。自从他与陈静勾搭成奸,出于本能,他就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一是离开黑瞎子沟,另找谋生之处;二是暗害陈忠实,用耗子药,像药死那条大蟒蛇一样。逃走他舍不得陈静。可是,若把陈忠实置于死地,也不是轻而易举的简单事情!偷情期间,他就说过:“妈的,我非把他整死不可!不然的话,再听见你俩搂着睡觉,我不自杀,也得变成了精神病!”陈静不以为然,美滋滋地用指头点着他的鼻子道:“哟!人不大,还挺有志气的呢!我是你大姐,陪着你玩玩,再胡说八道,我可真就不搭理你啦!胡来,蛮干,你有几条小命儿呀?再说啦,我比你大八九岁,等我皮松珠黄,你不得把我给一脚踹了啊!”陈静躺在他的身子下面,边笑边幸福地刮着他的鼻子道,“别忘啦!你还是个毛孩子哪!婚姻法规定,男性必须得二十二周岁才能结婚,再说你还是个三无户,我嫁给你,咱俩一对儿盲流,让我跟着你,喝西北风儿呀!”夏立志仔细想想也是:“那好!你先等着,等我落下户口,我再跟你正式结婚。不过,你不能再跟他睡觉……”
话没说完,陈静就欣慰地笑了:“行!不跟他睡觉,专门给你留着……男人,咋都这么霸道,这么个德性!”话没说完,两人就迷迷糊糊、不约而同地睡了过去。夏立志认为很正常,是疲劳过度得累晕过去。而陈静呢,凭着自己的经验和感觉,醒来后认为这是非正常现象。一是腹中的胎儿,使她不敢死活不顾地拼命折腾。二是野外“作业”,光天化日下面,毕竟是有点儿不雅,她把想法告诉了夏立志。夏立志说:“下次拿张狍子皮来铺着。这些天,我他妈的都习惯了,一到中午,就困得难受,干活儿没心,走路摔跟头,可是离开这块石头,就又咋也睡不着了。现在好说,冬天他妈的咋办呢……”夏立志刚刚下山,听陈忠实和陈静吵架,他就知道,两人的好事,肯定是让陈忠实察觉到了。做贼心虚的他不敢进屋,就只好硬着头皮,边逗弄三只小熊崽,边用耳朵倾听着事态的发展。心里头是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更像是突然揣上一窝小鸡雏,连抓带挠。盯着烈日下面自己的身影,嘴里无声地说:“该死该活吊朝上,随他的便吧……”陈忠实呢,开始的想法是:啥事我都看见了,也都知道了,你陈静也就不要再演戏糊弄我这个老憨了。咱俩是夫妻,特殊情况,你能认个错,我陈忠实就是不给你个台阶,也得睁只眼闭只眼地过日子呀!流产坠胎你自己遭罪,不流产不坠胎,早晚咱俩还不是夫妻吗?如今可好,踩着鼻子上脸,我不强究,你倒没完没了地闹哄上了。看陈静还在无泪有声地扯着嗓子干嚎,陈忠实真就急了。忽地从炕沿上站了起来,一步跨到门口处,伸手就拍在门板上,“哐”的一声,镶着的三块小玻璃也被震碎了。伴着破碎的玻璃声,他忍无可忍,怒气冲冲地大声吼道:“给老子演戏哪!妈的!”随着怒气冲天的一声吼叫,房上的灰尘腐草,也噼里啪啦地落了下来。
陈静的嚎声戛然而止,就像突然断了的电影片子。她扭头看着忠实,一脸的惊恐和惶乱。目光直勾勾的,脸色苍白,凌乱的头发揉搓得满脸都是。只见她张着大嘴,神态表情就像精神病又要发作了的刹那间。她全身颤抖着,额头与脖颈处有粒粒汗珠,一颗颗地滚了下来……事态的急转直下,无论陈忠实和一旁冷眼关注着的白大嫂,都是万万没有预料到的。吼声及门板与玻璃的破碎声,使夏立志扭头进屋,但他只扫了两眼,又一声不响、讪讪地退了出去。白大嫂的嘴角轻轻嚅动了两下,刚要责备忠实,但看见陈忠实的目光是那么严峻,表情又是那么冷酷,她又想丰沟之行,也许使他们夫妻间有更多的奥秘不宜公开吧?想着,白大嫂舔了舔嘴唇,也就非常知趣地退了出去。
夫妻吵架劝不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呀!白大嫂一走,陈忠实就略有歉意地轻轻说道:“哎呀!都怨我!看把你吓的!来,别害怕,别害怕!”他笨嘴笨舌地解释和安慰着,“本来嘛!啥事我早都看见了!可你就是不承认,还强词夺理!这事若换在你身上,你也不会容忍和原谅我的吧?”生气归生气,发火归发火,但生气发火都解决不了问题。可陈静的精神病一旦复发,黑瞎子沟蜂场,可就再也没有个清静的时候了。震碎玻璃,出了闷气,忠实心里头自然也就敞亮了许多。“你看见了?看见啥了呀?”陈静很快就稳定住了自己的情绪,把满脸的乱发猛地甩了两甩,满不在乎地继续抵赖道,“无事生非呀!平空捏造呀!说吧,你到底是看见啥了?说不清楚,拿不出证据来,今个儿,咱俩就算是没完!你以为姑奶奶是吓唬着长大的呀!”边喊,边瞥了外面一眼:小夏没有走远,还在继续偷听着呢!也许是为了给小夏撑腰吧,陈静有意识地把肚子冲着陈忠实努了两努,反守为攻,穷打落水狗般地:“说呀,咋不言语了呢?当着大伙儿的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