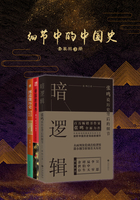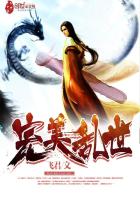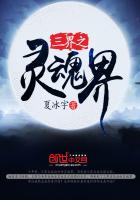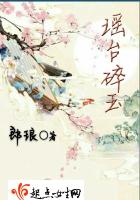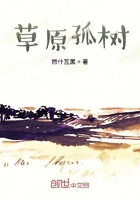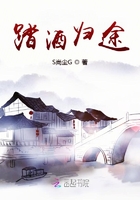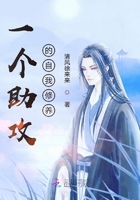老赵知道南方地势低洼,潮气重,军中已经有了疫情,于是想想就要退兵。他给曹彬等人的诏令是:要他们退屯二百里外的广陵(今扬州),在此地休兵,同时厉兵秣马,以为后图。老赵此意是不想两军你死我活血流成河,他宅心仁厚可以理解,但就战略家之责任伦理言,实为失策。金陵不是不可下,已经出师,再撤兵,以后再兴兵,军事成本会无形加大,更重要的是兵锋一顿师已老,往日威风不可得。故他的这个谋划遭到了卢多逊等人的反对。卢多逊多次劝谏老赵,打消这个念头。老赵固执地认为南唐人心稳固,兵多将广,短期内很难攻下,与其城下受挫,还不如主动退兵,两军都可避免过多杀伤。
这时候,扬州的太守侯陟因为收受贿赂被人检举,正在召赴京师。侯陟与卢多逊有私交,就派人到他这里来求情。侯陟知道金陵的攻守形势对南唐不利,卢多逊就教他来说江南事,争取让老赵改变主意,一旦攻克金陵,则侯陟坚定老赵信心也是一功。功过相抵,可以免死。果然,老赵召他,问他扬州不法事,但侯陟瞅准一个机会,即大言道:“江南平在旦夕,陛下奈何欲罢兵?愿急取之!臣若误陛下,可杀我三族。”
老赵听他话里有话,想想他又是来自扬州,应该熟知金陵形势,就屏去左右,召他升殿慢慢来说。侯陟将南唐目前的不利局面,从战略到策略,从大势到前景,分析一遍。老赵听了有理,竟将以前准备休兵的念头丢开,重新振作起来,决计继续攻取。而侯陟的罪过,也得到赦免。
大宋与南唐的心理较量正在令人晕眩的风景中展开。老赵一直在以武力为后盾,力争不战而屈人之兵;李煜则在考虑如何占据道义平台阻止老赵吞吐乾坤。紧张较量中,大宋、吴越联军在润州(今属镇江)与南唐一战,给了李煜刺激不小。
润州为古渡口,史称京口,地势险要,为金陵屏障之一。王师南下时,江南认为此地应有良将把守,于是想到了侍卫都虞候刘澄。刘澄乃是多年跟随李煜的人物,李煜登基之前,就在藩邸左右,得到特别信任。李煜将其提拔为润州留后。
临行,李煜对他说:“卿本来不应该离开我,我也很不愿意离开你。但此事非卿不能符合我的心思。”据说刘澄闻听此言流下泪来。他奉命辞别回家后,将家中金银玉帛全部带上,运抵润州。有人疑惑,他解释说:“这些东西都是吾主前后所赐,现在国家有难,我当散此以图勋业。”
国主李煜闻听后,非常欣慰。等他到了任所,不久就赶上吴越兵来。
部下向他汇报说:吴越兵初至,营垒未成,此际正好可以出兵掩杀。但谁也没料到的是,就是这个南唐后主李煜的老部下,已经心怀异志。他对部下说:“如果出兵,兵胜则可,不胜则马上被掳掠大败。救兵到而后图,战未晚也。”
这时,李煜又命凌波都虞候卢绛从金陵千辛万苦地突围而来增援润州,卢绛将士舟师八千人到京口,舍舟登岸,独自与吴越兵战。吴越兵稍稍后退,卢绛得以进城。
吴越兵重新来围。宋师丁德裕与吴越兵已经合为一处。卢绛与刘澄固守一个多月,互相就有了猜忌。刘澄此时已经向联军暗通了投降的约定,但他担心被卢绛谋害,于是找个机会对卢绛说:“有细作来报,说金陵受围日急。如果我们的都城都守不住,我们守润州又有什么意义?”
卢绛也知道都城早晚也会陷落,对刘澄说:“君为守将,不可弃城而去;可以赴难者,我卢绛耳。”
刘澄假装做出为难的样子,过了一会又说:“君言是也。”卢绛狠狠心,遂率众溃围而出。卢绛已经离开孤城,刘澄遍召诸将士,对他们说:“我刘澄守润州这么久了,决心不负国家社稷。但事势危迫如此,应该考虑生计,诸君以为何如?”
将卒闻言,皆发声大哭。刘澄见诸将如此忠心,担心有变局,也假装哭泣道:“我刘澄受国恩比各位还要深啊!况且我还有父母在都城,难道不知道’忠孝‘二字吗?只是力小不能捍御大朝耳!诸君难道没有听说过当初楚州之战吗?”当初,周世宗柴荣围楚州,久不下,等到城破,曾有血腥的屠城之举。此事在南唐人人皆知,刘澄以此来威吓诸将士。
在刘澄的胁迫下,润州降。
赵匡胤舌战才子
卢绛听说金陵危急,乃率众奔宣州(今属安徽),日夕酣饮为乐。有人劝他赶紧去救金陵,他不回应。他知道援救金陵与送死无异,但又绝不想投降。在矛盾纠结中,借酒浇愁。
李煜听到刘澄背叛的消息,应该有了绝望感。多年信任的一个人,居然心怀险恶--想想他守润州时将家财全部带出,那时就已经有了叛国的念头。李煜真是寒心。而卢绛不来援救的消息,也令他不安。卢绛,这是南唐名将凋零之后,少数几个可以托付的大将,他曾任枢密院承旨、授沿江巡检、拜上柱国,宋师来伐,又拜卢绛为凌波都虞候、沿江都郡署,出援润州,授昭武军节度留后。现在又赐宣州节度使。他不来援,金陵危矣!李煜了解到近一年来的败报,知道无法抵御王师。所有的侥幸心都在动摇。而李从镒也从汴梁回来了。他给李煜带来了宋太祖赵匡胤的亲笔诏书。这么多败报传来,刘澄、卢绛的不可靠,让他感到了绝望。李煜捧着老赵的诏书,有了归降的打算。但陈乔、张洎一个劲论“符命”所在,天不亡唐。况金陵古城有金汤之固,北兵不是那么容易攻取的,他们早晚会退兵。李煜对这俩人一向信任,这才中止了归降的打算。但是需要有人到汴梁去通使入贡,请求“缓兵”。李煜自信没有得罪大朝的地方,多年来一直小心翼翼地伺候着,如能说动老赵,可以效法吴越那样,为祖宗“血食”留江南一隅。南唐有个“高士”道人名周惟简,曾经穿着道服在宫中开经筵讲《周易》,官做到虞部郎中时退休。张洎推荐了他。说他“有远略,可以谈笑弭兵”。李煜于是再次召他为给事中,与修文馆学士承旨徐铉一同出使京师。
冬十月的一天,金陵城中通报宋师,说要派遣徐铉等人出使大朝,请开围放行。曹彬派遣了兵卫护送徐铉和周惟简赴阙。
徐铉乃是江南才子、一代名臣,有口才。当年的冯延鲁等人都对他的口才心存敬畏。这一次,徐铉也有抱负。想当年,冯延鲁凭三寸不烂之舌,说动太祖赵匡胤没有在平定扬州李重进后直接南下江陵;这一次,他也希望能说动老赵解围北还。如此,就是大功一件。何况,江南乃是徐铉桑梓之地,李璟李煜两朝待他不薄,知恩图报,他也有真诚效力的准备。甚至,对可能的不测,他也早就置之度外。史称徐铉“将以口舌驰说存其国,其日夜计谋思虑,言语应对之际详矣”。他准备了大段说辞,对这一趟艰难的苦差很自信。
汴梁这边也早就知道徐铉才气,于是有大臣很担心,预先对老赵说徐铉如何了得,如何博学,如何有才辩,应该有所准备。
老赵听后笑道:“你们不必多想了。这些事不是你们能知道的。”等徐铉来到宫前,立于庭上,果然就仰着脑袋宣言道:“李煜无罪,陛下师出无名。”老赵很从容地召他升殿,让他把话说完。
徐铉道:“李煜如地,陛下如天;李煜如子,陛下如父。天乃能盖地,父乃能庇子。李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过失,奈何见伐?”
大意如此,说了一堆。老赵待他说完,问道:“你既然说是父子,父子为两家人,两处吃饭,可以吗?嗯?”徐铉没有料到会有此问,一时语塞,不能答对。欧阳修撰《新五代史》论及太祖此语,甚为欣赏。他说:
呜呼,大哉,何其言之简也!盖王者之兴,天下必归于一统。其可来者来之,不可者伐之;僭伪假窃,期于扫荡一平而后已。予读周世宗《征淮南诏》,怪其区区攈摭前事,务较曲直以为辞,何其小也!然世宗之英武有足喜者,岂为其辞者之过欤?
我赞同欧阳修这个意见。“王者之兴,天下必归于一统”,乃是吾土“分久必合”的大势。可以将这个意见视为“历史有机性”。老赵平生不喜欢作伪,一言既出,已经判定“江南无罪”。但“无罪”在“一统”之前,必须让位,此中大义,与最大可能争取族群之生存空间有关,故权力之合法性来源之一就是武力征服。当年柴荣讨伐南唐,下《征淮南诏》,数落南唐种种“罪恶”,包括招降纳叛、勾结契丹等等,看上去义正词严,但还是不及老赵更为恢廓真诚。当着族群命运有可能趋向“一统”之际,割据,就是“有罪”。但老赵无暇多论,但以“一家人不吃两家饭”俗俚之语解之,反而收到“棒喝”之功。这也是化解夹缠不清之大匠法门,允为老赵一赞。
欧阳修语译成白话,韵味会消减,大略为:呜呼,说得真是大气啊!他的话说得多么简练!王者的兴起,天下是一定要归于一统的。可以招徕归附的,就招徕他们;不能招徕归附的,就讨伐他们;僭位窃取帝王称号的,定当扫荡一平而后作罢。我读周世宗的《征淮南诏》,怪他区区计较南唐以前的事,务要比较是非曲直作为托辞借口,气量多么狭小!但周世宗的英武有足可值得人赞赏的地方,也许是替他写诏书人的过错吧?
传说徐铉不死心,向老赵开讲李煜的才艺,说李煜的《秋月》诗如何如何美妙(可惜此诗今已不传)。老赵听后大笑道:“这个《秋月》不过是寒士诗,我是不作这种诗的。”徐铉不服气。说你不作这种诗,有能耐也作一首跟月亮有关的诗试试,看看可比俺家主人更棒。老赵笑笑道:
未离海底千山暗,才到天中万国明。
徐铉听罢大惊。他从这两句诗里听出了“一代英主”的襟怀,不得不拜服。老赵解释说,这不过是年轻时在各地流浪,醉卧田间,偶然所作。
宋陈岩肖《庚溪诗话》评这两句诗说:“大哉言乎,拨乱反正之心见于此诗矣!”但明胡应麟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这两句诗实是“俚语偶中律耳,弹压徐鼎臣(铉),自是贵势,非以诗也”。(《诗薮》)二人所见不同,我是欣赏这两句诗的,感到就纯粹审美而言,也很壮丽,应该属于唐人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评论的“雄浑”风格--“雄浑”在司空图那里居诗品第一。
又据《庚溪诗话》说,老赵微时,曾有客作《咏初日》诗,“语虽工而意浅陋”,老赵不喜欢,客人就请老赵来作。老赵应声曰:
太阳初出光赫赫,千山万山如火发。一轮顷刻上天衢,逐退群星与残月。
按《庚溪诗话》的说法,宋朝“以火德王天下,及上登极,僭窃之国以次削平,混一之志,先形于言,规模宏远矣”。
老赵虽然没有答应“缓兵”,但是对待徐铉等人与没有发兵之前一样,礼数周到,温文尔雅,很友好地将他们送回金陵。
这一年,大宋攻取润州,更名为镇江军。这应该是江苏镇江得名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