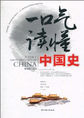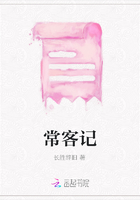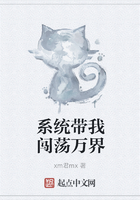老赵一句“宁不得江南,不可辄杀人”令多少史家学者为之赞叹!他还曾屡次下诏给大将曹彬,即使不得已巷战,也不能伤害李煜一家。但天命在兹,历史的神秘余数引导着大宋的将军与士兵,南唐的终结已是冥冥注定。后主的亡国之痛,也因他富有才情的词句而凝结为凄美的永恒。
历史的神秘余数
赵匡胤送走了徐铉等人,金陵之围又开始了攻城的准备。李煜知道徐铉等人请“缓兵”无效,只好继续招募民兵,同时下令南都太守柴克贞速去接管湖州,又邀朱令赟宁肯弃湖口,也要速来救援。同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招募民兵。
南唐的“民兵制度”别有特色。当初,先主李昪时,曾经有过“量田”,就是农田户口的调查,以此来规定庶民的赋税和杂役。当初规定:缴纳赋税达到两缗以上者,家出一卒,这些民兵组织起来有个番号,就叫“义师”。此规定意味着缴纳赋税达不到两缗者,不用服兵役。故能够服兵役的,应该是境况较优的人家。如果两缗以上人家又有分家,分出的家庭又达到两缗,则再出一卒,番号为“新生拟军”。民间有新置物产者也出一卒,番号为“新拟军”。又有三丁抽一卒的民兵,番号为“国军”,后改为“扳山军”。地方杂牌军,统由“物力户”也即有钱的大户人家为“将校”,负责日常管理。
中主李璟时代,曾鼓励郡民端午节划舟竞渡,官方给竞赛奖金,让各郡两两比赛,最后决出冠军和最后一名。优胜者加以银碗,谓之“打标”,这些人全部登记其名。到了后主李煜时代,这些“打标”的人物,全部调来成为民兵,番号为“凌波军”。
后主李煜时,又搜罗民间底层人物,如佣奴、赘婿之类,也组织起来,番号为“义勇军”。同时再告知有钱人家,让他们自备日用和军服、兵器,让他们招集无赖亡命之辈,番号为“自在军”。凡此种种,史称“民应之者益多”。到金陵被围后,李煜要张洎写了诏书,用蜡丸送往契丹求援。又写了好几篇战争动员令,送往境内各地,广招百姓,老弱不算,凡是能拿得起兵器的就来参军保家卫国,番号为“排门军”。
这类名号总有十三等,都派遣到边境各个要塞登城把守。直到一年后,金陵城破,这些杂牌军人才得以回家务农。
南唐士庶对捍御王朝有自觉性和积极性。说到底,南唐不是一个无道邦国。
但赵宋要比李唐强大得多;曹彬要比唐将强大得多;中原气势要比江南气势强大得多。李唐虽然兵多将广,人心无二,但气数已尽。“气数”,这个东西不是“因果”,不是“规律”。它由无数的偶然性组合而成,各种偶然性聚变为一种奇异莫测的气场,昭示了某种进入惯性轨道的趋势,不可变更。
一般以为“气数”“天命”这类传统史学观念是一种“落后”的“巫术”思想,但是考察现代历史哲学,就会发现,自新康德主义以来,没有什么人愿意讲述“客观”的“规律”史学,相反,人多信任神创论或偶然力量。
符号学家、史学家罗兰·巴特在他的《结构主义选读》讨论“历史的话语”时,就明确说:从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开始,历史,是史学家个性化表达的结果。希罗多德的叙事结构就表现了“一种特殊的历史哲学--倡举由人、处置由神”(可以想一想“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中国式说法,二者何其相近)。而在评价大史学家米歇莱时,巴特说:他在严密组织起来的概念和形态的对比中,“其结果意味着摩尼教的生死观”。
另一个历史学家雷蒙·阿隆在他的《历史哲学导论》讨论“历史规律”时,更认为往事构成的历史,不存在所谓“规律”,因为历史“不可逆”,更“不可再现”。他提出了“神秘的余数”这个概念。可能存在着“另外一种更高级力量的支配”,可能存在着“来自最高权力的命令”,而所谓“规律”“因果”这类讲述往事的概念,经由分析“所显示出来的神秘余数,也就全然不同”。因此,也就不存在所谓“规律”;而“因果”也各有各的不同。因为往事不可逆,故任何分析都不可能穷尽一切,一定在所有的分析完了之后,会发现不同类型的无法解释的剩余部分,这就是“神秘的余数”。
气数、天命、天道等等,就是历史的神秘余数,不可穷尽。李煜的南唐富庶程度不亚于中原大宋,文明程度不让于中原大宋,将士兵卒不少于中原大宋,但它从一开始,就没有与大宋抗衡的气势。这不是“历史规律”和“历史因果”可以解释得了的问题。无论诉诸何种解释或分析,总有解释不清、分析不清的存在。历史规律或因果,在分析中,不可整除;一定会有余数。这些余数就像π一样无限不循环,没有规律。历史是一个无理数。
更神秘的是,如果有老天爷,老天爷也不在南唐这一边。
朱令赟援助金陵
陆游《南唐书》载:“王师采石矶,作浮桥成,长驱渡江,遂至金陵。每岁,大江春夏暴涨,谓之’黄花水‘,及宋师至,而水皆缩小,国人异之。”此事仿佛“天助”。
朱令赟来援金陵也同样神奇得很。大将朱令赟几乎带着悲壮的使命感,从湖口(今属江西九江)率大军赴金陵,号称十五万众(这个数字显然夸张)。他需要沿江东浮八百多里,经皖口、池州、铜陵、芜湖,而后到采石矶。过了采石矶,才有希望到达金陵城下。而这一路上,宋师早已安排好了“打援”的部队。朱令赟大有“过五关斩六将”的慷慨。他把巨大的木材捆绑在一起建造水筏,长百余丈;他乘坐的主力战舰能够容纳千人。他已经做好战役准备,浮江而下直趋采石矶,焚浮桥,将宋师一分为二。这样就可以分别击破曹彬、潘美。此前一直在涨潮,等到他准备东下时,江水开始下降,大型战舰一时不能通过。
宋将王明军屯独树口(今属安徽安庆),闻听朱令赟整军而来,多少有些心慌,急忙派遣他的儿子乘快马将情报送到汴梁,并请求朝廷赶紧增造大船三百,来袭击朱令赟。赵匡胤复诏道:“你这个主意不是应急之策。朱令赟早晚到了金陵,宋师之围就完了!”于是给他密令,要他在江渚洲岛之间,多多竖立一些高大的木头,排列起来就像帆樯的样子。这样,朱令赟看到,就会怀疑有伏兵,可以迟滞他的行动。
果然,朱令赟远远看到“帆樯林立”时,就开始逗遛,他需要细作前去侦察。恰好江水浅涸,不利旗舰之行。他这一缓,就给宋师留出了时间。等他摸清情况,再度东下时,宋师已经做好了准备。
朱令赟待潮水上涨,乘巨舰高十余重,上建大将旗幡,浩荡而来。到达皖口(今属安徽安庆)时,宋师行营步军都指挥使刘遇,开始聚兵打援。他的任务就是截断西面援军,要曹彬放心围城。刘遇乃是后周郭威时期善战的老将。他与朱部一时遇合,难分胜负。朱令赟早有准备,看好风向,令士卒放起火来,直烧刘遇大军。刘遇不敌,正打算退守,不料忽然变了风向,南风转北风,大火反而向朱师烧去。朱师不战自溃。朱令赟全然没有料到风向会变!除了天意,他无法解释。这一场败仗意味着南唐期盼的援军再也不可能到达金陵城下。朱令赟一时陷入绝望,不禁万念皆灰。当大火烧到旗舰时,他在惶恐中镇定地走向了船头大火。刘遇反败为胜,生擒湖口战将多人,斩杀无数,缴获兵仗数以万计。史称“金陵独恃此援,由是孤城愈危蹙矣”。
刘遇,性格淳朴、谨慎,待士有礼,善骑射,宋太宗赵光义时,镇守滑州。有一天早上起来,正对客人说话,忽然感到脚下的旧疮疼痛。门下医生对他说:“这是有火毒。火毒不去,故痛不止。”刘遇当即解衣、取刀,割疮至骨,曰:“火毒去矣。”谈笑如常时,过了十多天,脚疮痊愈。也是奇人一个。
赵匡胤“按剑”对徐铉
徐铉等人回到金陵后,李煜想想不成,再一次派遣他们出使汴梁,务乞宋兵“缓师”。按规定,南唐来使,大宋要有人去接待,迎接、陪伴、送客。但宋廷皆知徐铉口才了得,没有人愿意接待他,以免遭到羞辱。有人告诉宰相,宰相也找不到合适人才,就来请示老赵。老赵让人将宦官中不识字的十个人报上来,然后用笔点了其中一人说:“此人可。”
廷臣都很惊愕,负责接待的侍者都不知道老赵啥意思。但也没有办法,只好派这个不识字的宦官前往接待。
一路上,宴请、陪坐、同行,徐铉是词锋如云,高谈阔论,旁观者听了都“骇愕”,就等着这个不识字的宦官答对。不料,这位宦官啥也答不上,史称“徒唯唯”而已,就是哼啊哈的,答应着而已。徐铉也不测此人深浅,跟此人聊了几天,没有任何回应,最后的结果是“倦而默矣”,累坏了,懒得说话了。
公元975年的冬天,距离上一次徐铉出使之后一个多月,徐铉再一次与太祖赵匡胤在便殿对话。
徐铉几乎是在哀求老赵说:“李煜事大之礼一直非常恭敬;但现在是真的身体有病,不能前来汴梁,并非拒诏。请求大朝缓兵,以此成全一方之命。”说话的言辞甚为恳切。
老赵开始与他谈论天命、一统。但徐铉越说越严肃起来,他带着书生之见,以为李煜没有得罪大朝之处,老赵没理,应该“缓师”。最后惹恼了老赵。史称赵匡胤“按剑”对徐铉道:
不须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乎?
徐铉这才明白:现在不是在“讲道理”而是在“论武力”。当他忽然懂得这个道理时,所有的口才、智能,都已经不敷使用。于是惶恐而退。老赵又来诘责高人周惟简。周惟简看这阵势,就更害怕了,名士之风顿失。他对赵匡胤道:“臣本居山野,没有仕进之意,是李煜强遣臣来此地。臣素闻终南山多产灵药,他日愿意到终南山栖隐。”
赵匡胤听他这样说,也很感动,史称“怜而许之”。最后还是给了他们厚厚的赏赐,放还金陵。
宁不得江南,不可辄杀人
宋师对金陵的包围,按照部署,潘美独当北面。围城部署完成后,曹彬按军规派使者将围城图呈给汴梁。赵匡胤对使者指着图上的潘美大寨说:“这里应深挖壕堑,警戒江南军来夜袭。你马上告诉曹彬,要快!”
为了节约时间,老赵马上安排使者吃饭,同时要枢密使楚昭辅迅速起草诏书。诏书写好,使者饭也吃过,立即回返复命。
曹彬接到诏书,亲自监督丁夫在潘美大营周遭深挖战壕,加固工事。在一个寒冷的冬夜里,南唐出动了五千将士来袭击潘美营栅,每人都拿着一柄火炬,接近后,炬火点燃,鼓声大噪,但在深沟壕堑前被迟滞。曹彬、潘美以逸待劳,趁势反击,全歼来犯之敌,生擒将校十余人。
金陵被围已经将近一年。曹彬记着太祖的嘱托,没有纵兵杀掠,用兵不狠,故久久未能破城。城中已经用光了柴薪储存,粮食也开始紧张,城外援兵相继被宋师击破,守城物资出现匮乏。曹彬等人一面加大了攻城力度,一面期盼着李煜早日投降。曹彬还给李煜多次写信,对他说:“城是一定会被攻破的!应该早一点考虑后路!”后来李煜复信,答应让自己的儿子清源郡公李仲寓“入朝”,也就是去做人质。这样,也是一个姿态,如果有这个姿态,曹彬也可以“缓师”。但李煜答应的这件事,却迟迟不来兑现。曹彬每天都派人去督促李煜,并复信说:“郎君仲寓不必远行到汴梁,只要先到我的大营,我们就全面停止攻城。”但李煜被身边的人所左右,无法做主,无法决定投降归附大计,给曹彬回信说“仲寓还没有准备好行李”,以此来推脱。
曹彬、潘美等人虽然焦躁,但老赵有死命令:不准滥杀无辜。所以二人攻城始终不敢使用毒辣手段。期间,老赵还多次发来诏书,反复晓谕曹、潘二人:“勿伤城中人!江南将士若犹困斗,李煜一门,切勿加害!”
二人思量来思量去,攻城如果不杀人,无法威慑金陵,于是给老赵发去了一封奏章,内中称:
兵久无功,不杀,无以立威!
史称太祖览之赫然震怒,在这份奏章后面批示了十二个字,字曰:
朕宁不得江南,不可辄杀人也!
记录的这句话见于宋人朱弁《曲洧旧闻》。朱弁对此评论道:“大哉,仁乎!自古应天命一四海之君,未尝有是言也!”真了不起啊!仁义!自古以来顺应天命、统一四海的君王,从未有过这类话语!儒学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的说法,与老赵此语同为“敬畏生命”的圣贤理念,值得为之浮一大白!曹彬知道,自从断了城中樵采之路,整个金陵都已经陷在炊烟难举的苦境,继续拖延下去,大批老弱将会冻饿而死。于是,决计加快攻城步伐。他确定了破城的日期:十一月二十七日。
宋师人人皆知:十一月二十七日破城!
曹彬的治病良方
自五代以来,破城之后即“纵掠”的积习,开始在围城达一年之久的将士中蠢蠢欲动。很多老兵、宿将,都曾在过去的岁月里有过“靖市”或“夯市”的历史,他们知道,那是一生中最“爽快”的日子。看着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剑锋刀刃下哀告求生,看着一个个体面的官绅颤抖着贡献出多年积蓄的黄白之物,看着一个个年轻的女人含羞忍垢听凭暴力欺凌侮辱……他们有一种渎神或败德的满足感。一种潜藏于灵魂黑暗之处的破坏欲望,让他们感到黑色的力量居然也那么迷人。他们愿意“享受”这个感觉,在恣意的毁坏中也同时自我毁灭。欲望,破坏的欲望,是给他们最切实的补偿。那是无数个刀头舔血日子的红利。破坏的欲望,如大海般汹涌,他们愿意在这一片汪洋大海中载沉载浮……但是老赵不允许。曹彬越来越感到执行老赵“慎勿杀人”的诏令难度太大了。尽管他已经知道李煜被左右架空,难于决断,他还是连续不断地给他发去了传告。他告诉李煜破城的日期,并告诉他“大军决取”金陵,是没有疑义的!十一月二十七日,这个日期,不可变更!请李煜“早为之图”。
从仲冬下旬以来,曹彬每天都给李煜发一份简报,告诉他大军准备攻城的消息,敦促他尽快决断,甚至,可以将早先说好的,将李仲寓送往我曹彬大营之后,一切好说。但直到日期临近,李煜还在拖延。
陈乔、张洎等人对李煜说:“金陵古城,固若金汤,天象也没有变化,意味着天命未必变更,哪有计日而破城的道理?这是敌人诈取之言,不可信。”
李煜于是回信,告诉曹彬:“仲寓还是没有准备好行李等等,宫中还需要宴饯送行,准备就在二十七日出城。”
这个意思其实是不相信曹彬会在这一天破城。如果这一天城不破,即等于屡屡告知的当日破城为假,如此,我送儿子到营,也可以不真。
但曹彬回信很肯定,也很诚恳:“即使提前一天,李仲寓到二十六日出城,都来不及了!”
李煜还是不信。这期间,赵匡胤的诏书也不断传来,主旨就是不允许杀害无辜。如果不得已巷战,也不能伤害李煜一家。曹彬规定了日期,做了细密的技术准备后,各种攻城器械都已经准备完毕,床子弩、抛石机、攻城塔、冲撞车、头车、飞桥、望楼车……都已经各就各位;神臂射手也已经处置到位。
“床子弩”,那一天,会取仰射角度精准地射向城堞女儿墙的空隙。只要那里有守军,粗大的箭杆就会将他的脑袋射飞。
经过计算,专门砸向城堞后面的大型“抛石机”,被安排在几个大门楼子前。巨大的石块早已备好,这些石块将从抛石机上远远抛出,会精确地落下,砸死或砸伤守城士兵。
与此同时,工兵和丁夫们会运来一袋又一袋的泥沙、一捆又一捆的柴草、一根又一根的原木,用以填平几处壕堑。而后,就有带滑轮的“飞桥”被迅速推来,由绳索控制,搭载在壕堑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