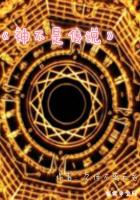楚尧说:“还有六七个小时就天亮了,你好好休息,我去货舱看看。”他套上风衣,点了一根香烟便走了。
他走后,小小的舱室宁静至极,天地间只有浪涛声和机轮声,还有,泊菡自己的呼吸声。
舱室里四壁油漆斑驳,却很清洁。楚尧自己的物品,一个大樟木箱放在墙角,上面刻着部队编号、姓名还有上海的家庭住址。箱子旁边有个装了搪瓷脸盆和电炉的网兜。
舷窗下的小桌子上,整齐地叠着书报杂志,墨水瓶一尘不染,钢笔无比妥当地插在笔记本上,可以想像在驻地的楚尧,平时住的地方也是这样干净整齐,所有的东西都一目了然。
这里是楚尧全部的身家,万一哪一天他不在了,也不会给收拾遗物的战友增加工作,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收到一个樟木箱子里,然后寄到上海。
他是英雄,就算面对死亡的阴霾,也努力维持最后的尊严,不给别人添麻烦。
泊菡怔怔地发了一会呆,越是看懂他,她就越舍不得离开他。
可是,命运给了她一个困局,她要是和楚尧在一起,楚家会是什么情景:婆婆还是婆婆,楚舜要变成她的小叔,念念变成她的侄女……多么荒唐的事!
她赶紧摇摇头,把这么可怕的想法忘掉。
泊菡从行李箱取出自己的用具,在舱内的盥洗间里整理好卫生,突然胃里翻腾起来,像是要呕吐,她先是疑心自己晕船了,还摇摇晃晃地跑出去拿晕船药,结果药还没吃上,就吐得呕心呕肺,几轮过后,额头上也起了高热,浑身发冷。泊菡在高中时学过红十字救护的知识,现在的症状很像急性胃肠炎。
她忍着难受打扫干净盥洗间,又取了楚尧的脸盆放在床头,靠在床边脱了力,等待着下一次翻腾的到来。
房门再次被打开,楚尧裹着一阵咸腥的海风匆匆进门,他一看泊菡脸色腊黄,床头还摆着脸盆,立刻明白泊菡也像船舱里的士兵一样,因为吃了不洁的饭菜,感染上了急性疫症。
伸手摸了她的额头,烧得滚烫。可船却医少药,更可恶的事,这艘破军舰的锅炉还罢了工,轮机长也是上吐下泻,没有力气来维修锅炉,供热断了,舱室里越来越冷。
舰上一个懂医术的学生兵说这样的急症千万不能脱水,否则会造成电解质紊乱引起休克。楚尧拿起热水瓶倒水给她喝,泊菡制止他:“水要烧开,怕不卫生。”
他点上电炉烧开了水,等着吹凉的过程,泊菡又吐了几回,喝些水好了点不吐了,可额头滚热,手脚冰凉,一个劲地叫冷。
睡了好久好久,泊菡觉得手脚微汗,身子暖和过来,烧也退掉了。白天的光明从舷窗之外照射进来,驱散了空气里湿漉漉的寒气,暖气也嗞嗞响着,开始恢复。她动了一下,发现这一晚她竟是和楚尧贴颈而眠!
身上的旗袍已经脱去,和楚尧的夹克一起丢在床尾。只剩一层薄薄的贴身裙子,楚尧更过分,半裸着胸膛,穿着背心,一双肌肉虬结的臂膀紧紧地抱在她的胸前。
泊菡一动,楚尧也醒了,拿手摸摸她额头,声音有些疲倦:“退烧了。感觉好些了吗?”
泊菡满心羞愤,手肘用力向后一击,想挣脱他:“你滚开!”她对他,用了粗鲁的口气。
楚尧在她身后痛得直抽凉气,听声音不像是装假,泊菡转头一看,他抱着肚子,一脸痛楚,嘴里说着:“你真狠,想要我的命?”
泊菡不相信自己的一击能有这么强大的效果,扒开他的手一看,脸又变得雪白,他腹部缠着纱布,正朝外渗着血水,那浓浓的殷红色,不是假装出来的。
“你……你受伤了?”她慌得明知故问,听说过他有伤在身,只是看他好好的,以为不碍事,现在才知道根本没有痊愈。
“你躺好,我帮你看看。”
楚尧却夺了她的手,满脸竟是讥嘲的冷笑:“哼!你是不是以为我轻薄了你?”
“你没有吗?”泊菡把视线从他裹着纱布,依旧能看出块块肌肉的腹部挪开。
“你自己冻得发抖,一个劲朝我怀里钻。衣裳也是你自己吐脏了,我没办法才脱的,至于你想像出来的轻薄,我只关心你的病情,其余的还无福消受!”楚尧难得对她这么凶,泊菡再看仔细了,他裤子战靴一件没脱,皮带扎得牢牢,根本不是登徒子的样子。
泊菡惭愧难当,窸窸窣窣地解开纱布,揭到最后一层,一处狰狞的伤口出现在眼前,刚刚结了痂的一处被她击碎了,渗出鲜血。
她从未见过枪弹的伤口,现在才知道皮肤碎裂是什么样子,那伤口只要再差个几公分,她都没法见到眼前的人,她吓得头发晕,手发抖,楚尧却握住她,挑着眉道:“说错话,做错事,怎么都没有一句道歉。”
泊菡愣了一愣,然后真心地说了一声:“对不起。”
楚尧嘴角一歪:“没关系。”显然,他故意在戏谑自己。
她正要抗议,楚尧却布置了任务:“木箱子里有纱布和药,你帮我重新上一下。”
泊菡拿出在红十字会学到的全部本领,在楚尧的指导下,终于完成了上药包扎的工作,最后还拿纱布打了个漂亮的蝴蝶结。忙完出了一身细汗,那突如其来的胃肠炎也好得差不多了。
“帮我解开,给别人看到像什么话!”楚尧看着前腹上面的花结,挑着眉抗议。
“怎么不行?如果有笔,我还可以在上面画画呢,”泊菡若无其事地说,“又不影响包扎的效果!”
楚尧从挂着的风衣口袋里拿出一支原珠笔,递给泊菡,促狭地将她一军:“画啊!”
泊菡只是随口一说,现在倒是下不来台了,真的画吗?她不愿意认输,脑子里闪了好多方案,又一一否定,看着楚尧靠在床头睨视着她,就接过笔来,在纱布上写了一排“章泊菡到此一游”,配上一圈小花边,洋洋自得道:“好看吗?”
“这么幼稚?”楚尧再一次挑起眉头。泊菡以为他还有什么话要教训她,可是,他却没有,像个任由小妹妹胡闹的大哥哥。
可慢慢的,大哥哥宠溺的目光变得有些发紧,喉头也不安地上下动着,泊菡被看得莫名其妙,突然意识到了问题,低头瞧了瞧,自己的薄裙肩膀滑脱了一角,露出了雪白的肌肤。
她面颊顿时着了火,赶紧拉好衣裳,可楚尧已经像猛虎那样扑上来,要亲吻她,然而,他的脸色变了,急速冲下床去,冲进盥洗间,过了好久才从里面出来,面容苍白,努力摆出轻松的表情:“不好意思,我也中招了!”
楚尧的病程发作很快,他身体一惯强健,一但被击倒,就是大病症。上吐下泻,高烧不止,只是他坚持自己处理,不肯麻烦泊菡。
泊菡只好不停地烧着开水喂他,不能让他脱水,可刚刚喂进去的水都被楚尧喷射性地吐出来,最后竟吐出幽绿色的胆汁。
泊菡怕得不行,她不能出去求救,楚尧现在昏昏沉沉的,也没法自救,说不定走出去一个趔趄就掉进海里,现在,楚尧的一切,都靠她了。
他烧得越来越高,脸色赤红,嘴唇枯白,慢慢地陷入呓语。冷毛巾冰头也没有什么用处,泊菡触到他的皮肤,滚烫得灼手,想来想去,也只有最后一个法子了。
她费力地脱掉他的战靴,红着脸解开皮带,除掉裤子,然后用力地把他推着后背贴紧了舱壁,利用舱壁给他降些温度,把几条冷毛巾和水杯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自己抱紧了楚尧。
女人血气不旺,天生肌肤清凉,一到冬天更是手脚生寒,泊菡就是拿自己当着个降温的冰袋,来拯救她的楚尧,把他那一颗滚烫的头颅,安在自己的怀里。
除了丈夫,她从没有想过还能和别的男人这样肌肤相亲,只不过现在怀里的他,老实得如同一个沉睡的婴儿,平日里充满力量的身体,现在又重又软,压在她身上,只有如影随行的烟味和专属于他的气息依旧蓬勃而出,很是诱惑。
他与楚舜完全不同,楚舜的身上,永远是干净,温和,纯粹的味道,像阳光下晒过的旧毛巾,是家人,亲人的味道。楚尧不一样,他身上也有爸爸和哥哥那样亲人间可以安心的气息,但更多的是一种陌生的,带着咆哮,带着力量,随时可以让她迷失心智的魅力。
泊菡好像看到了一些画面,顿时脸红心跳,她有心想抽身离他远一些,却拿不出丝毫的力气。
每隔一刻钟,泊菡起身给楚尧喂一勺水,额头换一次毛巾,他渐渐止了吐,却昏睡不止,根本不知道他爱着的女人,正玉体横陈在他怀中,要一点一点地渡出他的热度,把生气还给他。
反反复复折腾了十五六个小时,又是深夜,泊菡已累到精疲力竭,楚尧却连呓语也没有了,喉咙里光是喘着粗气的声音,好像要咽气了一般。泊菡抱紧了他,泪如雨下:“你要挺过来啊!你看我都好了,你那么强大,怎么就这么没用呢!”
楚尧就像睡着了那样一动不动,泊菡拧他的胳膊,拍他的脸,他都没有知觉,任她揉捏。
泊菡抱着楚尧,又是哭,又是亲吻他,一颗颗晶莹的泪珠洒落在他的脸上身上:“这里到底是天堂还是地狱?我求你快好起来,只要你能好,要我做什么都行!”
她难以置信,不知道命运和她开的是什么玩笑,昨天还相亲相爱的两个人,今天就要天人永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