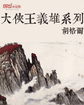画作参展的那几日,兰诺在夏妍的邀请下去她家做客。那是位于小河直街的一处古旧的老房子,附近的居处有着浓郁的江南水乡特色,因为湿气较重,白墙上爬满青灰色的霉斑,房屋依水而建,人自然也是傍水而居,错落繁盛的乔木,雨后尤其的绿。
周围的房子虽然有很多地方做过整修,但外观上基本还保持着原本的旧貌风格。夏妍家的房子地处偏僻,也同样保留着原始的风貌,行走在杭城的小巷小弄,与当街上的人擦肩而过,眼处所望,捕捉到的尽是古朴毓秀。灵动的雕花隔窗,木楼,青苔,白墙,屋檐后倾泻而下的爬山虎的藤条,叶缘微漾,错落繁盛的叶片覆盖在墙面,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墙外正开的白玉兰,散发微微的香气,磬钟状的花蕾,颜色透白如玉,花香清雅温和,一如杭城女子温婉的性格。
杭州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终年多雨,空气湿度较大,随处都可见到葱绿的植物与乔木,略旧一点的老房子上总有爬山虎的印记,历史建筑与传统文化相融汇,生活气息悠然镶嵌,阳光斜射的院落,寂静如常。
想来,我也是极喜爱这样的清幽,青砖铺筑的院子,打扫的很干净,屋顶上长满的青苔,柳树横扫墙垣,人生的低处,俯身捡拾记忆里的时光,陌上花开,在雨后生香。
“这是我母亲为我留下的唯一的念想”。这是在我们走进院子后夏妍对我讲的第一句话。关于老屋的由来以及对母亲的怀念。
睹物思人,融于其中的都是复杂的情感。
夏妍说:“对于回忆,大部分人都有各自的想法和保留的缘由,有的人选择适时地清空删除,有的人愿意永久的存放在心底频频回首,我是介于这两种选择之外的第三种人群,对于过去的事情,我没有办法彻底的遗忘和对大脑定期的清空,很多次从睡梦中惊醒,总觉得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恍同昨日一般,睡梦中清醒,睡梦中哭泣,然后擦拭眼泪,坚强的活下去。”
我们的家庭原本非常和谐和美好,父母都是平凡的工人,在一个衣料厂子工作,父亲负责厂子机械设备的检修和调控,母亲则是产品流水线上的质量安检员,把持着衣料流水线上的安检工作,我还有一个可爱的弟弟。原来的家庭虽然不富裕,但是每一天都过得很快乐。我大学读的是美术专业,因为自幼酷爱绘画,对颜色搭配有着强烈的敏锐和猎奇心理,高中的时候报考自己喜欢的美术学院和绘画专业,四年时间修完了全部的课程,带着自己满意的作品结束了学生时代的悠然岁月。弟弟比我低两届,他考得是一个二本院校的土木工程专业,毕业之后去了北京的一个建筑工地工作。一个工人家庭出来两个大学生,这在父母的内心里是一件值得骄傲和庆幸的事,然而,所有的故变是从十年前的一场灾难开始。
弟弟在上班的建筑工地忙碌时,不小心从高层甲板上摔下来,送去医院急救室住了十多天,一直昏迷不醒,医生后来告知,弟弟成了植物人,得知此噩耗,母亲整整哭了三天三夜,她陪在弟弟的病床前,悉心照顾,擦洗翻身,看着他匀称的呼吸和紧闭的双眼过了一整年,一年时间都未曾唤醒过弟弟的意识,没有出现电视里上演的奇迹,医院的医药费高昂,家庭已经无力承担,就在父亲准备将弟弟带回家前几日的一个深夜,母亲从医院的高层上跳下,头颅着地,当场死亡。她无法用自己的力量唤醒弟弟的长眠,也无法再忍受内心的悲伤继续煎熬,便以死亡终结了生命,永远的离开了痛苦的人世。
第二日清晨,我与父亲匆匆赶往医院,处理了后事,安葬了母亲。那一天,父亲的表情出奇的平静,他漠然的守候在弟弟的病床前,一句话也不说。我知道,母亲走后,照顾弟弟的重任便落在了我与父亲的肩上。我们都忍受着内心的巨大悲痛,承担着不能背负的痛楚。那夜,我坐在医院的长椅上,隔着窗户看着明亮的圆月,凄清的夜,无声的低迷和凄楚,如一把刀剜在心里,月是故乡圆,人却阴阳两隔,此生再不能相见。我一遍遍的回忆所有事情的发展发生的经过,眼泪一行行流下,那一夜,我一遍遍的听着手机里凄婉悲凉的音乐,将头深深地埋在臂弯里。大约在后半夜十分,我走进病房,看见父亲在对弟弟讲话,他把那一年家里发生的事情与母亲跳楼自杀的经过,一件件的讲给弟弟听,我们都不确定处于脑死亡的他会不会听得到,父亲机械的讲着,面目近乎冷酷的平静,讲到母亲跳楼那一段,弟弟的眼角居然流下了眼泪,然而面容依旧安详沉寂。不知是冥冥中的巧合,还是心灵进难企及的触动,就在父亲讲述前后事的那一天的夜晚,弟弟也离开了人世。
两个最亲近的人在两天之内永远的离开了我们。父亲也几乎在一夜之间全白了头发,我似也流完了毕生的眼泪,我们静静地处理着弟弟的后事,带着两盒骨灰离开了北京。离开了一个伤心梦碎的地方。
回到杭州的那段生活,大概是我人生里最最难熬的日子,父亲长时间的盯着母亲和弟弟的遗像发呆,有时候嘴里自言自语说个不停,几日后,我也发现,他的手不停地抖,吃饭时,常常把饭菜洒在桌子上。我与他讲话,他几乎听不懂我所表达的意思,甚至也慢慢地不认识人,记不起我的名字,他疯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和心理打击摧垮了他全部的意志,在带他去医院的路上,他时而哭泣,时而大笑,时而沉默流泪。看着他的精力被混乱的思维折磨,呆滞与张狂在精神世界里的隐痛,我却失去了全部解救的能力。将他的头靠在我的肩膀上,一遍遍的抚摸他的手,那双枯瘦粗糙的手,被岁月磨蚀的手,曾经撑起一个家的手,曾经将幼年的我举过肩头的手,渐渐地失去了力量,变得麻木而干涸。
那时候,真的是长日无尽。我已经忘记自己是依托怎样的信心,坚持着走过了那段难忘的日子。那一年我刚满二十八岁,结婚不到两年,丈夫是装饰公司的一名室内装帧设计师,工作及其忙碌,时常加班到深夜,他喝着浓烈苦涩的咖啡来提神,我则是陪在他身边通宵的画油画,两个沉默的人生活在一起,孤独不鸣而合,日子一成不变踩在脚下。
因为不放心父亲一个人居住,我们把他从老房子接来,在家里居住的那段时间,他常常控制不住情绪,半夜里呢喃不停,在客厅里来回的走,嘴里说的话我和丈夫都听不懂,他已经失去了所有的记忆,对我们保持着极高的警觉。每天把饭端到他跟前,他总是打量半天才肯动筷子,吃着吃着又突然的哀嚎或者大笑,我和丈夫都意识到他的精神出现了问题。在咨询心理科和精神科的医生后,决定送他去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医生采取了心理疏导和药物并合的治疗方案,让他住进封闭式的治疗管控区,我们常常隔几日去探望一次,送去换洗衣物和食物,陪他说话,带他在医院花园的长廊边晒太阳。有那么一刻,他仿似非常的清醒,有时会拉着我的手,对我讲心里的苦痛,我非常珍惜他清醒时与我讲话的那些瞬间。但他也越来越喜欢哭泣。大多时候,思维都处在一个极度混乱和疯狂的世界。人力无所控的时候,医生会给打镇定剂,让他熟睡。隔着窗户玻璃,看见针头扎进他的皮肤,我常常难过的不能自已。
日子漫长如同黑暗里的隧道,看不见任何光的源头。我不敢回忆过去的经历,也不敢想象自己的未来,生命里所有的时间似乎都要停滞在暗夜里无尽的煎熬中,死如灰迹。
那一年,我突然一改往日清秀简帧的画风,提笔画起了色彩浓艳的油画,喜欢上了梵高的作品。我把中国的水墨画与西方的油画相结合,融汇在心里,形成自己独特的画风,用颜料的涂抹表达内心的感情,细碎的心事,软弱的背负,和着复杂的心情,每一笔都倾注了内心的悲凉和幽深的苦痛,不眠之夜只与孤独相守的感量,每一瞬间都要死掉。我常常把自己关在房子里,不画画的时候也是发呆和阅读,婚后第二年,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却因为长期的心情压抑和极度悲伤,孩子也流产了。这大概是人生里第三件不能承受的关于生命的重创和打击。
那段灰暗的日子,丈夫常常会在闲暇时陪我出去散步,我们一起到医院去看望父亲。四月的时候,带着内心的思念去给母亲和弟弟扫墓。四月的杭州,春暖花开,空气很清爽,西湖畔柳树成荫,秀踏银屏,这是一个适宜人居住的城市。前来踏青的游人络绎不绝,我却失去了全部的赏景的心情,内心的无力感与荒凉越发的沉重,悲愁填满了整个空虚的缝隙,几番辗转,在宿命里忍受。这是我生命里的不能承受之重。几欲摧毁心灵的防守和最后的底线。
如果说,坚持走过那段难忍的岁月是心底燃起的力量,丈夫则是在精神上给了我莫大的支持,他鼓励着我,尽他自己最大的能力理解着我的苦痛,以及由苦痛给自己带来的那些破败的情绪。我们共同承载着亲人离世的沉痛和伤感。钟情与人,钟情于固结的诚挚,执子之手,一生结好。
这是夏妍给兰诺讲述的关于自己的经历。那些发生在运命中难忍的剜在心里的痛。
自从父亲去了医院,这座老房子便空了下来,画画找不到灵感的时候,我常常会在老院住一段时间,打理母亲生前留下的那些花儿,和父亲栽种的文竹,屋里的家具和器物擦拭的很干净。每次回到老院,心境都特别的静谧,睡梦中会回到少年旧景中,和弟弟在院子里追跑着玩,母亲洗过的床单被罩上散发着皂角的味道,父亲吹的笛曲,梅边落日,寂静而祥和的旧景,都恍如隔世,深婉,模糊,每每想起总是情不自已,潸然泪下。
所有美好的记忆,都留在了这个老院里。玉兰花,硕大纯洁的花蕾,静静地绽放,雁字回时,愁痕遍地,深长的怀念在漫漫的长夜里延伸。人生种种凋敝的悲剧,在痛苦中无力自拔。虽然难以释怀,内心里,依旧保存着对生命旺盛的延续,自己毕竟还不是世上最孤独的人。一个未出世的生命,虽然带给我深深的遗憾,然而冥冥中却提起了我对生命的感怀和珍惜。最亲近的人总有一天会离我们而去,活在当下,好好地珍惜生命里的每一天,爱护身边的人,便是生来所携带的全部敬意。尤其对一个母亲而言,因着艰难,由自己诞生的生命便也倍加珍视,把他看成了生命里莫大的殊荣。
夏妍的遭遇给了兰诺深沉的震慑。原来,她总以为自己心路历程走的艰难,然而仔细观察,还有一些人也是活在运命无尽的纠葛和痛楚之中,虽然痛苦在形式上各有不同,但对每一位所承受的当事人而言,都有着致命的打击和难以企及无法回避的裂痕,直指心底,疼痛至骨髓。我们暂且不去比较哪种痛苦更为深邃和艰难,毕竟作为承受方的承受能力和发生在各自身上事态形势的严重程度的不一,单纯的去讨论和比较,哪种更具有杀伤力,是没有特别的意义。如果理性的分析,最后能做的,便是将它静静地存放在时间的隧道里,不再做深入的追究,不要问:“为什么不幸的事都会落在自己的身上?”这样的问题,要重拾信心,面对余后的生活,在心底燃起力量,敬畏生命里本被赋予的广度和长度,由此涉足,弥补那些断裂的齿痕和未及填补的空虚。
伊壁鸠鲁曾说:“痛苦并非不可忍受,也不会永远持续,只要你记住它自有它的限度,不要在想象中将其扩大。”这是夏妍几年前在书中读到的一句话,她说要从内心的苦难里走出来,用颜色赋予生命的活力,诚恳的面对和释怀那些苦难,爱自己手里线下所拥有的一切,如此才是理***的真谛。
她拔掉花盆里干枯的兰花的叶子,给文竹喷水,放置在背光的地方;太阳花移放在窗台上,与阳光对视。兰诺静静地看着夏妍在老院里做的每一件事,清扫院子里凋落的花瓣和杂草,如同清扫内心里耕种的荒芜,还原事物原本洁净而彻底的容貌,不再刻意背负那些载不动的忧伤和酸楚。
兰诺说,她甚至无法相信一个经历苦难的人,也可以活的这样娴雅和平静,选择画油画来抒发内心的情感,让生活走向了实质。
她想起自己行走的那几年,深夜在火车上读书,说很少的话,写很多的文字,常常在深夜两三点,与一本书死磕,独自对峙着自己矜持而又过分的孤独,不想去靠近任何人,哪怕那个人能够带给她足够的温暖。
都说生命是一条漫长而琐碎的征程,我们不分晨昏在路上走,遇见爱的人,遇见生命里的不完整,经历痛楚,将生命的本身看做是一种承受,保持心性的达观,与生命相爱,与世界共处。如此,才称得上向阳希望,劫后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