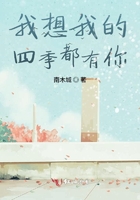姚妠容盯着妁慈黯沉无光的脸,俨然是观赏一场美人饮鸩一般快感十足。残忍的回应道:“陛下不舍杀你,陛下要招你入宫为妃。“
“妄~想~“妁慈嘴角突然泛出一抹笑意,阴冷孤傲。宴越之弹开姚妠容紧攥着妁慈臂膀的那只手。将妁慈护在宽大结实的背后。
姚妠容一如往常的淡定从容,冷冷一句:“陛下口谕,阻碍者,格杀勿论。难道你想血洗宴府吗?“姚妠容骄傲的扬了扬头,眼角随意一挑,扫向了门外。
管家跌跌撞撞的冲了进来,在宴越之耳边喃喃细语:“少爷啊。府外好多兵马,将整个宴府包围了。“宴越之无丝毫惊讶之态,此番场景,似乎是他预料之中的。
姚妠容端起桌上的茶盅,嗅了嗅盅中清香,故作一脸陶醉的神情,随后大步走向门旁,举起茶盅,将盅内茶水泼洒了出去。被茶水浇湿的泥土瞬间泛起了暗沉的湿色。
姚妠容将茶盅端放在桌几之上,悠悠道:“马车已在府门前候着了,若这湿土风干之前,还不见邵姑娘出府,就只能血洗宴府了。“妠容说完,转身走出房门。给宴越之和妁慈腾出了断情之地。
“我叫人备马,我带你冲出宴府,府中之人自然不会遭牵念。”宴越之胸有成竹,朝着妁慈轻轻点了点头。
妁慈心中莫名失落,她痴痴的望着宴越之清澈的眸,见他优雅雍容的苦笑,心绞疼难耐。
“事已至此,何必无畏反抗。”妁慈梨涡若陷,酸涩的液体迅速在唇角边掠过。
宴越之眉蹙一团,俊朗的脸庞瞬间变的生硬:“你当真要进宫?“
“是!”妁慈紧紧攥着手,指甲过于用力,“扎”进了肉里。妁慈丝毫感觉不到疼痛,所有的疼痛都掩盖不了这一刻的酸楚。
宴越之无助的摇了摇头,握着妁慈的肩膀,乞求的望着她:“你当真……不念一丝旧情吗?”
“是。“妁慈垂首,故作镇定,可整个身子早已酥软无力。
“此时此刻……你当真,没有一丝痛心?“宴越之又急又恨,神情萧索。
“当真!”妁慈哽咽着应了一句,短短两字,足以使她身心俱焚般痛楚。
宴越之轰然转身,举手砸在了桌几之上。“砰”的一声巨响。妁慈扭过头见宴越之失色悲愤的脸,紧紧闭上双眼,不忍再观。
见妁慈这般,宴越之刚刚的气愤烟消云散,紧紧的将妁慈揽在自己的怀中:“是我不好,不该不明白你的苦楚,不该逼你,千不该万不该。都是越之的错。”
“是我宴越之无能,这么多年,让你受苦了。不该救你于乱箭之中,让你虽有幸活着,却饱受怨恨之苦。不该日日让你在门前等我回府,让你饱受风寒之苦。“宴越之幽黑的眸流光四射,薄雾迷朦。情绪愈加激动,昂首一叹:”不该保护不周使你受伤,让你饱受皮肉之苦。不该替你挡那一剑,让你感恩于此,饱受内疚之苦。不该因你跟陛下为敌,让你左右为难,饱受抉择之苦。不该留你在府中,与我日久生情, 让你饱受相思之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