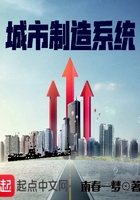妁慈只感觉双耳一鸣,瞬间失去了听觉。两腿一软,整个身子朝着前侧一倾,踉跄了一步。辅安和巧果连忙搀扶着妁慈的臂膀,安慰道:“娘娘保重身子啊。”辅安抬手朝着自己的脸上猛抽了几个耳刮子,哭腔道:“都怪奴才嘴多,明明知道娘娘念着赵家往日的好,还把这个消息说出来。奴才该死。”
妁慈双手握抱着廊道的木柱,脚下如顽石阻路凹凸不平,身子摇晃着,只觉得身子太乏太重,一步都动弹不得。索性瘫坐在了廊道一侧的窄板上,声音颤抖不已:“赵老夫人呢?”妁慈不由回想到当日在赵府,赵老夫人诚心相待,劝解自己用餐,又帮助自己救出宴越之的画面,着实在心中狠狠揪疼了一把。
“死了。”辅安垂首不敢看妁慈的脸,妁慈再也克制不住,眼角的泪如流珠低落,哽咽道:“那。。赵公子呢?”辅安深吸了口气,又回复:“死了,赵府上上下下两百多口人,一个活口也没留下。”妁慈双手无力,攥着衣衫的手一软,泪珠悄无声息的低落在裙上。心中仅存的侥幸,被一点一点的抽空,脸色的惨白如病疫中人。一群乌鸦廊顶划过,“呱呱”噪鸣,妁慈一眼望去,像看见了一群黑巫索命般游窜在空中。
“有人要害我,只管冲着我来便罢。”妁慈握紧的秀拳狠狠击打着身侧的木桩,满脸残湿的泪泛着晶莹的光:“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哪里有什么妖狐,无非是想设局置我于死地,可何苦要害旁人。”妁慈紧攥着心口的衣衫,企图用手中的力道来减轻心中的紧绷。
巧果慌忙攥着妁慈的手,反驳道:“这是什么话,这件事情娘娘难过一下便算了。万不能往自己身上揽,宫中耳目众多,一句不上心的话就会惹来麻烦,娘娘也是知道的啊!”
妁慈垂首,深深哀叹了口气,被泪水沾湿的衣裳,被攥的皱巴巴。
夜深了,冷月无声。这一夜辗转反侧,久久才入眠。梦回宴府,留恋于梅花馥郁之间,不过是过往云烟,浮生若梦。
妁慈乏了,累了,恨了,爱了,悔了,可一切似乎都在永无止境的继续下去,她再无回旋的余地。只因是被困在这个紫禁城内。不知何时醒来了,瞅一眼窗外,月色任是皎洁,地面被月色盖上了莹白薄纱,美不胜收。妁慈不由想到刚刚的梦境,还有宴越之那温煦柔情的笑意,随即薄唇一扬,唤道:“慈儿,今日身子好些了吗?”他竟不过是个模糊的影子,对自己不离不弃,却又伸手难触。
心口的胀气愈加难耐,妁慈瘫坐窗前的木凳之上,静静的看着,树荫向晚,虫鸟鸣啼。
这样一坐便到了天亮,巧果轻轻推门而入,瞧见这一幕,只能轻叹了口气,替妁慈梳妆更衣。许久,怕是感觉到了巧果梳头的力道不对,妁慈缓缓道:“昨夜,你也没有睡安稳吧?”巧果手中的玛瑙梳顿了顿,随后又如常的梳着,回道:“奴婢只是担心娘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