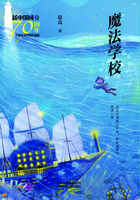乐人丰来到一幢洋房前面的花园里。暖洋洋的春雨继续浙浙沥沥,这毛毛细雨很有穿透力,他的衣裳已经被雨水淋湿了,但他仍然迈着缓慢稳重的步伐,不时地作着深呼吸。
因为这里的空气很新鲜,充溢着嫩枝绿叶的芳香,时而还夹杂着不知从什么地方飘来的馥郁的清香。这花园不大,甚至比乐人丰自己家里的花园还小,但布局非常优美,有玲珑剔透的太湖石假山,有造型美观的拱形小桥有好几条幽静的曲径。满园郁郁葱葱,满眼是说不尽的落叶和不落叶的草木植物,白色的和红色的桃花在棕榈树的绿影里散发出淡淡的清香:深胭脂红的玫瑰、色彩缤纷的月季,以及各种颜色茶花在雾霭般的细雨中羞涩地笑着,让人们看到它朦胧的色彩,朦胧的姿容,而越显神迷情动。
自从罗乐两家从市委机关宿舍搬出以后,今天乐人丰是第三次来这里。他事先没给罗琴君打电话,怕遭她拒绝,也怕正巧是她爸爸接电话,免不了会对他责备几句,他会感到很狼狈的。他和这位罗叔叔虽然同在春城市,却像月亮和太阳那样很少照面,自从两家搬开居住他差不多都快十年没有见到罗怡达叔叔了。
乐人丰正想着今天最好也别碰上罗叔叔,突然听到有人唤他名字,抬头四顾,原来罗琴君正站在窗前已经看到他了。
乐人丰掏出手帕边擦脸边加快脚步。
“为什么不坐车来,让自己淋成落汤鸡?”罗琴君在门口迎接他,俄尔,又揶揄地说道,“呵,对啦,你是秘密造访,所以不便叫车,对吗?”
乐人丰听出她的弦外之音,连忙把话岔开:“叔叔和阿姨在家吗?”
“你大概不想看到他们吧?要不,为什么专拣他们不在家的时候来呢?”罗琴君继续不真不假地说道。
“你别冤枉人,我又不会神机妙算,怎么知道叔叔阿姨不在家里?”乐人丰着急地说,一副委屈相。
罗琴君见他这副可怜相,噗哧地笑出声来,嘴角旋起两朵妩媚的浅靥,那笑声是欢愉的,跟银铃一般清脆悦耳。
他们说说笑笑来到一间很小的会客室,罗琴君给乐人丰冲了一杯速溶雀巢咖啡,放了重糖。她自己倒了一杯白开水,倒了一点蜜糖,来到乐人丰对面的沙发上坐下。
“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才来抱佛脚。又要我给罪犯画肖像吗?”罗琴君的性格是沉静的,同时也是开朗的,喜欢把什么都摊开来说。
“是啊,又来向你求援了。”乐人丰说。
“郑丽萍知道你来找我吗?”罗琴君问。
“我工作上的事情她从不过问。”乐人丰嘴上说轻的心里却想重的:郑丽萍反对他们来往的事,难道她已经知道了?转而一想,又觉得不可能,莫要犯疑心病“你不是在你妻子面前发过誓立下了保证,今后绝不再与我来往吗?”罗琴君声音平平地说一点也不生气,没有责怪之意她那沉静的神态,仿佛在叙说一件与自己并不相干的事情“你怎么知道的?!”乐人丰异常吃惊,因而也就顾不上掩盖真情了。
“请你不要追问,那是毫无意思的”罗琴君的神态同她的体态一样的沉静娴雅。
乐人丰没有追问,但他心里立即明白过来,肯定是郑丽萍给罗琴君写了信,求她别再同他来往。他在心里埋怨女子不该伤害罗琴君也不该对自己丈夫不信任。
“见不着你也就算了,既然又见着了你,我倒想顺便问一句:我们俩年幼无知的时候做的那件荒唐事,你妻子知道吗?”
乐人丰的脸孔涨得通红,并不是害臊所激起的羞红,而是负疚的心情使他脸红。为了掩饰自己的窘态,他立即回答道:
“我又不是无知无识的人,这样的事情我只能把它埋藏在心的最深处,永远成为内心的秘密,对任何人我也不曾透露过,郑丽萍也不例外。这一点,请你相信我。”
“我当然很愿意相信你。我也曾经这样相信过你。令人痛心的是,事情并非像你所说的那样。”罗琴君在说这番话的时候,表情是凄苦的,声音轻得像隔墙传来似的。
刑侦处长有本事在任何时候保持心理的平衡,这时候也禁不住变了脸色,心情像落叶似的纷乱。不错,他在同郑丽萍热恋的时候,为了对未婚妻坦诚,他多次想将自己年幼的时候在罗琴君身上所犯下的过错告诉她,但是每次都是话到唇边又忍住未说,因为他未婚妻的性情同她体质一样的脆弱,怕她接受不了。后来,罗琴君去农村找他,见他已与郑丽萍在相爱便主动回避了。但从此郑丽萍心里挽了一个疙瘩,有很长一段时间悒郁寡欢,吓得乐人丰更加不敢向她吐露真情了。他了解妻子的性格,她有可能给罗琴君写信,求她别再与他来往,但毫无根据而诬陷于人的事情,妻子是绝对做不出的。这事他只对孙跃文一个人透露过,如果要是从孙跃文嘴里泄露出去的,早就会满城风雨了。实际情形是至今无人知道这件事。不过有一件事现在想想确实有点难于解释:“文革”后期,外面传说孙跃文在追求罗琴君,开始乐人丰不信,但很快便得到证实,实属千真万确。乐人丰感到万分惊诧:
孙跃文清清楚楚知道他同罗琴君那段不同寻常的关系,为什么还会主动去追求罗琴君?难道他当真将这件事彻底忘了不成?叮是,他不该把它忘了,或者说不会把它忘掉的。当时,乐人丰猜疑、担心,害怕,却又百思不解。后来孙跃文同罗琴君闹崩了,据说是因为双方父辈的矛盾造成的,这种说法似乎可以成立。但在这个原因之外,是否还有别的原因,乐人丰就无从知晓了。难道他们恋爱告吹之后,孙跃文为了寻求对罗琴君的报复才故意将这件事散布出去的吗?此刻,乐人丰心中这样暗暗思忖,但很快他又否定了这个想法-既然孙跃文还记得乐人丰亲口对他说过的这件事,他为什么还要追求罗琴君呢?矛盾!矛盾!这一系列的矛盾,他一时无从解释。
“人丰,你听我说!”罗琴君打断乐人丰苦苦的思索,神色温和而语气深沉地说,“你事业上已有建树,又有一个很幸福的家庭。我呢,经过这些年的努力,艺术上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现在该轮到考虑个人问题的时候了。过去的事情,是我们幼稚无知的行为,不值得把它永远珍藏在心里,应当尽快地让它在心里烂掉,彻彻底底地烂掉,像一场虚幻缥缈的梦那样把它忘掉,忘得干干净净的才好……”
“你对我太宽宏大量了,我非常感激你。”乐人丰激动地说。
“这件事就在这里划上一个句号,今后谁也不许再提它了。”罗琴君说。想了想,又补充一句,“最好从今以后,我们别再见面,请你答应我这个要求。”
“我可以答应,不过我今天来要请你帮个忙,希望你不要拒绝。”乐人丰很认真地说。
“要我给罪犯画肖像?”
“请你替一个被害者恢复容貌。”
“替死人画像?”
“死者只剩下一堆骨头了,我能够从死者的牙齿想象出她生前的容貌,可是请来的画家没有一个能够表达我的想象,没奈何,只好请你助我一臂之力。”
罗琴君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她心有所动,这事似乎对她有些吸引力。只见她眨了眨那美丽的睫毛、瞳孔上扯起一片遐想的风帆。但是没多久,她的心情仿佛又平静如镜,支颐沉思起来。她的这副姿态,乐人丰很熟悉,过去,他顶顶喜欢观赏她这副姿态了。她那清秀的鼻子和拉斐尔笔下女性所特有的淡红色嘴唇,她那侧面的线条、轮廓如镰刀月般美丽。
“从死者的牙齿可以绘画出这人生前的相貌,这在科学发达的西欧国家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了,但在中国还没有运用过,认为这是异想天开者也大有人在。如果我们能够合作成功,对今后的刑事侦察工作无疑是一大贡献。”一谈起工作,乐人丰像是换了一个人,不再像方才那样拘谨和窘迫了。
“行是行,不过有个条件。”罗琴君从沉思中抬起头来说,“像画成之后,你最好不要说是我画的。”
她所以提出这样的要求,无非是为了不让郑丽萍知道,免得她胡思乱想。但她说得很含蓄,很婉转。乐人丰立即听明白了,点头表示同意。
于是他们起身,去了罗琴君的画室。
画室很大,却相当杂乱桌上地上到处是盛颜料的盘子和画笔,三面墙壁上都是油画、国画、肖像画、人物素描、生活速写,密密麻麻而又横七竖八的,到处是眼睛,到处是森林,到处是小溪或瀑布,到处是冰天雪地,乐人丰看得眼花缭乱。
乐人丰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具女人头颅骨根据牙齿的长度、宽度、厚度、密度、以及长短排列的情况,详尽地叙说着死者生前的容貌和面部的特征。他不善于用文学的语言加以描绘,甚至没有一个形容词。但他却又讲得很具体,描绘得细致入微,滔滔不绝,未打一个格楞,仿佛他就是死者的生前好友。
罗琴君像个小学生在聆听老师讲课,听得认真入神,偶尔提问一句,不时地在草稿簿上涂上几笔。乐人丰讲完后,罗琴君沉思了一会,便走到画架前坐下,用炭粉笔在白纸上开始涂抹起来。
不消十分钟,一幅年轻秀丽的姑娘的肖像画完成了,乐人丰接过来一看,感到比先前那几位画家画得都像,但仍不满意,逐一地提出了修改的意见。罗琴君接着又画了三幅,那第三幅乐人丰认可了,觉得基本上是他想象中的那个女子了。于是,罗琴君根据乐人丰认可的那一幅,运用色彩正式绘制了一幅死者生前的肖像。
乐人丰谢过罗琴君,兴高采烈地赶回公安局,拉着应克强去见柴之坚副局长,要求将画像投影翻印,发至全国公安机关,请求协查。因为春城市已经普遍查过,没有年轻姑娘失踪,据此,死者可能是外省市的。只有弄清死者是谁以及生前的情况,破案工作才不至于像无头苍蝇乱飞乱撞。
应克强本来就似信非信,立即提出疑议:“根据牙齿画像,大不了只能作为参考,不可能同死者本人一模一样,有没有必要兴师动众,通报全国公安机关协查?”
柴之坚副局长说:“克强的意见也有一定的道理,还是先在本市发动群众辨认,重点放在市府宿舍大院和市府工作人员的家属,因为凶手极大可能是市府机关内部的工作人员。”
这种做法尚属尝试性的,乐人丰自己也无十二分的把握,既然局长说活了,乐人丰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同意了柴副局长的决定。
画像投影拍成照片大量翻印后,通报全市派出所由专人负责发动群众辨认应克强的一队办案人员人手一张照片,走访市府机关工作人员的家庭清他们家属辨认。连市府机关也成立了协破小组,将死者的照片发至各部委组办,发动机关干部也来辨认第三天上午,应克强同刑侦队员小马来到乐人丰办公室,劈头说道:“人丰简直把我弄糊涂了!这个案子的嫌疑对象,怎么兜来兜去老是在你的好朋友圈子里面打转转?”
乐人丰站起身来,!困惑不解地看着他。
应克强说:“我同小马访问刘副市长家的老阿姨,她一看到照片,立即就说她见过是孙跃文的女朋友,三年前她在孙市长家当佣人时,孙跃文把这个姑娘带到他家里来过”
小马补充说:“老阿姨说得很肯定,说这张照片同孙跃文的女朋友一模一样。”
乐人丰听了这活,表面上未动声色,但他内心听受的震动,是无法衡量的一霎间他脑海里闪过一个与他一惯的性格极不吻合的念头,他唯愿自己首次的尝试失灵,唯愿这纯粹是一种巧合,但愿孙跃文不是真正的罪犯。而且乐人丰也绝对不会相信孙跃文是杀人凶手。他们俩毕竟从小一起长大的。孙跃文在同龄人中成熟得较早,从小颇有心计,别人很难看出他内心更深一层的东西;他喜欢往女孩子群里钻,交女朋友不专心,喜新厌旧,这些都是事实,但他绝不至于行凶杀人。
应克强似乎看出乐人丰内心的矛盾,又似乎他的思想仍在原来固定的轨道上,说:“其实小马的活也有点夸大。老阿姨说,照片同孙跃文的女朋友相比较,照片上的人嘴巴太大,颧骨也略高,耳朵太小,额头窄了一些,差异之处还是很多的,只是脸型很像,如此而已。”
经验在向乐人丰暗示,根据牙齿绘制死者生前的容貌,只能求得大体上相似,不可能十分逼真分毫不差。小马说一模一样,乐人丰很不以为然,而应克强的“只是脸型很像”,反倒令乐人丰暗暗吃惊。他的心被糟糕的感觉攫住了。但他很快意识到自己这种情绪不对头。他是国家的执法人员,公安干部,怎么可以徇私情呢?他决心忠于职守,履行职责。
他很快修补了心理的藩篱,恢复了平素的本质。
“你们问了老阿姨没有,还有谁见过孙跃文的那位女朋友?”乐人丰平静地说。
“据老阿姨说,那天孙跃文家里没有人,他只让女朋友在家里坐了一会就把她带走了。”应克强回答。
“那姑娘是本市人还是外地人?”
“外地口音、但老阿姨分辨不出是南方口音还是北方口音。”小马说。
“不是分辨不出,而是时间久了老阿姨记不起了。”应克强纠正道。
“不能因为他是我的好朋友,是孙市长的儿子,而顾虑重重。必须重视老阿姨所提供的情况。既然孙跃文的女朋友是外地人,在本市总该有个落脚的地方,弄清她的来龙去脉并不困难”乐人丰冷挣地说。
“就算你的画像基本准确。就算老阿姨的眼光基本准确但中国姑娘面孔相似者很多万一两者不是一个人,张场出去影响不好,甚至不好收场。这事只宜暗中进行,注重策略,不能让孙跃文知道我们已经怀疑到他身上。”应克强老练地说他始终不打算掩饰自己对画像半信半疑的基本态度。
乐人丰觉得应克强的顾虑是台乎情理的可以这样说:应克强的顾虑也正是他的顾虑他完全同意应克强的建议,将调查孙跃文女朋友的工作,就交给应克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