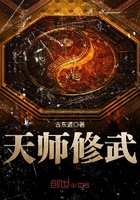他浑身像被抽空了一样,这份难受比任何一个时期的难受更为可怕,还不及在农村受着气种地的滋味好受呢。他无力地瘫在椅子上,把下颌抵住桌面,眼睛僵僵地停在玻璃板上。这桌子,不知谁用过的,桌面上还放着一块旧玻璃板,玻璃板边上粘着污渍斑驳的医用胶布,玻璃板下压着几句格言和警句,还有一张市直各单位电话号码表。他漫不经心地把眼睛搭在玻璃板上,搭着搭着,他就像触电一样跳了起来。
喂,你是体改委工业体制处吗?
是,我是体改委工业体制处。
我是市政府办公厅工业科,请你们科长听电话。
请问什么事?
市里要开工业企业改革大会,知道吧?
知道,知道。
请你们把全市体改情况写个情况报过来。
请问什么时候要?
今天下午。
好的,那,我们中午加个班,下午保证送到。
下班前,材料果然送到了!那真是一份拿得出手的好材料啊,全市工业企业现状、面临的问题、解决的思路和对策,下一步工作的计划。数字翔实,分析透彻,情况具体全面。他把大腿一拍,说我就不信我孟正律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第三天,他把材料交给翁科长:科长,这材料,你看看怎样。
翁科长看他一眼,接了,放在桌子上,确切地说是扔在桌子上,然后端着茶杯踱到窗前看着窗外。两三分钟后,又回到桌前,但还不看材料,却收拾起已经很清洁的桌子,正正台历,顺顺稿纸,擦擦水杯。又足足五分钟后,才把材料拿了起来。
这边的孟正律,眼里看着报纸,支着耳朵听着那边哗哗的翻页声,随时猜度着那边看到的地方,想象着那边可能的反映。
翁科长很快看完了,然后又哗哗地来回翻了几遍,又翻完了,按说该说说是行还是不行,可他不说,他把材料又那么放下开门出去了。
我写得太好了?盖了他的帽了?压了他的马头了?还是写得不好,他不好说?
或许他看着材料不是我写的?莫非知道我向体改委要材料的事了……第二天,他早早地到了班上。等了一会儿,翁科长和小邓才一前一后地到了。
翁科长从手包里拿出份材料,目不斜视地跟小邓说:去打印。
小邓接材料出去了。
头下班,小邓拿着一沓打印好的材料回来了,进门就朝他走来,说:小孟,咱俩校对吧。
他接了一看,材料题目是“——同志在全市工业企业改革大会上的讲话”,他心里一怔,忙往下看,发现除去一些数据和他写的材料一致外,其余,基本没一点一致的地方。
他脑子又像触电一样轰地一炸,手脚就凉了。
他不知道他是怎样和小邓校对完的,也不知道怎样回到家的。
下来,翁联合就不给他分派工作了。可他怎么也不能成天待着啊,他只好每天打杂儿——翁联合就这么淡着他,冷着他,怄着他,让他如同一只老鼠,一只被一副不紧不松的夹子夹住尾巴的老鼠,松也松不开,夹也夹不死。
小邓天天急着赶写信息,这个月小邓想争取信息采用量第一呢。
翁联合也在忙,刚忙完了一份调研报告,又忙着起草另一份调研报告。早晨一上班,扎头就忙,一直忙到下班,几乎连头都不抬一下。越是忙,电话越是多。哎呀,张局长啊,我说咱还是推推吧,你看我这都忙得喘不过气儿来了,再说领导也忙啊,过两天吧,过两天我一定帮你安排……哪位?李主任啊,你们的事我想着呢,不用客气,应该的,应该的……马书记啊?你现在过来可不行,你来了,我可没时间陪你,我这都马踩着车呢……我说小邓啊,不行,这个报告还是你来起草吧,我还得接月底那个现场会的讲话啊……孟正律也不看他,知道翁联合这是成心折腾给他看呢。
他嗵地站起来,径直就去了阎市长办公室。
阎宗品手里好像正处理着要紧的事,抬头看他一眼,说:有事?
他犹豫一下,说:没什么事……阎宗品就接着看文件,意思显然在说没事来干吗?
在他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时,阎宗品又抬头看他一眼,意思好像又在说没事你来干什么?
他想说,可又觉得无从张嘴,他就待不住了,说:阎市长您忙吧,我先走了。
出来时,比进去时心情还糟。阎宗品也没对他表示出什么非同一般的关系——阎宗品对孟正律也看不上眼儿了?也认为孟正律是个扶不起来的阿斗?
怎么就这么窝囊?翁联合看不上也就罢了,小邓看不上也无所谓,要是阎市长也不想理你,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
4.谁是婆婆谁是媳妇?
下班了。儿子在姥姥那边,范东红已经做好饭等他呢。
见他不高兴,范东红也不敢多说什么,忙着又端饭又端菜。见他对饭菜不感兴趣,忙又拿出平时不舍得喝的好酒。这些日子,他在范东红面前的分量早就翻几番了。不要说姓范的一家,包括范家远远近近的亲戚里,不但没有一个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就连一个在工厂办公室工作的都没有。范母当时刚一听说孟正律从小工厂调到了市政府,还以为女儿跟她说着玩呢。在知道是真的以后,没等到下班,就找人把范父叫回了家。范父听范母学说完,叭叭把烟头在烟灰缸里磕几下,眼睛瞪得天大,说叫我回来就为这事?范母说是。范父说叫我回来干什么?范母说想跟你商量商量,看是不是做点好饭打点好酒请亲戚朋友吃顿饭,庆贺庆贺,免得让人家说范家眼里没人。范父把工人帽往头上一扣就往外走,走了两步又回头说小家子气!不要说请亲戚朋友庆贺,这事,说都别说我知道!他,怎么了他?他要不是当初跟我家红红定亲结婚,能留城?不留城,他能有今天?嘁!范母一想,也极是。
但在行动上还是管不住自己,见了面,还是忍不住围着孟正律转磨磨。让孟正律更瞧不起的是范东红,如果她也能架住点劲儿,对他的态度别扭转那么快,孟正律但凡还能瞧得起她一点。唉,如果是矢秀白……天亮后,他就急着去给矢秀白打了电话。
其实,上次去长旺回来的第三天,他就给她打通了电话。很顺利,正好她接。
我去长旺来着。你来过?你来干什么?我有什么别的事?看你。那?怎么没看见?
我看见你了,俩人。出去和回来我都看见了,看你们进了大门我才打的电话,可打了好几次都不是你接,也不好让叫。哦?哎呀,你以后再打,就在早晨天刚亮时。
为什么?我每天黎明起床。人家呢?人家没我起得早。你家电话在哪儿?在厅里,离卧室一大截。之后,果然就方便了,每次和她通话,都在一大早。
这次电话一接通,她就急着问他去市政府报到了么?他说报了。她说怎么样?
他就把这情况说了。
你多聪明的人,怎么办这傻事?我也觉得我这一阵子脑子不够用,的确把事弄被动了。你要没有俯首甘为领导牛的气度,你就别去那地方工作!你以为甘当公仆是一句闲话呀?进了那地方,必须先做仆,才能再做主……放下电话他拍着胸脯说:孟正律能一步步从一个末等农民进了高校,进了城市,进了市府,那么孟正律就一定能从一个末等秘书走到上等秘书,走到官员,走到上等官员!
他走到翁联合跟前,说:科长看你忙的,我怎么也得替你干一点啊,再说了,我也得学习啊,我不学习我也会不了哇。这样吧,你写,我抄。
翁联合显然没想到他说这话,翁联合看看乱七八糟的草稿说:没事,我自己吧。
孟正律说别介,让我来。说着,收拾起散乱的草稿,说:我得抄,抄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然后回到桌前就仔细地抄起来——仔细得有点像临摹字帖。
用的是矢秀白送的那支英雄牌钢笔。他的手死死地握着笔杆,感觉像握着矢秀白的手一样。握着握着,矢秀白的气息就顺着钢笔沿过来了,字也写得又流畅,又自然了。
翁联合没想到,才这么几天就把孟正律捋直了。他知道他是阎市长带过来的,他也没打算捋他,可他实在反感人们一介绍他时,总说他是改革招生制度之后的大学生,言外之意改革开放前的大学生好像都是废物。翁联合是保送的大专生,可就是这个保送的大专生愣是扛着工业科大材料呢,工业科也是市政府硬顶硬的主要科室呢。不就是跟阎宗品过来的吗?不就是个本科生吗?别说你孟正律,就是阎宗品本人,又怎么了?说到跟文化跟企业业务沾边的话题还能有几句,到了处理实际问题时,就说不出几个道道儿了。那天体改委工业体制科长一说孟正律私下要材料的事,他嗵地就火了。好啊,你孟正律上来就想讨巧儿啊,翁某人怎么过来的?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练出来的,也是遭憋遭出来的。翁某人刚来尝的什么滋味?是怎么接受老同志们的下马威的?那杀威棒打得,到现在还隐隐作疼呢。那么容易就由小媳妇熬成大媳妇啊?给孟正律交代材料时,就料定他写不上来。按说,他孟正律应该有个谦虚的态度,应该提心吊胆讨教,可他偏不,偏要不露声色地玩漂亮。翁联合让你玩出漂亮来,你还知道谁是婆婆谁是媳妇?
世间的事,有时真的在于心境呢,这不,孟正律抄了几次材料后,居然觉着翁联合的材料的确写得不错,无论文字,还是逻辑,还是政策性和时效性,都比自己强多了。
孟正律的变化是一系列的。那之后,他每天早来晚走,翁联合还没到呢,他早就打扫了卫生,桌子上收拾得整整齐齐、规规矩矩,正中间放上笔和稿纸,右手边放上一杯新沏的香茶——是他从自家拿来的。下班后,翁联合不走,他就不走。
这天,又只剩下了他俩。翁联合说:小孟别写了,走,出去吃点饭。孟正律自然受宠若惊。
吃着饭,两人不断说话,虽然说的话题无关紧要,但他也清楚地感觉到翁联合对他已经没戒心了。
吃完饭,翁联合挥手叫服务员结账,服务员指着孟正律,说这位先生已经提前放下现金了。
接下来,孟正律又请翁联合出来吃,头一次找了个好馆子,第二次翁联合就指定去了一个普通馆子。翁联合说没必要,哥们儿,随便。
终于“哥们儿”了,“哥们儿”就得有个“哥们儿”样,让他自己都感觉奇怪的是,从此,他从心里真的就和翁联合亲了起来。
不久,翁联合母亲去世,他就真的跟自己亲人去世一样地着急,一样地忙前忙后,一样地熬得红鼻子红眼的。而且还有种心安理得。怎么了?从正面说,我忠于科长这是我的本分,从侧面说,人家已经和你“哥们儿”了么!最后在上礼时,他和同事们一起上了50块钱的同事份子后,私下里,他又塞给翁联合500块。
5.市场经济变数大着呢
早晨的雾气缭绕着还没完全撤去时,武汉的客户就进来了,这时矢秀白正和玉仙核对着一批货单,矢秀白一见客户,就朝屋里喊:解放,解放,武汉的客人来了。
段解放应声出来了,还挺快。
这个客户是解放厂几个大客户之一,就是这几个大户保着解放厂的流水呢。
段解放客气地把客人让到屋里。客人一进屋就说渴得不行,先咕咚咕咚喝了几杯水,才让解放领着去看大货。
客人一把一把摩挲着大货,说这次想多进些,可你们得把价格降低点,每斤,至少降一毛。段解放问这次想多进多少?客户把五个指头一撮一晃,段解放一看,扭头就喊:咳——当家的,你说呢?
矢秀白忙朝这边走着说:又拿人开涮呢,谁是当家的?这个家,还不是你说了算?解放把膝盖一拍,说:我听出来了,当家的是同意呢,那,就把价格往下勒一毛吧。
两人都为成了这笔生意高兴,更为缓和了关系高兴。办清手续,又执意把客人请出去吃了顿午饭。
实际上,段解放满肠满肚都是悔意,他觉得矢秀白做不出那等事来,尤其是玉仙那么急赤白脸地给他又发誓又赌咒,他就更觉得矢秀白不会,况且他自己一气之下又去舞厅,又睡小姐,把自个的清白也破坏了,而且又是矢秀白把他保出来的。
矢秀白心里也终究是踏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