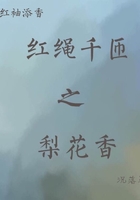随着时日增加,宁氏和吕氏手里那把汗就越捏越紧了,她们成百上千次地计算着矢家这茬人出来的日子,也成百上千次地端详着张秋花的肚子。
终于熬到了这天后半夜,吕氏发现张秋花屋里亮了灯,张秋花笨重的身影不停地在窗户上晃动,吕氏慌慌地披上衣裳赶过来时,宁氏也颤颤地捻着小脚过来了。
吕氏先把儿子矢根支出去烧水,又忙为张秋花掐肩捏腰,宁氏为张秋花滚了一碗姜糖水。张秋花浑身上下冒着汗,吕氏和宁氏浑身上下也冒着汗。
看着张秋花不停地趴下起来,起来趴下地折腾了好些回,脸和脖子像水洗的,头发也像水洗的,领口里也朝外冒出黏黏的热气,吕氏才拍拍枕头说:躺下吧。
那个让矢家盼了十年的孩子一出来,吕氏抢上去就看清了,像她娘,像她娘,完全像她娘啊——团团的小脸,细长的眼睛,扁平的鼻子!黑黑的头发!吕氏第二眼才看的性别,在她看清是个女孩儿时,那高兴劲儿一点都没减。
宁氏捧着那张小脸,转过来转过去地端详片刻,就把孩子裹上被子掂掂地抱出来喊叫矢家父子。等在外头的爷俩一听宁氏声音就知道孩子一准是长好了。在他们捧着孩子刚看清模样时,宁氏就磕磕绊绊地去给祖宗磕头了,那爷俩也忙抱着孩子跪在祖宗跟前。
老祖宗,老祖宗啊,老祖宗保佑矢家啊!
宁氏被矢群矢根架起来时,额上已经淌下了鲜红的血印子。
宁氏为曾孙女取名矢秀红。
宁氏和吕氏把瓦缸里所有白面都打扫出来,蒸了一笸箩馒头,还把馒头拿硫黄薰得雪白,再点上红红的胭脂,给村里每家每户都送去一个。
宁氏还让吕氏送给在街心里赊小鸭子的中年人一个,那是一个慈眉善目的中年人,骑个大水管自行车,车上驮着两只竹筐,筐里带着几十只小鸭子。这人每年都来,他把小鸭子赊给村里人,第二年再来,小鸭子成活了就收钱,不成活,就不收钱。这中年人接了馒头,也替他们高兴,还高兴得直擦泪水呢。
到了一九五三年,张秋花又生了第二个闺女,这闺女长得比大闺女更加好看,鼓鼻子鼓眼睛,黑头发,黑眉毛,更是一个典型的汉家女子!前两年“镇反”运动中,堤外村受花源头乡指示,对矢家查了几次,怀疑有海外关系。最后虽查无实据,可矢家在村里一下就更加地不体面不光彩了。张秋花这次能生出个好看的孩子,矢家人战战兢兢的心才放松了些。宁氏为孩子取名矢秀青。
宁氏和吕氏又蒸了一笸箩馒头,还是薰得雪白,还是点上胭脂,还是给村里每家每户送一个,还是连街上做小买卖的都送了,赶巧还有那个赊小鸭子的中年人也在,赊小鸭子的中年人接了馒头捧在手里细细地打量,人们便笑那中年人,说看呐,这人也真是,得个馒头,像得了只金元宝呢。
这年腊月,矢柱得了心疼病,吃了几服药总也顶不过去。矢柱就让把矢秀红和矢秀青抱到床前。吕氏就让矢秀红叫太爷爷,秀红亲亲地叫了太爷爷,矢柱眼圈就红了,攥住矢秀红的小手,就又看着矢秀青。张秋花把矢秀青的小手也放到矢柱手里,矢柱一手攥着一个曾孙女的小手,嘴角咧着,眼里一跳一跳地闪着光芒,宁氏给矢柱擦一下清泪说:下来就等曾孙子了。矢柱脖子一歪,眼睛就闭上了。
到了一九五四年秋后,张秋花刚把一天的活计收拾清楚,肚子就生疼起来,吕氏扶着她刚把身子躺顺,肚子里那孩子就急着要露头。吕氏急着去拿新做的小被子,一个蓝花的小被子,小子家的小被子得雅致些,不能红花绿草的——张秋花早说了,说怀下这个孩子,跟怀前头两个不一样。不一样?还不是个大孙子么!
吕氏拿了小被子刚走到炕沿上,那个孩子就着急忙慌地出来了,吕氏抱起来一看,“啊”的一声,脸就变得焦黄,吕氏忙看婆婆,婆婆也早没了人样了。张秋花一低头,才发现孩子脸色嫩白、眼睛深陷、眼珠棕黄、鼻子又高又挺!天爷呀天爷!
都几辈子了,那该死的洋血,怎么又逆了回来?!
奶奶、奶奶……娘,娘啊……更让一家人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一大早,老大矢秀红突然肚子疼得直打滚,只几下子就没了呼吸。
吕氏戳着三孙女嫩嫩的额头说:死丫头,是你,妨死了老大!早知道,还不如不要你!
三孙女额头立时红了一片,薄薄的额头骨呼地悠几下,险些要被戳透,可是孩子却没哭,一双栗色的大眼眨呀眨的,翻卷的睫毛一扇一扇的,似乎在问干吗戳我?怎么你了?吕氏心头的火嗵地撞了头皮,“啪”的一下,一记老巴掌就落在了嫩白的脸蛋上。可这孩子还是没哭,只把笔挺的鼻子耸两下,把眉头抽出个死死的结儿。在吕氏又要打第二下时,矢根惊慌地跑进来闷雷样地喊叫:娘!快去看看我奶奶吧!
吕氏惶惶地赶到婆婆屋里时,婆婆已经躺在一洼血水里,胸口上生生地插着一把剪刀。
3.除去爹和爷,她跟谁都不一样
张秋花看着怀里的三闺女,说你……就叫矢秀白吧。你,你是怎么托生来的?
你?
生了老大,张秋花在炕上躺了十天;生了老二,张秋花在炕上躺了一集;眼下,把矢秀白包上,她就下了炕。张秋花又洗菜,又做饭,又洗衣,又垫圈,可是乳房里的奶不但不少,还常常滋滋地往外冒。
吕氏从看了三孙女那一眼后,整个月子,再没过来。吕氏也是那一天就把矢秀青领到她屋里的,矢秀青从这天起,更成了奶奶的心头肉。
懂点事后,矢秀白就明白无误地知道奶奶不喜欢她了。不过,她也极想让奶奶喜欢,在奶奶要下炕时,慌忙把枣木拐棍递上去,可奶奶抬手就把拐棍夺了。她也曾在奶奶把三寸金莲伸到炕沿下找鞋时,慌忙把一双小鞋子捧到奶奶脚下,可奶奶拿脚尖勾起小鞋子刷地甩出老远,小鞋子飞出的那条弧线,像一柄月牙刀把她小心房刺得生疼。她蹲在炕沿下,一只小拳头使劲儿抵住嘴,另一只小拳头把流出的眼泪擦干净,把没流出的眼泪硬硬地咽回肚子里。
她终于明白,奶奶嫌的是她的面相。她偷偷地对着镜子琢磨,这眼睛鼻子脸蛋,跟太阳花儿一样水灵精神,可奶奶为什么那么讨厌呢?她又偷偷地看奶奶、看娘、看爹、看姐姐和过往的村人。她终于发现,除去爹和爷,她跟谁都不一样。也因了她的难看,一有来人,奶奶就要把她往小磨坊里推。矢家小西屋里安着一台小石磨,可她不愿去,她拼命地朝后曳着小身子,可奶奶两只老手太有劲,三下两下把她塞进磨坊又“啪哒”一声挂上一把大锁。
奶奶串亲戚从来不带她。那次,奶奶领着秀青又去串一门高亲。秀青说那亲戚家的房子比矢家房要高好几倍,也大好几倍,人家影背墙上画着两只仙鹤,跟真的一模一样,老想从墙上飞下来。人家吃的大米饭跟雪一样白,猪肉片子跟镰刀一样大,粉条子跟手指头一样宽。秀白实在想跟着去一次,这天奶奶和秀青都穿着平展展的新衣裳,奶奶个红包袱,里头包着一方红柳条笸箩,笸箩里装着各式各样的花饽饽,那是奶奶和娘头天夜里蒸的,第二天清早又拿硫黄薰得雪白。
她悄悄地跟着,脚步跟小狸猫一样轻巧。但还是让秀青发现了,秀青扯住奶奶衣襟往后一指,奶奶就咬牙切齿地骂开了:你个白妮子,快回去!再跟着,看我打折你腿!在她赶了好几段,奶奶往回撵了她好几段时,爹才把她拦住了,爹把她揽在怀里,给她擦泪,给她掸泥土,又带她摘野花逮蚂蚱。她戴着野花,拿着一串蚂蚱回到家,她娘果真就拿个长柄黑勺子,把蚂蚱煎得焦黄香嫩给她吃了。
之后,她既习惯了奶奶的嫌弃,也习惯了爹和娘的呵护。
再后来,不用奶奶管,她也很少去街上了。尤其是街上开社员大会或者有婚丧嫁娶的,就更不敢去了。那些人,给点面子的,只看看她还不说什么,不给面子的,少不得把她拉住,捋她头发、摸她眉毛、按她鼻梁子。问她怎么跟别人长得不一样?
问她知道太奶是怎么来的么?她从来不回答,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她就忙着跑回家,忙着忍着劲地不上街。
可有时也忍不住,她就跑去要跟孩子们一块儿玩,可人家摇着手说:够人了,够人啦!找别人玩吧。她一找别人,别人也说够人啦。她就想办法让人家高兴。人家拿瓦片踢房子,她帮人家捡瓦片;人家跳绳儿,她帮人家悠绳儿;人家踢毽子,她就抢着说她的毽子好使,她娘拿新布缝的,里头装的谷萆子。
她不小心踩了一个女孩脚,女孩张嘴就骂她小白鬼子!她问谁是白鬼子?女孩说你是小白鬼子,你爷你爹是老白鬼子!她把脸憋得发紫,可她一句话都说不上来,说什么?她和她爹她爷的确长得白,的确长得像电影上的白鬼子。
她问娘:奶奶是多少钱买来的?
娘忙捂住她嘴,把她下半句话憋在嗓子里。
她扯开娘手又说:奶奶干吗那么凶?是老妖婆么?
娘把她扯一边说:闺女,不能这么说奶奶,不能!
奶奶那个青粗布门帘一荡一荡的,她顺着门帘缝儿,看见奶奶从大襟上解下那个红亮亮的铜钥匙,奶奶鬼鬼祟祟地打开那个黑红的小橱子,橱扇上的铜片子叮叮响着。姐姐两手扒住小橱,眼睛一眨不眨地随着转。奶奶低着头,一只老手不断地掖着耳边一绺白发。一股甜香顺着小橱扇涌出来,又顺着门帘缝涌进她鼻子,钻进她肚子,使劲搅着她肠胃。
姐姐庄重着小脸儿往外走时,奶奶的一只老手理着那绺白发,另一只老手一下下地戳着姐姐后背。奶奶在嘱咐姐姐,可是姐姐常常不听,在奶奶一转身时,就把攥着的吃食往她手里塞。她有志气,使劲闭着嘴摇头。
不过,她也记得奶奶曾经对她满意过一次。
那一年,奶奶把小葱捆成一捆儿一捆儿的,让她姐俩背出去换鸡蛋。太阳平西时,她们就出来了,秀青背一个柳条筐头,她一个柳条篮子。她们走进堤内村时,各家正好冒出炊烟,村街上也飘出了棒子面或高粱面饼的香味。
有鸡蛋的换小葱啊——趴着锅台烙饼的妇女们听见喊声,忙打发孩子握个鸡蛋跑出来,一个鸡蛋换一捆小葱。有的鸡蛋是刚从鸡窝里掏出来的,还带着热乎气儿呢。
傍晚了,她们几乎把所有小葱都换完了。在她们准备往家走时,有个小女孩拿着半块高粱面饼跟出来,愣愣地看着她们,秀白问你要换小葱么?小女孩说想换,可我家鸡还在窝儿里卧着呢。秀白一看,那鸡窝里的母鸡果然正安静地闭着眼睛使劲呢。她们就坐在一个小土坡上等。眼看太阳要落,她们也急得直转圈圈,可那鸡一点不急。秀青看看天,说让小女孩明天再换吧。可小女孩让她们再等等,说那鸡蛋这就出来。秀青说回家晚了奶奶要骂。秀白便问小女孩家里有小米么?小女孩说她娘刚从碾棚里碾回来了。秀青说不行不行,奶奶没说让拿小米换。秀白说行,肯定行。秀青就说奶奶要打,可打你。秀白就说奶奶这回不打。
到了家,在奶奶惊异地盯着小手绢上黄澄澄的小米时,秀青那细眯的眼睛惶惶地看着奶奶,把秀白一下推个趔趄说:是她,不是我。可奶奶不但没打她,还把没牙的嘴一咧,赏给了她这一辈子第一个笑容。奶奶一边笑,一边踮着小脚熬了一锅米汤。奶奶哧溜哧溜地喝米汤的声响,在她耳朵里响了好些天,奶奶豁着牙床子的笑容,让她记了一辈子。
4.考试第一名基本都是矢秀白的
她就这么一天天长着。虽然屡屡经历着饥年荒月,尤其在大跃进的低指标、瓜菜代时,人人都饿,人人都一脸干菜色,她也常常饿得前心贴后心,可她还是一寸一寸地长了起来。到了五年级,她超了秀青一头多,身子也抽出了条儿,脸上模糊的红白变成了透明的粉白,栗色的头发油亮柔软,栗色的眼睛闪着一层潮湿的晕泽。
在人们惊讶她怪异的时候,常有人暗暗惊讶她实际很漂亮呢。
这时的她已经在想事情了,她那相貌来自父亲,父亲那相貌来自爷爷,爷爷相貌打哪来?
我奶奶是山里来的?她问娘。
张秋花透过花镜下框看着她,说:是,是你太爷一褡裢钱换来的。张秋花看一眼吕氏低垂的门帘,又说:打从山里出来,再没回去过,也可怜见的。秀白也盯着奶奶的门帘,让娘再往下说。张秋花就把针搁在大襟上,继续说:从你太奶那会儿,就敬着她。这些年,一直这么过来的。秀白又把身子往娘跟前凑凑:娘,你说说太奶。你太奶,挺好个人,心善,一手好针线。这堤外村,家家都穿过她做的活套。
听说太奶到死,还带着天津音儿。张秋花没说话,只把针往头发上划了几下。娘,那,你说,我太奶是不是天津的?张秋花把脸一沉说:你这孩子!我还有事呢。说着起身忙往外走。这白妮子一会儿不定又问什么呢。
那时学生的年龄差别很大,有的孩子上学很早,有的孩子上学很晚,秀白是上早的,而秀青又是上晚的。前赶后错,秀白和秀青上到了一个班里。
也像许多生不逢时的人一样,秀白很勤奋,功课比秀青和全班学生都好。到了五六年级时就到了“文革”中,学校在批“反动派”“反革命”“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洋奴买办”时,同学们也少不得往她身上想。到了“文革”高潮,村里揪斗“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便激烈了,也有人想把他们归进去。怎么了?堤外村没有牛鬼蛇神么?有!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就是!这些年一直没人敢说明的话,出来了。可是,到底没有真凭实据,矢家为“牛鬼蛇神”的说法便不成立。
到了一九七二年,正好赶上所谓“修教路线回潮”,县里一改几年来一直由贫下中农推荐升学的模式,要组织高中升学考试了。校长老师一夜之间振奋了,忙着组织早晚自习,还买了一台手推油印机,印试卷、刻片子,三天两头考试。教室里外天天飘着油墨的清香。考试第一名基本都是矢秀白的,老师校长自然把矢秀白当成了升学拿名次的指望。
那些日子矢秀白可真是风光了,老师表扬,校长表扬,同学们更是高看一眼。
可是到了考试那天,奶奶吕氏放矢秀青走后,把大门一锁,攥根枣木棍子就横在大门前:你,不比秀青,不能出村念书去。
她跺着脚说:我就得去,老师校长还让我拿花源头公社第一名呢!
奶奶蹾着枣木拐棍:矢家许你在当村念书,就着实不赖了,去花源头公社念?
门儿都没有!
你不让我去,那,你得给我老师说去!
奶奶立时像个漏气的风箱,呼呼地喘起了粗气:你说什么?你老师?就是那个他爷爷在日本炮楼上做过饭的小子么?嘁!矢家再不济,也没给日本人做过饭吧?
矢家人去找他说话?
老师爷爷给日本人做饭的事矢秀白也听说过,她便忙又软了口气:奶奶,你就让我去吧,我考上学,上出来,我一准孝敬您呢。
我呸!我呸呸!孝敬我?你要孝敬我,你就别给我出门,更别出村上学,那里十里八村的人都有,我不能让十里八村的人笑话矢家,笑话老矢家活了几十年还有你这一号人呢!
一边编筐的矢群对吕氏定的事从不表态,一边搓麻绳的矢根便拿眼直看张秋花,张秋花忙说:娘,要不,就让白妮子试试去吧。
亏得这么大岁数,说话也不知道前思思后想想!吕氏把唾味星子喷了张秋花一脸。你们丢得起人,我可丢不起那人!不能去,就是不能去!
张秋花像吃了毒药的母鸡,胸脯挺几下,嘴张几下,一句话没上来,就红着眼圈“咕咚”一下跪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