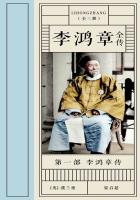神秘主人迎上一步和沈端先握手。
方脸型青年补充一句:“他比我大六七岁,我们是老朋友。”这话是示意给主人,可以充分信赖这位新的联系人。
主人请客人坐下吃茶。
沈端先不由思忖:这位神秘主人是何许人?同伴不介绍他的姓名,显然有保密性质,这更增加了几分神秘感。
他听他们随便说着话,神秘主人总对同伴叫“汉年兄”,看来他和潘汉年是相当熟悉的。
临分手时,神秘主人取出一盒雪茄烟,边交给潘汉年,边说:“汉年兄,你带上这个!”
潘汉年脸上漾着笑,连一句“谢谢”的话也不说,就收下了。
沈端先明白了:这不是什么临别的礼品。
辞别了主人,走到街上,潘汉年才告诉沈端先:“这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党员,一直是我和他单线联系,他会提供许多有用的情报,你可绝对不能怠慢他啊!”
“既然都是党内同志,为什么他不称你‘同志’,还叫你‘汉年兄’呢?”沈端先提出疑问。
“他这人和官场人物往来多,尽管政治思想转变了,在交际场合的一些老习惯却改不过来。”潘汉年说着又补了一句,“这也是他处的环境造成的。”
路旁的法国梧桐已经黄叶飘零,他们踏着落叶并肩走着,潘汉年回头瞥一眼那座小洋房,低声说:“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安南巡捕不敢到这里捕人,你在紧急危险的时候,可以到这儿来避难。”
沈端先“嗯”了一声。
这个神秘主人是谁呢?
沈端先和他来往半年之后,大概,主人对这位单线联系的忠诚战士充分相信了,才坦然笑着对沈端先说:“你大概还不知道我的真姓名吧?告诉你,我叫杨晳子,杨度。”
沈端先大吃一惊。
会是他?一个经常把搜集到的情报,放在一盒雪茄烟里,或者放在一个火漆封印的大信封里,或者用其他方式送到党的手上的革命同志,会是一个曾经捧袁世凯做皇帝大开历史倒车的人?一个常常把敌人追捕的同志留在他的住处的地下党员,会是当年的一个帝制余孽?
他再打量一下眼前这个富有神秘色彩的人物,见他眼光中有高傲也有和蔼,言谈举止上既潇洒又见真朴,他没有半点不良嗜好:不吸烟,不打牌,不涉足花街柳巷。在他身上,早已没有了老政客的影子,虽有绅士风度,更多的却是正直纯朴一介书生的本色。
不敢相信的事,终于被这个可信的形象证实了。
后来,他逐渐了解了杨度的情况:杨度来上海后,先是参加了鲁迅、田汉、胡鄂公等所组织的“自由大同盟”,旋又加入“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接着又加入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中国互济会”。后由中国共产党中央直属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第一书记潘汉年介绍,由党的领导人周恩来同志批准,正式加入共产党,成为出入龙潭虎穴的革命战士。
这时,他的公开身份是杜月笙的挂名秘书。
他走进杜公馆,是他的老朋友章士钊从中促成的。
章士钊这时是杜月笙的法律顾问,他受杜月笙的嘱托来到白利南路兆丰别墅——杨度原来的住所,向杨度说明杜月笙准备有所借重的盛意。
杨度听了,开始有些反感,难道一向自命不凡的自己,竟堕落到在一个流氓头子的手下讨生活?接着又转念:为什么不利用杜氏做一面挡风墙呢?杜氏和国民党政府的上层人物、特务、金融巨头都有密切关系,为什么不通过他多了解一些反动集团的内幕情况呢?
他将自己的想法向党组织汇报,取得党组织的同意,应邀来到华格臬路杜公馆。
章士钊陪着他,来到第一进大厅。
大厅正中放着紫檀木八仙桌,两旁是镶着文石镂花的八仙椅。镂花紫檀木条几上放着三尺高的福、禄、寿三星细瓷彩像,旁边是落地大自鸣钟。这一派陈设有些庸俗,但很有气派。大厅正中朝南墙上挂着一副黑底金字的对联,特别引起杨度注意。联语是黎元洪的秘书长饶汉祥写的,联语是:
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尺五天
这副对联烘托了杜月笙富埒王侯、食客三千的流氓声势。
杨度稍一玩味,嘴角流露出一丝轻蔑的笑。
章士钊向杜公馆的听差叮嘱了两句,听差便进去禀报杜月笙。
听差回来,便请他们到第二厅相见。
杜月笙站在石阶上表示欢迎。
这里是十分富丽的西式陈设:华美的地毯,几套大皮沙发,墙上挂着巨幅油画。
杨度端详杜月笙这人。他不过四十出头,修长身材,骨瘦如柴,满脸烟色,长袍马褂,举止倒也落落大方、彬彬有礼。
听差端来咖啡和水果,宾主随便谈着。
杜月笙很会交际,也和杨度亲切谈话,却又处处不忽略章士钊的存在。他先望一眼章士钊,转向杨度笑道:“行严兄几次和我谈起晳子兄,我也早就闻名,晳子兄真是名满天下的宪政专家呵。”
一句信口恭维的话,却在杨度思想上搅起了波澜。蓦然间,袁世凯的影子在他脑海闪过。他弄不清这是恋旧意识还是偶尔出现的感伤情绪,只觉得胸中涌起一丝朦胧的辛酸。
他已是共产主义先进战士,但是旧思想感情的残余泡沫还是有时泛起。他的脑中又闪过一种对眼前人物的批判意识:袁世凯的官气、张宗昌的匪气、杜月笙的流氓气他这种气倒是不外露的,算得是各有特色;而自己周旋于官气、匪气、流氓气之间,依然不脱书生气,还是一介书生呀!自己不无感慨的是,过去已有一个“帝制余孽”的臭名,今后倘再有人送一个“流氓势力的走狗”的新头衔,可真造孽啊。那样,自己前边走,背后会有人指着脊梁骨骂。一个革命者为什么要背这样的恶名?
但他又想到,古代哲人侠士,或混迹于屠钓,或混迹为版筑、击柝之流,甚至佛家也有吃狗肉,鼻涕拖得很长的有道高僧。作为革命者,为了革命的利益,又为什么不可以忍受罪名呢?
他的脑细胞里有不少古代人物和宗教人物的思想烙印,而这些,像经过反刍一样,草变成了乳汁。为革命,又值得计较什么?个人的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只有这时,他才感到自己的人格得到了净化,思想境界变得超脱了,精神面貌也越来越走向昂扬。
杜月笙当然不会了解杨度此时此际的复杂心情,他微笑地望着客人,对杨度冷漠而高傲的神情,自以为非常理解。杜月笙认为,凡是失意的政客,或者曾经阔气过的大老官,总是惯用表面的傲气来掩盖自己的狼狈相。杨度一定也是如此。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做自己的法律顾问,袁皇帝的宪政专家做自己的秘书,自己的身价不是比皇帝和总统还高出一筹吗?自己正是名流之上的名流,闻人之上的闻人上海报纸称杜月笙为“闻人”!
杜月笙得意地想到,既然杨度目前处境穷困,自己更应该照顾他的面子,于是笑道:“听说晳子兄很重友情,兄弟也很爱交朋友。不瞒老兄说,兄弟为人处世有一本‘三字经’,就是做人要吃三碗面:一是情面,二是体面,三是场面。这是三碗难吃的面,可是为了朋友,都要吃。”说罢朗声大笑。
杨度正要回答,不知什么时候走进来一个老枪——这是上海对吸食鸦片、又黑又瘦的烟鬼的称号——坐在角落里。这时老枪搭腔道:“杜先生一向是行侠仗义,对朋友一向是急人之难,慷慨乐施。有人说,杜先生是朱家、郭解一流人物,其实,朱家、郭解,哪能和杜先生相比!”
杜月笙更得意了,他知道杨度在北京时,住的是袁世凯送他的房子,自己身为名流之上的名流,闻人之上的闻人,怎能输给短命皇帝袁世凯?因笑对杨度道:“听说晳子兄住处狭小,我在薛华立路有一所房子,虽然不大,但还整洁,愿奉送晳子兄,请万勿推辞!”
章士钊忙插话说:“杜先生和晳子兄真是一见如故。”
杨度想到,住杜月笙送的房子,对革命工作也有许多方便之处,因拱手谢道:“初次相见,就蒙厚爱,真是愧不敢当。”
杜月笙嘿嘿笑着,便唤账房办理交割房产的手续。
听差走来禀报:又有客人请见。
杨度见他忙,便起身告辞。
杜月笙送到大厅门口说:“以后是一家人了,随时可以谈谈,恕不远送了。”
杨度和章士钊来到前厅,账房追上来说:“杨先生要是到薛华立路去看房子,这里派人陪着去,需要什么家具,可由这里代为置办。杜先生还关照下来,以后每月送月敬五百元给杨先生。”
不知是巧合,还是出于杜月笙的有意安排:现在“月敬”五百元,恰和杨度在袁世凯时代担任参政时月薪五百元的数目完全吻合。
章士钊笑着问账房:“杜公馆单送月敬一项开支,怕也不是一笔小数目吧?”
账房是杜月笙早期所谓“出窝弟兄”之一,总管杜公馆的银钱出入,人称杜公馆的“财政部长”。听到章士钊的问话,他便带点夸耀的神气笑出了声,说:“正是啊!杜先生手头阔绰,对很多人都送月敬。送给报馆好多记者的月敬是每人二百元,送上海市长的月敬是每月五万元,送给法国驻沪总领事的也算月敬的话,是每月十八万元,还有……”
杨度与章士钊交换着目光,似乎同时在说:你看,给我们的“月敬”,不过是奉献给洋人和大官僚之后的一点残汤剩羹罢了。他们也知道,杜月笙送给洋人和党国要员那么多钱,正是他开设赌台,包运鸦片能够通行无阻的原因。
杨度从此做了杜月笙的挂名秘书。
大官们拿女秘书当花瓶,杜月笙也拿杨度当客厅的珍贵摆设,他接见重要人物时,有时叫杨度陪着他。
杨度的接触面宽了,向党提供的情况因此更具有重大价值。
)第九节 太阳照着他
杨度的母亲李老太太已经去世,他把妻女接来上海同住。
他对家里人绝口不提自己入党的事,这是纪律,是严守党的秘密;同时,他也不愿让家里人对他的安全担心。
他曾设想过,如果被捕,在法庭审讯时,他也要一口咬定自己不是共产党员,那样,敌人即便杀了他,连敌人自己也得不到捕杀了一个革命者的满足。
一天,上高中的女儿下学回到家里,谁也不理,一头扑到床上哭了。杨度走过去关切地问她,“怎么啦?”
女儿不吱声,依然抽泣。
“是谁欺负你啦?”
“同学欺负你?”
这一问像碰到了痛处,女儿伏在枕头上哭出了声,肩膀颤抖着,像受了无限委屈似的。
他更不放心了,走近床边怜惜地问:“为什么欺负你?哦?说话嘛。”
女儿使性子,翻身朝里,没好气地说:“还问咧,人家都骂我!”
“骂你什么?”
女儿猛地坐起来,眼泪汪汪的:“骂我是——先是骂你,骂你是袁世凯的奴才,又是杜公馆的走狗,骂我是你的臭闺女!”说到后来,女儿的声音哽咽了。
杨度不禁老泪纵横。过了大半辈子,什么酸甜苦辣都尝过,受女儿的严词责备才真不是味儿。
女儿立即觉得对爸爸太无礼了,话说得太重了,等待着爸爸的大声呵斥。室内沉寂着,阴云密布却听不见雷声。
女儿一扬头,瞥一眼爸爸,那带有几分鄙夷恼怒的眼睛立即闪动着怜惜的光辉。她结结巴巴地说:“同学,还有广大民众,都主张打倒帝国主义,反对新军阀。爸爸,你就不能站在民众一边吗?”女儿的声音又哽咽了,哽咽中带有央求。
女儿的话听来还是火辣辣的,但做爸爸的一点也不生气,相反,倒为女儿的要胜好强要求进步感到宽慰。不无懊恼的是,他不能亮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只能找话安慰女儿:“你该相信爸爸,爸爸的爱国心,绝不比别人差呀。”
“空话!”女儿心里暗骂,可是她没说,也不忍心太逼爸爸。
他也觉得是空话,而实际情况又不便讲,一种无可奈何的痛苦心情出现了。不过,他又觉得,落了女儿的埋怨,也不值得伤心。这种埋怨,倒可以说是一种鞭策,鞭策自己献身革命事业。只要对革命事业有利,个人痛苦也算得到了补偿。
他是严守党的秘密的,但他又是爱讲话逞雄辩惯了的。现在也不甘心缄默,对女儿也确实有好多话要说,他便对女儿说些不涉及那个秘密的题外话。
他说:“在三国时代有个关云长,你知道吗?知道,那好。关云长身在曹营心在汉,一直传为佳话。难道爸爸就不能这样吗?”
他从女儿的疑惑眼神中,知道这并没有说服女儿,便说:“我讲个故事给你听吧。”
女儿用手帕擦擦眼角的残泪,用几分好奇几分疑惑的神情,望着坐在藤椅上的爸爸,听爸爸说道:
“在上海还没有租界之前,有一支英国船队从上海出发,准备入侵苏州。因为这一带水网密布,湾汉纵横,他们摸不清航道,便抓了一个中年渔民,强迫他领航。中年渔民看看躲不过,就说:‘好,这一带我熟。’他果然站到船头上指点航向。有几次,他要英国船队绕过险滩躲过暗沙,航行在水流深处。你看,他多么像一个为虎作伥的坏人呀!岸上看到这一情景的人,谁不骂他呀!”
他停了一会儿,继续说:“可是,当那支船队快速行进时,一下子搁浅了,船陷进了浅滩松软的泥土之中,活动不得,像飞蛾跌落在灯油里,扑打几下翅膀,不动了,连马达也像被胶住似的,哑了。中年渔民准备跳水逃走的当儿,被英国兵开枪打死了。他死了,他的爱国心迹终于大白。”
女儿默默地听着,意识到爸爸的故事是有所指的,但她还是要问故事的结尾:“那外国船队,后来怎样了?是不是到了苏州?”
“好就好在这浅滩芦苇丛生,有一支农民武装在这里活动,中年渔民是了解这一情况的,所以故意把鬼子船队引进伏击圈,农民军一声呐喊,直杀得鬼子兵丢盔卸甲,死伤无数。”
女儿听他讲着,忽然意外地发现,爸爸眼睛里闪耀着某种新奇的闪光的东西,她不知道那是什么,但她意识到那是富有正义力量的光芒,是高傲纯洁、充满自信的心灵的反射。这个发现,使她觉得既陌生又熟悉。
停了一会儿,爸爸又开口了:“后来,人们追念这位爱国的中年渔民,在上海的老城隍庙特意为他塑了一尊像,供人瞻仰。可是,外国侵略者不答应,强迫官府把塑像拆掉了。从清朝政府、北洋政府,到今天的南京政府,都是‘爱国有罪’啊!可是,爱国的中年渔民却活在人们的心中。”
他的语调平静,但平静的表层掩盖的愤慨情绪,女儿还是感觉到的。她有些醒悟了,她终于谅解了爸爸,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了爸爸。
他离开女儿,回到楼上书室里,取过一本书,读了几行。思绪很乱,集中不到书上。眼前又闪动着女儿哭泣时那委屈的神情,还有说话开始时那种不信任的目光;渐渐地不信任的目光消失了,许多信任的目光浮现了。那信任的目光,来自一群革命同志:潘汉年、沈端先、柳直荀……他印象最深的是那位批准他入党又和他有过多次接触的党的领导人。
领导人的亲切形象浮现在眼前:宽广的前额,两道浓眉,一双大而明亮锐利的眼睛,光芒四射。他神采奕奕,举止儒雅,处处显示着富有理智而机警过人。他说起话来,逻辑力强,具有直接抓住人的心灵的惊人力量。一次相见,自己曾向他吐露了一种担心:“我可是一个帝制余孽呵,你们不嫌弃吗?你们真会把我引为同志吗?”领导人爽朗地大笑起来,他说:“历史的污点是污点,但早已成为历史。古人说:‘观过知仁’。从过去的错误中更能看出一个人的品质和心迹。晳子先生毅然摆脱旧营垒,追求真理,献身革命,我们欢迎还来不及,怎么会不引为同志呢?同志,革命不分先后,对每个革命者,我们都会完全充分予以信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