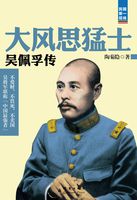夏寿田等他平静下来,才告诉他远春的死讯。远春是疯癫致死的,葬在陶然亭香冢附近。杨度听了,心中隐隐作痛,更加深了政治上失败的痛苦。小凤仙为蔡将军的功业彪炳而感到骄傲,远春却为自己的失败而饱受凌辱。人们可以把侠女的桂冠奉献给小凤仙,但有什么理由要把唾沫星子吐到远春脸上?这是历史的不公正,是远春的悲剧。他悼念远春,惋惜远春遇到的不是功成名遂的人,而是自己这样一个十足的倒霉蛋!不错,时代是前进的,推动时代前进的人是英雄,拖历史倒退的人是罪人。但是,如果只是名义上保住了共和,却弄得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甚至旧军阀倒了,新军阀代之而起,这到底是进步还是倒退?他想不通。他不服输,不认错,他的傲气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有所增强。他不是用傲气维持体面,不是用傲气作为自己的铠甲,而是从骨子里瞧不起黎段官府那批人。
夏寿田在天津没有住处,便住在杨度寓所。
受通缉不是蹲监狱,这里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只是不能离开租界。说句挖苦话,这种中西结合,倒有古人“画地为牢”的遗意。但是他的心情是痛苦的,觉得自己像一条活鱼冻结在冰山里,心都冷透了。
谭嗣同时代的戊戌变法是悲剧,他参与扮演的洪宪帝制是闹剧,张勋复辟,更是闹剧的余波。张勋率领辫子兵入京,又捧出了溥仪皇帝,组成了李经羲内阁,内阁成员中不少是洪宪帝制的残渣余孽:袁乃宽是内务大臣,杨士琦交通大臣,张镇芳度支(财政)大臣,雷震春陆军大臣;北京到处挂起了黄龙旗,假辫子、红顶花翎又从旧货摊上翻腾出来,戴在一批新大臣头上。一切封建顽固势力又一次沉渣浮起。张勋邀请杨度入京参加复辟事业,杨度拒绝了他,并在复辟丑剧演出的第三天,向张勋和康有为发出通电,电文中指出:
公等于复辟之初,不称中华帝国,而称大清帝国,其误一也;阳历断不可改,衣冠跪拜断不可复,乃皆贸然行之,其误二也;设官遍地,以慰利禄之徒,而宪政如何进行,转以为后,其误三也;设官则唯知复古,用人则唯取守旧,腐朽秽滥,如陈列尸,其误四也。凡所设施,皆前清末叶不敢为而乃行之于今日共和之后,大悖人情,至此而极。度认公等所为,与君主立宪精神完全相反。如此倒行逆施,徒祸国家,并祸清室,实为义不敢为。所可痛者,神圣之君主立宪,经此牺牲,永无再见之日。度伤心绝望,更无救国之方,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
他的心情是极度痛苦的,最大的痛苦是坚持半生的思想信仰至此彻底崩溃。本来,他忠于他的政治理想,坚持他的政治节操,他从不见异思迁,更不翻云覆雨。但是好曲不能唱三遍,他认识到他的君宪救国的美梦,像彩色的肥皂泡一般完全破灭了。一旦脚下失去依据,精神失去主宰,就像身子倒悬在黑暗的虚空中,有不断下沉的惶惑感。
张勋复辟,只有短短十三天就宣告失败。杨度从此也从思想上卸下了君宪主张的烂包袱。可是,又往哪儿去找心灵的慰藉和精神的解脱呢?往哪儿去找新的人生道路和救国道路呢?他天天坐在窗前,翻读佛家经典。他思索着,仿佛受到了某种启示,写下了这样两段话:
无我即佛;一心无二即佛;自由平等即佛。
随偈入世,满目疮痍,除救世外无事,除慈悲外无心。愿做医生,偏医众疾。
他的佛学思想不是出世的,倒一心想改革佛教以救世。
晚上,他离开孙毓筠的寓所,向回家的路上走。秋冬之间,雾气很大,望出去一片灰蒙蒙,雾幕中的路灯像投在深水中的光点。他在人行道上慢慢走着,生怕冷不丁地撞在别的行人身上。他蓦地觉得,自己这半辈子也像是走在雾中一样。
在雾中走着,朦朦胧胧,又看到前面的路灯投下了一团光晕。是呀,在事件旋涡中,很多事看不清楚;离开那旋涡,一切倒变得清晰起来。袁世凯的垮台,早已垮在密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之时,正如清王朝早已垮在屡次割地赔款、屈辱求和之日。倘若清王朝顺应民心,起而号召全国同仇敌忾,一致对外,清王朝可以不亡。孙中山开始号召革命,很多同盟会员并不理解共和民主是什么,都是激于朝廷的卖国政策才起来革命的。袁氏的失败也是蹈了清王朝的覆辙。袁氏的失败,还在于他逆历史潮流而动,民智已开,不能使之重归愚昧。他的失败,还在于他的排除异己,屠杀革命党人,从而失去人心。
杨度也初步清算了自己:在共和国体形成之后还奢谈君宪,是反历史的梦痴。迷信君宪,也是封建思想在自己灵魂上的投影。
雾好大,险些撞在电线杆上,想到哪儿去了?对,想到袁氏的垮台。人们都把袁氏的垮台归因于云南起义,正像被矿工挖空的矿山突然崩坍,便说是由于矿工的最后一斧一样,是既对又不全对的见解。
在街角的雾气中,闪出一张惨白的少女的脸,一下子就消失了。她大概拉住客人了,暗中可以听到她发出可怜巴巴的狎笑声。
“卖馄饨喽——”嘎哑的尾音拖长着。再走近些,才看清馄饨担上的玻璃油灯,灯光幽暗昏黄,照着卖馄饨老头的佝偻身影。
一切都像雾中的幽灵。
他想到自己脸上像是烙了火印,人家都用“帝制余孽”的固定形象看待自己。传播丑闻的人都是业余创作家,经过反复加工,那形象已独立存在,再不像杨度本人。正像古老笑话说的和尚与解差的故事一样:和尚把解差灌醉之后,把枷锁套在解差身上,并剃光解差的头,自己逃走了。解差醒来摸摸自己的光头说:“和尚倒在,我却不见了。”是呀,作为臭名远扬的“帝制余孽”倒在,杨度的“我”却渐渐不为人知了。
在雾中行走着,脑海中不断盘旋着一些事情,走过家门时没有察觉,等到察觉,已越过家门好长一段路了。
为了撙节开支,李老太太和黄夫人由老王头护送,回长沙居住,老王头也留在长沙。这时和杨度朝夕相共的人只有夏寿田。夏寿田潜心学佛,有时和他说到古代高僧慧远在庐山学佛的故事,两人渴望一旦获得自由,便同游庐山。
夏寿田和曹锟有交情,便写信给曹锟吁请解救苦难。曹锟于是呈请北洋政府,以“时事多艰,人才难得”为理由,请赦免帝制罪犯。次年,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三月,北洋政府发布赦令,对帝制罪犯和新的复辟罪犯一律予以特赦。
听到特赦消息,杨度深深透了口气。他急于走向广阔的空间,去呼吸自由的新鲜空气,于是和夏寿田结伴由海路到上海,再由上海前往庐山。
庐山的云雾和瀑布迎接了他们,也暂时抚慰了他们的忧闷心情。
他们住在牯岭一家旅馆里,每天寻慧远遗迹,访莲社旧踪,也饱览了三叠泉、黄龙潭、乌龙潭、石门涧几处瀑布的胜景。飞流,云气,景色瞬息万变。忽儿雾气裹山,不辨东西;忽儿烟消云散,群峰罗列。他们感到,这很像他们的命运,飘忽不定。
晚饭后,他和夏寿田走在山径上,想欣赏一下旧历十七八的月亮。听山上人说,这时赏月最好。太阳下山不久,东边的天际露出金黄色的一痕圆弧。他们定睛看去,流光溢彩的冰轮开始冉冉上升。
附近树上有怪鸟发出“嘎嘎”的鸣声,远处又传来野兽的嗥叫声。夏寿田望着又被云气遮住的月亮,笑道:“在这里参禅,真可以万念俱空,觉得过去的宦海浮沉,都是一场空了。”
两人正谈着,七八米远处一块寂然不动的怪石,突然出声笑了,使杨度和夏寿田都吃了一惊。杨度向那人望去,在月亮一露脸的时候,模糊看出是一个侧身坐着的和尚,身穿一件辨不清颜色的旧袈裟,双手略一合掌,又寂坐不动了。
杨度走上一步搭讪道:“大和尚住何处?定是有道高僧吧,在下忧患余生,不知高僧肯指点否?”
怪和尚合掌道:“阿弥陀佛,贫僧听得出施主都是失意的贵人,贵人失意,才能觉醒啊!”
一阵微风掠过,云气迷漫一色,天上的月亮没有了,眼前的怪和尚也被淹没了。神秘莫测的夜!杨度甚至怀疑那和尚是不是真的人,或者只是一个幻影?但他还是致谢道:“多谢高僧指点!”
怪和尚像个隐身人一般,只听他的声音说道:“两位施主,总是尘缘未尽啊。”说着,他像突然脱去云气的轻纱,又活脱脱地出现在皎洁的月光之下。
夏寿田说:“请问高僧法号?”那和尚更不答话,起身径走,只见云气埋住了他的双脚,转眼整个人都消失在云雾中,似乎天上的月亮也被他带走了。
庐山之游,迷离恍惚。杨度自己夸口说已洞彻身心,万缘俱了。夏寿田知道这不是他的真心话,他始终是一个不能忘情世事的人。他借学佛谋求解脱,却始终摆脱不了他对国家前途和个人身世的无穷忧愤。
)第十九节 三游江亭
他和夏寿田重新回到北京,暂住在宣武门外北半截胡同。夏寿田的姬人叫姚无双,三十多岁,善画花鸟草虫,是齐白石的女弟子。在夏寿田避难天津时,她寄住在北京朋友家中,这时也接来,夫妻同住在杨度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