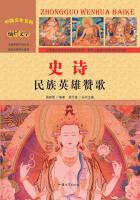他最后一句话没有指明“他”是谁,这也是奸雄到死都在玩弄诈术的地方。他用这话减轻自己的罪责,又嫁祸于人,又用这句不明不白的话刺痛那些推戴他当皇帝,而后来又背叛他的人。
杨度到底是书生,他对袁世凯的话只懂了一半,便认定“他害了我”那句话骂的只是他杨度。他用径丈的白色贡缎,写了一幅引人注目的挽联:
共和误中国?中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这里是辩白,是反驳,是发泄对袁氏的怨气,是说明袁世凯的失败,罪不在君宪本身,而是袁世凯咎由自取。
杨度尽管在挽联中,表示要到阴曹地府和死袁世凯打官司,要争一争是谁应负失败责任,但他还是有始有终,从天津赶回北京参加到袁世凯的送殡行列。
袁柩起灵的时候,他赶到了。他看到的出殡场面使他吃惊,全部仪仗完全是大行皇帝的气派。只见袁柩上披着“皇杠”用的棺罩,黄缎底,上绣龙纹、云纹;八十人的“皇杠”,每个杠夫都着缂丝銮驾衣;仪仗用品全是向清室銮仪卫取来的。起灵时,北京城内城外各庙宇同时撞钟一百零一下。在满城钟声中,袁柩起动了。袁柩前面,黄色彩亭八抬,内供洪宪皇帝的金印金牌;洪宪皇帝宝座八抬,各色绣花大纛旗十二对;绣花片幡二十四把;执金立瓜、金斧钺的执事四十八名;和尚、喇嘛、道士各十五名,手持引幡、经幢及各种吹奏法器;铭旌、祭幛、挽联、香幡、黄伞、影亭、衣冠亭之类络绎不绝。花圈五十对,由执事穿孝衣持行。绿色呢轿八抬,内供袁世凯的魂牌,特由袁世凯生前的卫队百余人护送。纸糊的冥器有牌楼、享殿,也有轮船、汽车、马车。军乐队六七十人,华乐队七八十人,分奏哀乐。最前面是保安队开道,陆军仪仗队和海军仪仗队共两千人。袁柩后面,“后护”四十八名,都倒背枪支,枪上系着黑纱。
新任总统黎元洪主祭,新任国务总理段祺瑞执绋,段内阁全体阁员也同时执绋,各国公使送殡。送袁柩前往河南的专车从前门车站启动时,放礼炮一百零一响。哪一点,哪一节,不是大行皇帝的气派!
杨度望着这浩浩荡荡的送殡场面,胸中不由涌出一个奇异的感觉。他仿佛看到的是魔王出巡的怪影:山精木怪,各执兵器;乌龙青蟒,蜿蜒出没。又仿佛看到的是小魔王借为老魔王发丧而炫耀法宝,是小袁世凯借为老袁世凯出殡而举行示威。这小魔王小袁世凯不是袁克定和袁克文,而是段歪鼻子他们。杨度曾希望狮子可以镇住群狼,可惜老袁不是真狮子,现在狼群更要翻天了。大头目一死,小头目蜂起,杨度觉得他的预言不幸快要被证实了。
送殡行列由新华门向南,过中华门,出正阳门到前门车站,沿路看出殡的人在两旁站得人山人海。
远春、小凤仙也在路旁看热闹。
小凤仙悄悄对小姐妹们说:“这里还下半旗志哀,听说西南各省还悬旗庆祝哩。”
远春听到这话,没做声。这些天来,她总怕别人用稍带讥讽的口气提到她的杨先生,更怕别人把杨先生和袁大头挂起钩来。她注意到,小凤仙每次提到蔡将军,总是眉毛一扬,眼睛一亮,有一种掩饰不住的得意神气。而她却不敢提杨先生,这使她非常痛苦。一个人倒霉用不着株连和他有点关系的人,只是精神痛苦就已经够呛了。前一天晚上,段祺瑞的一个亲信爪牙,跑到班里指名要她见客,她装病不见,那家伙就冲着班主妇大骂杨先生,说杨先生是帝制罪魁,要把杨先生抓起来办罪。还说远春早晚逃不出他的手掌心。那家伙在外间拍桌大骂,远春在套间字字听得清。那家伙一走,远春又哭又骂,闹腾了一夜。这天看出殡,她不肯来,是被小姐妹硬拖着才来的。她呆怔怔地望着那出殡行列,一声儿不言语。
出殡行列一队一队走过,一个既可悲又可笑的场面出现了:四十八名十三四岁的少年,穿孝服,手持雪柳,呜呜咽咽地哼哭着,为孝子助哀。在雪柳队后面是袁克定,他麻衣麻冠,左手持魂幡,由两名侍从扶掖着;袁克文左手持哭丧棒,也由两人扶掖着。奇怪的是孝子只是轻声哼着,似哭非哭,而雪柳队的孩子们却是哭声震天,悲恸欲绝。看到这怪诞奇异的场面,远春觉得一阵酸楚,泪水立即挂在睫毛上。小凤仙瞥她一眼,凄然说:“也真够可怜,为了挣几个小钱,就替人家哭丧。”
一个爱多嘴的姑娘说:“这有什么可怜的?人家打官司要打屁股,还有专门被雇替人家挨打的呢。把屁股打得皮开肉绽,还不是为了畏畏那张嘴。”
远春听了,嘴角颤抖了一下。
一个小姐妹问:“那当官的就答应?”
爱多嘴姑娘说:“怎么不答应?官府有这个规矩嘛。有被雇打人的,就有被雇替人挨打的;有被雇批文章的,就有被雇替人家做文章的;有被雇专门骂人的,就有被雇专门替人挨骂的;有被雇当凶手的,就有被雇当替死鬼的。这种事多着哩。”她说着,无意中向远春斜了一眼。
这一眼像电光一击,远春全身一震,立即敏感地认为是嘲弄她的杨先生,顿时骂道:“要骂就骂到明处,指桑骂槐干什么?知道他是替人挨骂,做替死鬼,为什么还要挖苦他?”
爱多嘴姑娘说:“井水不犯河水,我又没说你,你多什么心?”
远春脸色一变,嚷着:“听话听音,我还听不出来?”她那美丽的眼睛一下子变得愣怔怔的,行动也变得粗暴起来,忽而两手颤抖,一把抱住小凤仙喃喃地说:“你快藏起我来,他们要抓我呀!”说着,一阵呼吸急促,两眼发直,身子软瘫,倒在小凤仙身上。
众姐妹吓慌了,为她揉搓胸口,掐人中,忙乱一阵,她缓过气,呜呜咽咽地哭起来。
姐妹们费了好大劲儿,把她弄回乐班,为她找医生,为她灌药。
她刚睡下,杨度在送殡之后前来探望她。
丫头把她发病情况告诉了杨度。杨度悄悄走近床边,见房内凌乱不堪,远春静静睡着。他刚走近,她突然张开直愣愣的眼,撑着身子要坐起来,歇斯底里地嚷道:“别走近我,别带我走!”身子撑不住,又颓然倒下。
杨度带着负疚的心情,俯身望着远春微闭的眼睛,轻声提醒说:“远春,是我呀!”
远春张开失神的眼,精神依然狂乱,撑起身子大声嚷道:“我知道你是谁,你是姓段的,你是二皇帝,你是阎王爷,你别闯到我这儿来!”
丫头听到喊叫,忙过来抱住她,要她躺下,她才安静了些,顺从地躺下了。丫头低声请杨度暂时离开。
远春听到丫头说“杨先生”,又嚷道:“不许骂杨先生,不许你指着他的脊梁骨骂他!”
丫头又好话哄她,她才慢慢睡下。
杨度的心情十分酸楚,见远春病况一时不会好转,便和班主妇徐娘商议,先请医生诊治,如不见好,就送天津医院治疗。杨度要先回天津,便留给徐娘一笔钱,要她照料远春。
他离开这里,回到石驸马大街。这时李老太太和黄夫人都已搬到天津居住,这里只留老王头看门。
走进大门到二门的路上,一条砖砌路的砖缝里已长出了杂草,显然门庭冷落人烟罕至的标志。在客厅里,见那块“旷代逸才”的大匾,已由老王头派人摘下,原来挂匾的地方露出一大块空白。在杨度看来,那也像在他心头挂上了一片空虚。
老王头向他报了一笔账,他才发现自己已是债台高筑了,办筹安会还欠了外边不少钱。虽然曾由老袁批发了一笔经费,但各省代表由筹安会接待,帝制垮台后,还是由原来的筹安会资遣各省代表回籍,这笔开支庞大,把经费全用光了。他不得不把马车夫打发走了,马车也卖了,又把贵重家具、地毯以及多年收藏的珍贵字画和图书折变了一些,清理了债务。
一切贵重陈设搬走之后,客厅变成了过去荣耀的残骸。走进去,脚步踩在大方砖地上,会听到空空洞洞的回响。墙上还挂着梁启超为他写的谭嗣同诗句对联,字字像是冷眼看人,似乎也在嘲笑房屋主人学步谭嗣同,却学成了个反面角色。他崇拜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不料自己竟做了另一类型的“六君子”之首,这是历史的嘲弄。一位哲人说过:一切历史事变和人物都出现两次;第一次以悲剧出现,第二次以闹剧出现,这里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第十八节 劫后彷徨
杨度回到天津,住在租界清鸣台八号,寓所狭小。他一面沉溺佛经,一面又不能忘情国事,仍订阅各种报纸,关心时局动向。
他从报纸上读到不少嘲骂袁世凯的对联,倒代表了大部分舆论。一联是:
假冒共和虚名,别具肺肠同路易;
倘讲君臣大义,有何面目见德宗?
又一联是:
曹操云勿人负我,宁我负人,唯公能体斯意;
桓温谓不能流芳,亦当遗臭,后世自有定评。
又一联是:
劝进有书,劝退有书,葩经云进退维谷;
造祸由己,造福由己,太上曰祸福无门。
他再看下去,发现有两联骂袁世凯也捎带骂到他杨度头上,一联是:
鹿逐中原,浩劫遍及廿二省;
龙飞何处,伤心唯有十三人。
又一联是:
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
十三人是指“筹安会六君子”加上称作“七凶”的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二陈汤”指陈树藩、陈宦、汤芗铭。“六君子”与“二陈汤”都是中药方名,对仗是工巧的。杨度看了,仿佛字字戳痛了心上的伤口。他最难过的是,他自以为矫矫不群,不屑与“七凶”尤其是梁财神之流为伍。可是在大多数人看来,他和他们仍是一丘之貉。什么“伤心唯有十三人”?十三人中早有人投向段政府,成为改换门庭的新贵;还有人,像袁乃宽过去经管袁氏私产,多少袁氏的房地产、店铺、金银储存,都由他经手,袁氏的家属并无人过问,现在由于袁氏的死,他反而捞到大量昧心财。他们伤什么心?至于杨度自己,伤心的也不是袁氏的死,而是袁氏玷污了他的君宪理想。
过去的生活结束了,他开始要饱尝生活的严酷和艰辛。
他开始天天读佛经,希望用佛学重新思考人生;天天临碑帖,希望用书法谋求心理平衡。他有时坐在窗前久久不动,脸上显现着悲剧里人物的庄严。
夏寿田从北京赶来看他,一见面,杨度就感觉到又有严重事件发生了,因为这一切都明显地写在夏寿田的脸上。便问:“午诒,你打北京来,有什么重要消息么?”
夏寿田皱皱眉头说:“段祺瑞内阁对我们下了通缉令了。”他的声调尽量保持平静,但透露出的心情是沉重的。
“都是通缉哪些人?”杨度瞪大了眼睛。
“段内阁要惩办帝制祸首,开头有人提出十三人名单。可是有些人各有奥援,有人力保段芝贵,有人为严复和刘师培开脱,有人要照顾李燮和与胡瑛这些老同盟会员,袁克定不算祸首且不说,他还从家乡彰德打电报为雷震春和张镇芳乞情。袁乃宽因为姓袁,也可以不问。这样十三人只留下五个,大概段内阁觉得人数太少搪塞不过去,就添上顾鳌、薛大可和我三人。你看看这个吧!”夏寿田从衣兜里掏出一纸文告递给杨度。杨度接过文告,见文告是以新任总统黎元洪的名义发表的:
自变更国体之议起,全国扰攘,几陷沦亡。始祸诸人,实尸其咎。杨度、孙毓筠、顾鳌、梁士诒、夏寿田、朱启钤、周自齐、薛大可均着拿交法庭,详确讯鞫,严行惩办,为后世戒。其余一律宽免。
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年)七月十四日
杨度看罢,不屑地骂道:“哼,窝囊猎人是怕老虎的,只好向小鹿、兔子开枪!”他顺手把文告扔到桌子上。
夏寿田苦笑道:“我们一无军阀背景,二非进步党国民党人,三非遗老重臣,替黎段设想,也只好整治我们。”
杨度的眉梢痉挛一下,突然爆发一阵大笑。夏寿田觉得他的笑声有些刺耳,愕然地望着他。
杨度收住笑,解释道:“前清末年,我和梁士诒一同参加经济特科的殿试,梁士诒名列第一,我屈居第二。这次在通缉令上,我名列第一,倒叫他屈居第四了。这叫做‘天道好还’。我和梁士诒是死对头,过去在总统府常常避道而行,这次通缉令上,他一道陪绑,这叫做‘冤家路窄’。你说好笑不好笑?”
夏寿田无语,只奉陪苦笑。
杨度又说道:“把你、顾鳌、薛大可也列入惩办之列,真是岂有此理!你对帝制有什么责任?正像你常说的,你不过是总统跟前一个跑腿的。顾鳌不过是约法议员、政事堂参议。薛大可一个报人,只是写过两篇帝制报道,署名‘臣记者’罢了。拿你们,包括我这手无寸铁的文人开刀,而对那些攻打护国军的将领和上书劝进的各省将军,却一个也不敢碰。这不是拿我们,尤其拿你们三个当替死鬼么!”
夏寿田听他骂街,不便附和,免得使他火上加油,便走到书桌前看杨度新写的两篇佛学论文,见杨度都自己署名“虎禅师”。
杨度兀自坐着生气,突然用拳头猛击桌子,立定一个主意:到北京投案去!让他们收不了场!
夏寿田从他捶桌子的动作,觉察到他的意向,以息事宁人的态度劝他说:“我离京来津,是他们先送个信要我离京,然后才发出通缉令的。他们既然通而不缉,我们当然不能找上门去,逼他们非缉不可呀!”
杨度在屋内踱着大步,愤愤地说:“为什么通而不缉?还不是怕正式审讯会闹得收不了场!不让我们上法庭,他们就可以虚张声势,无理辩三分。这样,我这个帝制祸首更该出庭,和他们公开辩论一番,出出他们的丑!”
孙毓筠前来看望杨度,走到屋门口,听屋内大声说话像吵架一般,愣在屋门口迟迟不敢进去。杨度一抬头看见了他,忙请他进屋。一问,才知道孙毓筠也是逃避通缉才来天津租界的。当他明白杨度的意向时,也劝杨度不要自投罗网。他说:“人们都说我举棋不定,见异思迁,这是挖苦我,其实也是谅解我。人们认为我昨天赞成帝制,今天也可能反对帝制,所以没有几个人真正恨我。晳子,他们倒确实恨你呀。你去北京投案,他们不让你在法庭上陈述,说不定还会暗害你。你可要考虑一下其中利害呀!”
“我可能得罪过人,但我从来没有存心陷害过谁。”杨度自以为心地坦然。
“你不一定有心得罪谁,但你的傲气,也会有人想背后捅你的刀子。”
夏寿田从旁再次劝说:“记得老师曾说你憨直,嘱咐你遇事圆通些。这些年你有所改变,可是碰到大事情,你还是老脾气。何必呢?从今天起,你就看破红尘,潜心佛学,做一个真正通禅入道的虎禅师,不是很好么!”
夏寿田捧出王闿运老师的话规劝杨度,杨度才不言语了。他想起老师确有远见,离北京时还劝自己少出风头少说话,自己真是愧对老师啊!想到这里,怒气平息了。
他思索着叹口气说:“我弄懂了。洪宪帝制好比是老袁坐轿子,有人是前后顶马,有人是抬轿子的。而我,是走在最前头吹喇叭的。前面遇到敌兵,或者走近陷阱,第一个倒霉的就是走在最前头吹喇叭的,而顶马的,抬轿子的,都来得及向后转。杨士琦最滑头,陈宦变得快,脚底一滑都溜了,我,也算在官场混过几年,可是,多蠢呀!”
孙毓筠与夏寿田对望了一下,只好报以苦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