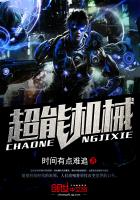杨度天天在纯一斋值宿,很多人都认为他是总统身边红得发紫的人物,都来巴结他,趋奉他。一天,那位年轻漂亮自称“总统门生”的沈佩贞也不经通报,径自闪了进来。
她看出杨度对她的到来有些愕然,先自开心地咯咯笑起来。
“想不到吧,我是来向您道喜啊!”
杨度知道她经常出入总统府,并和总统的各房姨太太有来往,能闯到这“禁地”来并不奇怪。便一面让座一面问她:“我有什么喜事呀?”
沈佩贞一扭腰肢坐到沙发上,把腋下夹的精致的小提包放在身边,抬起头嫣然一笑说:“向您道贺乔迁之喜。您从人间迁到天上,不是大喜么?”
杨度微微摇头:“我没有住进来的时候,仰望这里真如同天上宫阙。搬进来后,觉得也不过如此。一切总是在希望中最迷人,拿到手就平常了。”
“我不同意您的话。”沈佩贞撒娇地撇撇嘴说,“有情人希望成眷属,在希望中当然迷人,其实,希望成了事实,才更迷人!”
杨度明白话中的挑逗意味,便仔细打量她,见她不过二十多岁,有一张秀媚的脸、玲珑小巧的耳朵、细长白净的脖子、微红的两颊,笑时露出两个酒窝,一双水汪汪的眼睛特别勾人。他又见她眼睛眨动着投来一个媚笑,猛地记起曾见她这样媚笑过。他想起上次宴会上她跟梁财神的亲昵情景,便问她:“你这次进来,见到梁财神没有?”
“见到了。我在里头还见到了五姨太太,五姨太太还送我一张玉照呢。”她从小提包里取出一张四寸照片,带着自我炫耀的神情送给杨度看。
杨度知道五姨太太是袁世凯最宠的姨太太,他不愿亵渎老袁的眷属,没有接,在沈佩贞手上瞥了一眼便推还给她。在他一推时,她那白嫩滑腻的小手在他掌心里磨蹭了一下。
杨度矜持地笑问:“那么,梁财神送你什么没有哇?”
“哟,干吗调查这个!他是我的义父,他给我钱花也是应该的嘛。”
轻狂!势利!一心想往高枝上飞!一种类似恶心的反感从杨度胸中升起。她并不美!那微红的面颊、浅笑的酒窝、水灵灵的眼睛,都隐隐透着一种浅薄和轻浮的贱相。他垂下眼皮,即兴找词儿,先“唔”了一声,才前言不搭后语地说:“你真是女交际家,我自愧弗如。”
“哟,怎么又谦虚起来!您那么大的学问,连总统也要请教您,我磕头拜师还攀不上呢,还谦虚个啥!”
对这样一个女人,既不便得罪,又不愿沾惹,杨度正感到为难,忽然小听差急急前来禀报:“总统来啦!”
杨度又惊又喜,因为总统屈尊光顾僚属的住处是件稀罕事,也是一种荣誉;自己又可趁此摆脱沈佩贞的纠缠,岂非一举两得?于是,他便邀请沈佩贞一道出屋门迎接总统。
沈佩贞却着了慌,她这个“总统门生”怕总统看到她的轻浮,忙摇摇手,轻声说:“不,我要回避!”她立即把照片塞进小提包,三步并两步,钻到套间里去。
杨度只好单独走出屋门迎接总统。
一群侍卫人员簇拥着袁世凯走来。
袁世凯拿一根下端镶有铁包头的藤手杖——这既可以支持他的瘸腿,又可以防身,他走路时两脚一高一低,有些轻微摇摆。那根藤手杖随着他的脚步,咯,咯,咯,在地面敲着。他进屋时“哦”了一声,像咳嗽又不像咳嗽,更像是用以显示他的尊严,然后进屋。
侍卫人员都留在廊下听候。
袁世凯进屋,向室内陈设扫了一眼,自动坐在一张雕花椅子上。
杨度想:要是老袁撞上沈佩贞,才热闹哩。老袁会不会骂她?沈佩贞又将是一副什么狼狈相?他这样想着,等着老袁和他谈正经事。
袁世凯两肘靠着椅子扶手,抽了两口雪茄,问:“晳子,上次你说的王闿运老先生,你写信叫他来吧!”
杨度坐在对面椅子上,回答说:“王老先生名重海内,他的学问和文章,当代无第二人,只凭一封信,他是不会来的。”
“哦,那晳子就辛苦一趟,代我到长沙请他出山吧!”
杨度忙答应着。这时他全副精神都扑在他的政治性谈话上,把套间里躲着的美人儿完全忘记了。他乘机说道:“总统延揽人才,不遗余力,这是国家的兴旺气象。只是起用的旧官僚不少,擢用的新人才还不多,蔡锷以善于练兵著称,要改造北洋军,非他莫属。只要总统委以重任,结之以恩,他是会乐为总统所用的。总统不存派系之见,不存南北畛域之见,用人以公,示人以诚,定会赢得人心悦服,百姓拥戴。”
袁世凯含糊地“嗯啊”着,忽然记起一件事,说道:“曾有人揭发蔡锷在云南有脱离中国版图,另建一国的叛国企图,我就不相信,我认为蔡锷不是那种人。”原来这揭发材料就是袁世凯一手制造的。他布置捏造了那份揭发材料,目的是要蔡锷听话,如不听话,随时可以定他个叛国罪;现在他又向杨度卖人情,还可以通过杨度向蔡锷送人情并施压力,真有一石三鸟之妙。
杨度不知其中真情,表示同意总统的意见,因又说道:“目前除改造北洋军之外,邀请各党召开国会,制订宪法,都是当务之急。”
袁世凯装作高兴地说:“对呀,晳子确有宰相之才,如生在君王时代,定可以做中国的俾斯麦和中国的伊藤博文,可惜现在是共和时代,只有使你屈居人下了。”他又做出不胜惋惜的神情。
杨度听来,老袁这番话,意味着巨大的尊重,绝对的信赖,像是令人陶醉的美酒,甜丝丝的,稍有点儿苦味儿,那苦味儿更使甜味儿显得纯正。他还有不少要向老袁劝谏的话,可是,那美酒一般的话,正在全身血管里流动发酵,使他把要劝谏的话变成了感恩的话,“我跟总统走,跟定了。”这是连杨度自己说出口后也感到惊异的话。
杨度又问老袁:“总统是否还记得夏寿田?”
袁世凯精神一振:“夏寿田,他现在怎么样?”他记得这个老朋友的儿子。
“寿田的父亲早已去世,寿田做过几任地方官,但宦囊不丰,他又不善理财,现住在长沙,生活上也委实拮据呢。”杨度如实回答。
“这样吧,”袁世凯带着罕见的关切心情说,“你到长沙去请王老先生出山,顺便叫寿田一道来京吧!”
袁世凯走后,沈佩贞才从套间里钻出来。头发也乱蓬蓬的,不知在什么旮旯里钻过。杨度见她一副狼狈相,忍不住笑道:“想不到我这里成了金屋藏娇之地!”
沈佩贞白他一眼,一言不发,从小提包中取出梳子,对着大穿衣镜拢头发。她从镜中看到杨度正从背后看她,依然带着幸灾乐祸的神情。她生气了,也因为不敢在这里见总统而生自己的气。她拢好头发,扭身就走。
杨度去长沙时,向袁世凯要了亲笔信。
袁世凯打发杨度走后,知蔡锷已经到京,便准备接见蔡锷。
)第三节 蔡锷到北京
袁世凯接见蔡锷,故意大摆威风,想对蔡锷来个下马威,来个心理慑服。通向接见大厅的路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大厅阶下站了一排排卫兵,穿一色的黄斜纹布军服,手持步枪,挺胸立正。卫兵一律选的是大个子宽肩膀的,整齐划一,十分严整。
大厅阶上几十名将军分班站立,都着黄呢军服,佩绶带,带德国手枪,头戴鸡毛掸子似的高筒将军帽,脚蹬高统皮靴,屏息耸立,脸上毫无表情。
袁世凯以大总统兼大元帅的身份,着金边耀眼的大元帅服,威严地站在大厅中央。庄严的气派,尊严的声调,严厉的目光,连那直森森刺向嘴角两旁的八字牛角胡,似乎也助威风似的微微颤动着。
这时传呼下来,命蔡锷穿过卫兵组成的人巷,到厅上晋见。
蔡锷,个子不高,身材瘦弱,脸形微长,有些血气不足。他穿一套洗涤过的旧制服,年方三十,在高级军官中算是相当年轻的。他的外表,看上去不像一位将军,倒更像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可是他智谋深沉,心雄万丈,神态严肃安详,浑身蕴藏着旺盛的精力。他有眯起眼睛用挑衅的神情看人的习惯。当下他看到老袁摆下这个阵势,不由心中窃笑:老袁呵,也太小看人啦,接见我又不是什么隆重大典,耍这威风干啥!他缓步穿过人巷,神态从容,旁若无人,升阶入厅,向老袁行鞠躬礼,然后微笑着注视老袁,态度安详,不卑不亢,问一声:“总统好!”接着说:“接见我这一介武夫,何必如此郑重其事呵?”
袁世凯没有吓倒蔡锷,倒是蔡锷镇定异常的神态使袁世凯吃了一惊。袁世凯只好收起威风,改用亲切态度接见蔡锷,心上却在掂量:这个人不可轻视呵!杨度劝我委以重任,要是听从他的话,当真授蔡锷以兵权,蔡锷肯俯首帖耳为我所用吗?他心上疑惑,表面上却是非常亲切,立命撤除兵卫,并挥退左右,请蔡锷坐下,开始进行试探性的谈话。
袁世凯摸摸牛角胡,温和地笑道:“松坡,你善于治军,早负盛名,我也正要借重你。你看,目前要提高军队素质,加强战斗力,是不是应该着手建立新军?”他想到自己以小站练兵起家,练新军是培植私人势力的好机会,他要试探蔡锷是否也有类似的野心。
蔡愕是机警的,也毫无拥兵自重的念头,便答道:“目前建立新军,必然要增加国防开支,加重国民负担,在财政拮据的今天,倒不是急务。其实,兵在精而不在多,当务之急应该是改造旧军。”
袁世凯“嗯啊”着,搜索的眼光直在蔡锷的脸上扫来扫去。
蔡锷用平视的眼光望着对方,他有改造北洋军的夙愿,他看到北洋军是全国最大的一支军队,但是这支军队,毫无国家观念,只是造就了大大小小的军阀,必须改造它,使它脱离私人掌握,成为真正的国家军队。蔡锷知道,袁世凯就是北洋军的头号军阀,一直视军队为己有,自己要是把话直说出来,必然深为所忌。于是,他委婉地继续说道:“改造旧军,要采用新的操练方法,严格训练;要整顿军纪,裁撤不称职的军官;更要教育官兵知道保卫国家,听从中央政令,而不要动不动自立山头,闹封建割据。”
蔡锷的措词,很有分寸,既切中要害,又强调军队要服从中央政令,满足了老袁“朕即中央”的心理。
袁世凯点点头,故作关切地笑道:“松坡来京,一路辛苦,暂时休息几天,以后就借重你襄办军务吧!”
大概权力欲太强的人,往往都猜忌心重。袁世凯对蔡锷,既赏识又不放心,既想重用又猜疑不定,就像要拿动一把刚淬火出炉的钢刀,喜它锋利又怕他烫手一样。袁世凯一直没有授予蔡锷以改造北洋军的实权。但先后还是给了蔡锷以政治会议议员,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经界局督办等等一大堆头衔,后来又任命他为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办事员。统率办事处是袁世凯的最高军事机构。它的办事员人选是极其严格的。他肯这样任用一个非北洋派的下台军人,还是部分地听从了杨度的劝告的。
这时杨度陪着老师王闿运,还有王闿运的“上炕老妈子”周妈,以及同乡同学夏寿田,一道从长沙来到北京。蔡锷听说杨度回京,特来石驸马大街看望他。蔡锷和王闿运早就相识,和夏寿田更是亲密好友——蔡锷早年在江西闹革命,夏寿田以贵公子身份掩护过他。好友重逢,都非常愉快,杨度办了一桌酒席,为老师和好友接风。
厅上陈设朴素大方,最引人注意的是墙上挂着一副梁启超为杨度写的对联,联语是:
寰海惟倾毕士马逢时差喜卫哀骀
梁启超的书法,笔力遒丽。写的联语是谭嗣同的两句诗。当时积弱的中国饱受列强欺凌,所以爱国志士希望中国也出现铁血宰相俾斯麦那类人物。哀骀是战国时代卫国形体丑恶的人。谭嗣同这两句诗,语含愤激。杨度崇拜同乡先辈谭嗣同,他的君宪思想也有谭嗣同流风余韵的影响。这副联语也间接表明杨度的思想状况。
王闿运年近八十,后脑勺还拖着一根瘦小辫子。周妈四十多岁,还缠着一双小脚。人们常常打趣地说:辛亥革命只是男人解放了头,女人解放了脚,这话有道理,但也不完全正确,至少在王老先生和周妈身上,头脚都依然如故拒绝维新。人们对辛亥革命感到失望,就怪不得君宪思想仍然拥有市场了。
席上,玩世不恭的王老先生当然坐首座,性格泼辣的周妈坐在他的下手,蔡锷和夏寿田分坐两旁,杨度打横奉陪。蔡锷说了袁世凯接见的情景,笑着加按语说:“老袁这人太好做戏,我算暂时做了他的配角。”
周妈正狼吞虎咽地嚼鸡骨头,手上扬着鸡腿,阔嘴巴周围沾着鸡汁,就大笑道:“老袁做戏,像不像个大白脸呀?外省人都骂他是‘奸曹操’呢!”
杨度忙放下筷子辩护说:“外人不了解他,骂他的人不少。依我看,他还是有爱国心的,他办事有魄力,有办法。权力欲是大些,也好玩弄权术,但这也是自古以来一些当权人物的通病,为什么要特别骂他?对我们来说,要救国,还是要拥戴他。只有他有力量维护全国的统一。”
蔡锷沉默不语。夏寿田听得有趣,插话问:“那我们跟着他,能做些什么呢?”
杨度向全桌的人扫了一眼,胸有成竹地傲然答道:“有应该做的,有能够做的,事情多得很呢!”他望着夏寿田继续说道:“午诒,你会得到老袁重用的,因为老袁用人,重视门第出身,又喜用亲友子弟,这些条件你都符合。你得到重用后,我们先要做的事,是互相配合向老袁建议,让松坡掌握实际兵权,最好是做陆军总长,那样改造北洋军,名正言顺,定会收事半功倍之效。”
王闿运用手帕拭去胡子上的酒滴,摇摇头说:“不妥不妥,现任陆军总长是段祺瑞,他是老袁的嫡系大将,你要夺段总长的兵权,老袁会答应?”
周妈忙搭腔道:“你老师说得对呀,一拃不如四指近,人家是一家人呀,咱可犯不着去捅马蜂窝!”
杨度望望老师的白胡子,又望望周妈的阔嘴巴,笑道:“我熟悉他们的内幕。他们表面上情逾骨肉,比老子儿子还亲,实际上,相互意见很大。段歪鼻子是个刚愎自用的家伙,对老袁也不大听话。老袁早就有意撤换他,一是一时无人代替,二是怕伤小站旧人的心,才迟迟没有行动。只要时机成熟,松坡完全可以取而代之。这不是争私利,是把将来军阀割据之祸,消弭于无形之中。松坡认为怎样?”
席上的目光都集中在蔡锷脸上。
蔡锷平静地笑道:“晳子是个热心人,我没说一句话,就把我推到候补总长的位置上了,只要对国家有利,我当然乐意干。不过,寄人篱下,一切要听命于人,这不是我们自己说了算数的。以后再说吧。”
这几句话使这个话题冷却了,大家开始说着其他闲话,蔡锷有事要先走,杨度离席去送他。王闿运对夏寿田慢吞吞说:“晳子才高气傲,以澄清天下自许,而往往急于求成,考虑不周;松坡智虑深沉,不露锋芒而胸怀大志。如松坡能与晳子合作,他们的成就将是不可限量的。”
)第四节 畅游三海
第二天,杨度陪同王闿运和夏寿田坐着马车,前往总统府。
在马车上,杨度向他们介绍:“逊清皇帝溥仪已让出中南海和北海,退居皇宫乾清门以北,神武门以南,自成小朝廷。现在总统府就占有三海。北海、团城、中南海都划入总统府范围,号称‘三海’。”
王闿运拈着须尖点头叹道:“这三海,当年可是禁地呵。”
夏寿田问道:“我看到报纸上披露,总统的年俸是三十六万元,比美国总统还高一倍多;总统的办公费四十八万元,交际费三十六万元,这些数字准确吗?”
杨度摇摇头道:“这不过是法定数字罢了,总统的特别费是没有限制的。这都是梁财神那批混蛋干的好事,他让总统可以任意批条子到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取款。人们都说,中交两行是袁家的金库。要真正实行立宪,就不会这样让梁财神闹得无法无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