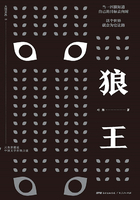据说,当一个人进入一个新的环境时,他往往会不知不觉感染上那里的气氛。这时,王良正觉得非常的渴,非常的饿。他以为这是环境的感染,其实不是。从昨天早上到此刻,他只吃过一把炒面和五六根半截面条子,喝过半碗黄褐色的面汤,怎能不又饿又渴呢。
他走出生产队办公室的院子,便和李明贵分手,他沿中村的小街去上村,李明贵去下村。他一路上坡,走得很吃力,便把脚步放慢些。中村小街上仍是没有人影。他向四边观望,除了沟那边莽莽的黄土荒山,以及沟这边灰扑扑的矮屋、几株死树和一条死蛇般躺在面前的路之外,眼前一无所有。一种荒凉、枯萎、压抑、肃杀的气氛把他这几年来沉积下的郁闷全部从心头引发出来。他真想仰天长啸,以使自己的血液保持流动,但是他没有敢发出任何声音,依然沉默着继续向上走。他想尽快见到薛永革组长,尽快报到,尽快开始在这个新环境中的改造生活。当他正感到十分孤寂的时候,忽然,他发现前方五六十米处有一个人,正俯身在路左侧一家人的院旁。他是在这个人直起腰时才看见的。这个人一转身,王良便认出,这就是早上拉着那个名叫李秀秀的女人从村边走过的男人。他记起方才李山梁书记和李明贵关于这人的对话,他知道这人就是学校的李老师。王良立即好奇地想:他又在干什么?直想几步奔上去仔细看看。但是再想想,自己是个有问题的人,又是刚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不应该多管闲事,便忍住没有走过去。他见这位李老师直起腰以后,继续往前走,在不远处拐进一条小巷里。王良记住李老师弯腰下去的地方,只是出于好奇,向那里走去,想看看他做了什么。那是一家庭院的入口,这家是一间屋的建造格式,院子也小,院口在猪圈右侧,他正是在那里俯身下去的。王良真是奇怪了,那里放着一小堆刚刚挑来的野菜,全是荠菜,一苗苦菜也没有。多肥多新鲜的荠菜哟,还沾着露水呢。明明是刚才那位李老师放下又走开的,这是怎么回事?再仔细看看,那荠菜堆旁的墙脚边,还有两支铅笔粗细的长长的黄色草根,显然也是有人挖了放在那里的。王良后来知道那是甘草。这又是谁放下的?他带着心中的疑问离开,向上坡走去。
快到上村时,迎面走来一个人。他中等身材,留着马桶盖似的分头,皮肤粗黄,小眼睛,塌鼻子,厚嘴唇,有点像漫画家丰子恺笔下的那个阿Q。这人身穿绿色军装,大大的裤脚下露出一双土里土气的千层底双梁黑布鞋,背个绿色军用挎包,年纪约莫三十岁。王良立刻判断出,这无疑是薛永革组长。村民是不会留分头的,他们都剃光头,或者任其乱长,梳也不梳,身上更不会有这种军装。他便立刻整一整自己身上的蓝色干部服,把领口的扣子扣上,再迎上去,称一声“薛组长”,半弯腰地一鞠躬,双手递上那封介绍信。
薛永革也猜到这是新派下来的人,早在远处便露齿表示着欢迎。他快步走到王良面前,见这位同志并不握住自己向他伸出的手,而是先鞠躬行礼,再递上一封信,已经有些诧异。薛永革连忙撕开信,那里面大约没有许多话,他马上抬起头来:
“咋的?你是右派分子嘞?”“是,我是右派分子,还没有摘帽。请你帮助我在这里继续改造。”薛永革犯难了。他需要人来工作,却派来个政治上不能信任的分子。“你是省里的?”
“是。从北京下放到省里,才两个月。”“啊,还是北京的嘞,中央来的。”
薛永革的口气表示,王良从北京来这一点,在他思想中颇有重量,似乎一个北京的右派和一个小县城的好人比,也有那么一点优越性。这种推理符合中国人上尊下卑的观念。一定是这个信息促成了他面部线条的变化,好像嘴唇两旁划出了一对尖形的括号,眼角上的鱼尾纹也变得明显了一些。这个信息同时也促成了他要王良分担工作的决心。王良等他吩咐。薛永革不说话,缓缓往中村走,王良紧跟在他身后,要求他派自己一个固定的劳动岗位,说自己保证完成任务。搞食堂、下地生产,做什么都行。薛永革不同意。他脸上那种似乎是微笑的表情一直保持着,这至少比王良近几年经常在上级脸上见到的横眉怒目好一些。王良非常重视薛组长脸上的这种表情,因为这跟他在这个山沟里将有怎样的处境有必然的联系。他正在心中研究分析这位新领导对他是如何的想法时,就已经走到中村村边了。这时,薛永革组长站住对王良说:
“介绍信里只说明你的政治情况,没有说你下来只能参加劳动,不参加基层工作嘞。”
“右派分子是改造对象。我下放河北农村也是只参加体力劳动的。”“右派是敌我矛盾,要在人民内部处理呀,这是毛主席说的嘞。”王良没敢再说话。“党和人民没有把你抛弃,你不能自绝于人民嘞。你现在还是在人民内部呀。
我在这里代表党执行政策,怎么能忽略这一点呢?再说现在是在火线上,你知道吗?火线上呀,正是用人的时候嘞,我们部队里是讲究火线立功、将功折罪的嘞。这正是你争取重新做人的好机会啊。”
王良不敢反驳薛永革的道理。他需要用人了才说这话,这就是薛永革的辩证法,有一些当领导的人是很会耍弄这一套的。王良心中暗想,原来这人并不像自己方才想的那样土,他还是有一套办法的。就这样决定了:薛永革不对村干部说出王良的右派身份;王良在薛永革组长的领导下,负责把下村一片的工作搞好。王良说自己没有资格,有难处,不能做。薛组长先是用那双小绿豆眼睛瞪了王良一下,见王良低下头,他又拿出那种似乎是微笑的表情,说:“你是中央干部嘞,做这点工作算个啥?一切有我负责嘞,你就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好好干嘞!”王良还能说什么话?薛组长接着便谈起正事来:“上村出了点事情,要马上处理。我们这就叫上李山梁,一同去看一看嘞。
下午你留在那里,我给你说说全队的情况嘞。”他们找到李山梁。不等薛永革说上村的事情,李山梁递给他一张委员李江玉老师写的纸条,他要求开个支委会研究一下。薛永革接过纸条看一遍,往桌上一掷,不屑地说一句:“就会说空话!”说完瞅王良一眼,拿起那纸条交给王良,叫他也看看。这位提意见的人建议党支部采取紧急措施,防止队里儿童和孕妇的死亡。具体意见是:一、给一些情况严重的幼儿和全队唯一的孕妇吃净面饼子,叫队里身体尚好的人和党员团员每人把粮食让一点出来。这位老师愿意第一个让出一部分自己的口粮;二、考虑停止办食堂,把粮食分给各户,鼓励大家自找食物,保住身体。薛永革根本不考虑这个意见。他气愤地说一句:“典型的知识分子,纸上谈兵!这第二条意见根本上就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嘞!”他把那纸条揉成一团丢掉,向李山梁叙说起上村发生的事情。
上村出了这样一件事:李树旺两岁的孩子前天死的,昨天埋在村后半山坡上。而今早有人发现,尸体暴露在外,下半截,屁股以下,连两条腿,没有了。李树旺家女人在村里、坡上没命地哭喊。薛永革一早去看过,叫人先用麻袋片子裹起来,又把那女人赶回家去,便来找李山梁商量办法。村长李满坡住上村,本来可以推给他去办的,可他上个月底借口去亲戚家治病,带上女人娃娃走了,一去不回来。薛永革要李山梁和王良都去看一看,他大概是不愿意一个人担责任。
王良随着薛永革组长和李山梁书记一同走到上村尽头的南山脚下,从这里可以更清楚地看见远处那两座并列高耸的圆锥形大山。打开麻袋片,那丢在坡上的半截孩子尸体血淋淋的,那肉是紫红色的,细细的肚肠拖出来,真不敢看。丢失的部分被截得那么整齐,而且是从厚土层中刨出来的,不像是野兽所为。谁干的?为什么……王良不敢想下去。薛永革和李山梁都一声不吭,更轮不到他说话。三人在坡上站一阵,最后薛永革对李山梁说:
“埋掉算啦。你去给李树旺说,狼吃的嘞。叫他女人老实点,不许大哭大叫。反正死孩子一个,又不是活活弄死的,哭个啥嘞!”
他接着又吩咐李山梁,去上村一家家传个话,不许借故造谣生事,否则按搞破坏论处。李山梁临走时他又补一句:
“死亡数字上添一个行啦,别的上报时就甭提了嘞。”没等李山梁走远,王良听薛永革自言自语地说一句:“这种人的孩子,活该嘞!”他不是对王良说的。王良也摸不清头脑,心想也许这是个坏人吧,但是他没敢多问。两人都沉默了一阵,才向村中走去。
王良在上村吃午饭。上村管食堂的女人外表看来四十岁上下,大家叫她七姑。她是村长李满坡的第七个姑姑,单身一人住在最南头山坡底下。王良后来听说她长期以巫术为业,真有点意外,第一眼看见,好像并不能察觉她身上有多少巫婆的邪气,只是让人直觉地感到,她跟一般的乡下女人,尤其是这山里蓬头垢面的、在当干部的人面前每一根汗毛孔都流露出胆怯的女人们,鼻子眼睛嘴都不大一样。她衣着比较干净,脸上也没有三个白圈圈,浑身上下有那么点诱人的东西,王良也说不清是什么东西。是那双灵活的眼睛?是那张略显扁平、表情活泼、微笑中含着挑逗的脸面?是那对因年龄而稍有下垂,却仍然耸出两颗刺人眼睛的乳头的胸脯?还是那副明显是葫芦型的细腰大臀的体态?反正这个女人让王良看了第一眼、第二眼,还想再多看几眼。这个李七姑把伙房和她自己都收拾得干净整齐,屋里虽有苍蝇,比下村食堂要少多了。菜饼子也做得细致,苦菜都是洗净切碎的,苦水也挤得很净。李七姑见王良坚决不肯吃净面饼,要和大家吃一样的菜饼,特地用她自家的窖水,还加了盐,为他烧了一碗荠菜汤。虽然没有油水,但是也很好吃。那裹了燕麦粉的苦菜饼子真难下咽。尽管李七姑做得细致,那苦菜饼子仍是又燥、又硬,好像直接在啃坡上的草。燕麦粉只是装饰,少得可怜,一抖就掉,除了被压成扁圆形之外,它毫无任何“饼”的特征。王良只得尽量用那碗荠菜汤把咬在口里的草往下冲。相比之下,那汤真是美味。李七姑不声不响,给他送上第二碗汤来。王良很不好意思,因为让她发觉了自己吃苦菜饼的感受。她一边递碗给他,一边说:“头一回吃这个吧?慢慢会习惯的。”说时面带和善的微笑。他们便有了交谈。王良向她问起坡上李树旺孩子的事。李七姑只摇头,也不开口,让王良没法再往下问。她的一双眼睛很动人,喜欢盯住人看,像会说话。她好像在用眼睛悄悄地对王良说:你是谁?你来干什么?你觉得我怎么样?大概每个做巫婆的都有这个本领吧,否则怎么迷惑人?王良在心里拿她这双眼睛跟早上见到的女主人秋眉嫂的眼睛相比较,觉得还是女主人那双眼睛美。那双眼睛里透着柔情,而这双眼睛中虽也含情,但却带有一股勾引人的光芒,明显地流露出一种肚子饥饿之外的那种女人在男人面前才会流露出的饥饿来。但是,这双眼睛中又似乎有一种女主人秋眉嫂眼中所没有的力量。走出伙房时,王良不由得回头望了李七姑一眼,发现她也在背后望着他。
王良已经走下坡,回头看不见这位李七姑了,她却仍然立在伙房门边上。李七姑今天确实有了些心思。这偏僻的山村里,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一个男人。念书人也有过,比如李江玉老师,可是,李老师多年来连跟她说句话也不情愿。可是这一个,这么年轻,这么壮实,这么漂亮,待人还这么和气。想到这里,李七姑把头发一甩,叹了一口气,不再想下去,回到伙房去做她自己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