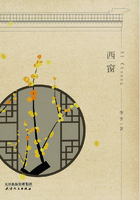几天后,奉薛永革的指示,王良去拜访李江玉,想要他恢复上课。这样,这位薛组长便可以向上级报一份已使他管辖下的人民安居乐业的功劳。这项任务不好完成,人人都说李江玉古怪,但王良从他上次和李山梁争论种子拌农药的事上,认为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从他对待李秀秀的事上认为他这人心肠好;上次在道口接他时跟他的交谈中,也觉得他并不是一个不好相处的人。或许李江玉的“古怪”正是一种与自己相投的知识分子特点吧。薛永革说,上次做李树旺的工作,证明知识分子有一套,非叫王良“再上一次火线”。李山梁赞成叫王良去,他说跟李江玉谈话怕是只能王组长去,王组长肚里墨水多,只有王组长才能说得过李江玉。薛永革听李山梁这样讲,脸上很不高兴。
学校办在李家沟的祠堂里,在中村一条巷子中,就是那天王良见李江玉走进去的那条巷子。李江玉自己也住在祠堂里。这祠堂的门楼足有两丈高,有些破朽了,但仍是全村最巍峨的建筑。走到门口,王良一抬头,看见四个砖刻的大字:“飞将军祠”。原来李家沟人是汉朝飞将军李广的后代,他不禁肃然起敬。院落比一般农家大多了,又因为有围墙,没有猪棚牛圈,显得空荡荡、阴森森的。屋顶是黑色的瓦,生着一列列暗绿色的瓦松,木柱和门窗上是斑驳的红漆。从大门到正殿,有青砖铺砌的走道,砖缝里长出几株稀疏矮小的绿草来。整个祠堂中,黄土色比较多,这几株小草更是给这个庞大的荒凉环境平添了一点生气。不过,这种生气毕竟少得可怜,敌不过这座破烂古庙式建筑和门外那莽莽的黄土世界共同构成的压力,只给人一种徒然挣扎的感受。正屋是殿堂,左厢当教室用,右厢和一间披屋给李江玉老师住。他在父母妻儿相继死去后,丢开老屋,搬到了这里。院里静得很,王良推开殿堂那掩住的门,头伸进去望望,一种庙宇神坛的肃穆气氛让人心悸。他没有踏进门槛,只立在门口张望。正面是坐北朝南的神龛,没有塑像,正中一块半人高的牌位,红底金字刻着:汉大将军李广神位。它左边有一块小些的牌位,供的是汉骑都尉李陵将军。香炉蜡台供桌都很有气派,但是都很古旧,被蛛网和尘土封盖着。殿内乱堆些砖头木料,也都陈旧了,大概是哪年修整用剩的。右边墙上是一幅“飞将军驱匈奴图”,是哪个乡下匠人的手笔吧,用黑墨描在石灰墙上。那跃马扬刀的将军,两眼好似两只铜铃,倒也炯炯有神。左边墙上是密密麻麻的楷书,从起首几句看,大约是《史记》中《李将军列传》里的一段文字。这些字、画、神龛、牌位怕至少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了,保存得还算完整,可见村民对英雄祖先的崇敬。那间当教室用的厢房是破门破窗,黑板是用三合土在墙上抹过,再用锅灰涂黑的,桌凳全用土砌,多已破裂坍塌。李老师住的那间屋上着锁,披屋敞开着,那里是水窖口子和一些柴火。院子里静得怕人。王良走出大门,想找一个人家询问一下。
祠堂旁住的一家人告诉王良,李老师可能在东山他妻儿的坟上。这时大约八点来钟,王良便向东山走去。村东这片山坡,近年来不知不觉变成了公墓,一个个新垒的黄土堆,记录了李家沟人这一时期的饥饿史。山坡上一片空寂,王良仿佛听见从那一只只坟堆中发出“咚──咚──咚咚”的声响。他想数一数一共有多少座新坟,但他的手指好像又在依着那“咚──咚──咚咚”的节奏数着数目,让他不愿再数下去。这里缺石料,过去坟墓都是用砖头修砌,墓碑也用砖,讲究一些的人家,把方砖磨平,对缝,刻上字,再造一个围框,也能保持许多年。这些新坟都是没有碑的,大约是没有气力花在这上边,或者是一时之间要做这许多也来不及。山坡上没有人,王良举目四望,黄色的山峦下,黄色的土坡上,是一堆堆大大小小的黄色的坟茔。在那零乱布置的坟堆中,有一座特别显眼,它稍稍高大一些,坟前竖立着一块木板,这是其他坟堆前所没有的。王良向它走去。那木板上用苍劲有力的魏碑书法,工整地写着“爱妻立红爱子迎水合葬之墓”,时间是当年的二月,立碑者的题名是李江玉。王良没有马上走开。伫立墓前,他默默请求死者接受一个陌生人的凭吊,心中不禁怆然。他正想离去,无意间发现,那木牌的背面好像也有字迹,他在那儿读到十二行五言诗。王良对这倒很有兴趣。他想不到李江玉在这一点上也是他的同好:
食色人性也,我今两空空,青山绿水情,一黄土中。死者长已矣,生者何所终?悠悠天地间,苦雨卷凄风。别矣我水儿,别矣我立红,泉下相见时,且诉苦与衷!
在这满眼空寂的凄凉的黄土世界里,这些哀怨动人的诗句和周遭茫茫的蒙昧很不调协,显得有些突兀。不过,这些诗句也让你感觉到,这蒙昧的原始的饥饿的世界并没有和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和文化相隔绝,并且也没有完全和人类的情感、希望、追求相违背。然而,这感情是多么的沉重,这希望和追求又是多么的渺茫而无力。
今天没有见到李老师,王良倒觉得很好。他不应该贸然去跟李江玉谈学校的事,而应该先多多了解一些李老师的情况,否则怕谈不拢。王良沿山坡信步走去,心中反复品味着那块墓碑上的忧伤的诗句。王良觉得,李江玉的情感领域比他自己开阔得多,自己写的诗比不上人家写的。不过两人的风格有些近,这让他觉得亲切,到底是同一代人。
不知不觉走到了上村,王良去向薛永革报告任务没有完成。薛组长不在屋里。王良路过李树旺家,远远看见他一个人赤着身子在屋前埋头翻弄着脱下的上衣。王良已经熟悉了村民们这种常见的动作,那是在捉衣缝里的虱子。有些人在捉到的时候,还一只只送进嘴里毕剥地嚼碎吞下去,让这点营养再返回到自己的身体里。他们大多不情愿让王良这个外来人看到这动作。王良远远地叫一声:“树旺!”李树旺听见,披上衣服,迎他走来。
“嫂子怎么样?还好吧?”王良问道。
“好。躺着哩。”李树旺话不多,但态度是欢迎王良的。王良随李树旺走进院里,两人并肩蹲在上次谈话时蹲过的地方。又是一阵长长的沉默,这回王良先说话:“我去找李老师的,没找见。”“找江玉呀。他,好人啊。”“你们熟?”
“论辈分,他叫我爷呢。出五服[1]了,不计较啦。”王良还没说话,李树旺又说了:
“江玉给咱李家沟做好事。办了十年学,赔上个媳妇跟个十岁的娃。”“他孩子死时十岁啦?”“嗯啦。阴历年时候,跟他娘前后隔三天。可怜哟。”王良觉得自己又更深一层地进入到李家沟人的悲哀里。他不愿再问下去。一阵沉默后,李树旺又说:“听说秀秀那妹子男人也不行啦。叫她往后就伺候李老师一辈子吧,他两人都会情愿的。”“能那样倒真是好。”王良说。又一阵沉默,王良便找话说:“这天热啦,有几棵树该多好!”
“树?”李树旺转头瞪王良一眼,才说,“人家说这是划定的粮食自给区,不叫种树。那年村长李满坡费多大力种上的,都叫给砍啦。”他告诉王良,几年前,高级社时,李满坡曾经弄来些梨树苗,种在梯田上。后来被当做违反统一规划的资本主义表现批判过,他做了深刻检讨,自己去砍掉。后来没人再种过。
“那山上不能种吗?”王良忍不住要再问。“山上?种了归谁?怕惹麻烦啊!”王良又陪李树旺默默地蹲一阵,眼睛定定地望着李树旺颈后那块亮亮的伤疤,望着他那张一动不动的、满是皱纹的古铜色的面庞和一双深陷的充血的眼睛,王良这时恨不能分担一点李树旺心头的忧愁和哀伤。该回下村吃饭了,还要走五六里路,王良立起身来,李树旺却示意叫王良再蹲下。他慢腾腾地问王良:
“李明贵家女人是咋的?昨天夜里从七姑子屋里哭着跑出来!”李树旺这句话令王良猛地一怔。秋眉嫂这几天对王良态度的变化正让他心中[1]五服:中国北方旧时的丧服制度,以亲疏为差等。民间“出五服”的概念是笼统的,泛指同宗而极远的亲属关系。
不得安宁。昨晚她不知哪去了,好晚才快步奔回家,进院子时一只手蒙在脸上。明知王良立在正屋门口,也不和他打招呼。她进屋后,王良听到李明贵的吼声和她的啜泣声,只是没听清他们说些什么。王良这一天心里正搁着这事,听李树旺一说,王良连忙叫他快说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