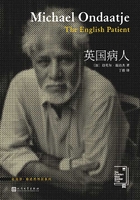小王是我许多学生当中的一个。几年相处,师生情深,渐成忘年交。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他忽然来访,带着个重重的提包。他从中取出一大捆陈旧的稿纸来,这是一部小说的手稿;取出几本残破的线装书,这是一部木刻本的《诗经》;还有一枚用一块布手巾包着的绿锈斑斑的铜质顶针。他把这些恭恭敬敬地放在我面前,向我述说了一个故事:
他的父亲,名叫王良,十多年前在中国大地上那场史无前例的“革命”中死去。这几件东西是这位先生的遗物。儿子读过父亲的手稿后,知道这两件东西和这部手稿是不可分离的整体,便把它们一同收存,直至今日。现在,他把它们郑重地托付给我,请我代为保存。他家在国内再无亲人,而他本人已决定,像许多当代的青年人一样,离开这片土地,去世界的另一边,在另一片天空下和另一片土地上,为自己寻找另一种生活,另一种命运。
小王告诉我,父亲含恨而去时曾反复地说,他一生都忘不了他所描写的那黄色的山、黄色的土地、黄色的天空,以及那片天空下,那片土地上,在黄土中生、黄土中死的那些人。他把那段生活用他自己真实的名字和第三人称的小说形式写下来,是想让它随时生动地再现,成为永恒的存在。他希望自己能随时回到那段生活中,也希望后来人如果有机会读到它,能从中了解生活、了解情感、了解人性,同时也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那一段历史。他说,这部木刻本《诗经》和这枚铜质顶针以及包它的那块布手巾对他而言是神圣的,上边凝聚着一种真诚的爱和一种永远的遗憾。
受此重托,我不胜惶恐。我把两件物品安置妥当,便来拜读王良先生的手稿。一口气读完,我深受感动,便萌生了把它发表出来的念头。我觉得,这里有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有好几颗至今仍跃然纸上的心。它虽是一去不复返的往事,但它像人间所有的往事一样,常常成为一面最忠实的镜子,成为高悬在我们每个人头顶上的一盏永不熄灭的明灯。经常照一照它,会让我们的脸上更清洁;当我们向前迈步时,它会帮助我们判定路途、选择前程。我不能让这部书稿在我的手中就此埋没,否则王良先生这一辈子岂不真是白活了?他不也曾是一个爱过恨过,有血有肉、有才能有追求的人,一个吃过许多不该吃的苦的人吗?于是我便为这部作品的发表而忙碌了一阵。感谢一些朋友的热心帮助,现在它已与大家见面。以下的文字,与原稿丝毫不差。唯有“饥饿的山村”这个笨拙的题名是我加上的。我没有像普希金在《别尔金小说集》中所做的那样,把它就称作“已故王良先生的一部小说”;给它加上这个名称,是为了多少传达一些作品的内容。
作为这本书的作者,我似乎应该说一点自己对它的感受。我喜欢这本书,它实实在在地写出了我们国家在那个年代里的一些大事,诸如天灾人祸、“三面红旗”和“反右”斗争等等;并且它在感情上很能打动我。我觉得这也是一本写人性、写人间真情的书,而不只是一本记录真实生活的书。我深深地为王良这位已经离我们而去的同辈人感到遗憾,他这一辈子活得太苦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处境,这的确像他所说的那样,是我和他那一代人中许多人的共同遭遇。这怪不得他,这是生活本身造成的;但是无论如何,他真不应该去死啊!如果他能坚持下来,活到今天就好了。但是,无论如何,王良他是绝对没有可能感受到我们今天所感受的一切了。当然,他再也不可能把他的才能发挥出来贡献给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事业。这遗憾将无法弥补。我想,只有我们这些没有遭到和他同样命运的人,才会更加珍惜我们的今天,更加努力地为我们的伟大祖国和伟大人民而工作,借此给这种并非只是他一个人的遗憾稍微做一点补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