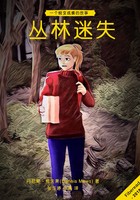这天,王良在队部办完事从中村回下村去吃午饭。他是绕东边小路走的,没有沿大沟走,想顺便多看看这里的情况。大晴天,黄土中蒸发出热气,空气十分沉闷,没有树,连灌木丛也没有,土地和人都逃不脱一颗红太阳的烧烤。一路上一个人也没遇见,王良不觉沉入独自的遐想里。他想到,太阳这东西,真有些奇怪,世间万物都离它不得,但是谁也不愿意蒙受它过多的热度,连没有知觉的泥土地,离它太近了,也会被烤成荒漠。他不禁自言自语道:太阳啊太阳,你若有灵,应能主动随时调整你的温度和你与世界人类的关系,做到天下处处都沐浴到你的温暖,又不至于被你伤害,那该有多好!当王良从沉思中醒来,太阳却更加烫人了。四周一个人也看不见,他加快步子,想早点回屋休息。他已经走到下村了,一拐弯,出乎他的意料,迎面走来了一个人,是李秀秀。她好像是从牛庄回来,不愿意走村里的路,定是怕遇见熟人,特意走这条小道,想不到偏偏和王良碰上。她真想找个地方躲一躲,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便站住不动,低下了头。
王良也没想到会遇上她,不知说什么好,便先喊了声“李秀秀”。这样招呼了她一声,再走到她身边停住。王良本想问她是不是从牛庄回来,可是他刹那间多了个心思,没有这样问,而是改口问道:
“你家里的身子好些了吗?”
李秀秀不说话,仍是站在那里,低垂着头。过一会儿,王良又问她:“你的头痛病好些啦?”李秀秀还是没有回答。她是很想回答王良的问话的,她知道王良问她是出于一番好意。但是她怎样回答呢?她一见王良,心里便有着那天牛庄的事。那天以后,她心里老是有着他的影子,真想再见到这个天下少有的好人,真想跟他说几句话,不光是向他道谢。在李七姑家碰上了他,因为有李七姑在,想说的话没能说,今天有了两个人单独在一起的机会,可是怎么开口呢?自己做的事多丢人啊,他会怎么看我这个人……想着想着,她自己也没有料到,忽然说了这样一句话:
“王组长,我是去牛庄拆那个窝棚的。我以后再不去了。”
她这话说得过于突兀,让王良不知怎样回答,他连忙说:“我没问你这个。我问你家里的和你自己身体好些了吗?”李秀秀并没有回答他的问话,却向他深深地鞠一个躬,腰弯得几乎头碰到膝盖上,嘴里低声说:“王组长,我谢谢你。我对不起你,你是好人,我是个坏女人!”说完便呜呜地哭起来,一边悄悄张望着,想从王良身旁找个空处溜过去跑掉。李秀秀的话让王良心里难过。他想起李江玉那天自言自语的话:“多好的妹子哟……把人饿得变成了鬼……”又想起那天她忽地解开衣裳的样子……他心中涌起对这个女人的强烈的怜悯和同情。他连忙说:“不要这样说话,李秀秀。你没有做错什么,不要这样说话。”李秀秀呜呜地哭得更伤心了。王良不知怎么办才好,只能用一个干部所能使用的言语安慰她。“秀秀,你是个好姑娘。你要挺过你一辈子里的这个难关,这灾荒会过去的。
我们的国家以后会好起来的,你以后也会过上好日子的。”李秀秀仍是不住地哭。王良只好继续说安慰她的话。“以后你就住回来吧,李老师说他家那几间老屋给你了。这里的乡亲,还有你爹妈,也会照顾你的。”见李秀秀只哭不回话,他又说:“我也帮不了你什么,不过我来这里要住一阵的,我能帮你的地方,你不要客气,找我好了。”听王良这样说,李秀秀哭得更厉害了。这样好心肠的话,这样认真的关心话,她一辈子没听见过几回。但是现在,她说什么好呢?忽然,她又向王良深深地一鞠躬,埋头便从他身边跑过,沿那条小道向后山方向跑去了。王良望着她渐渐跑远的背影,胸部被一种莫名的痛苦填满了。他长长地吐一口气,想把心头的郁闷全都吐出来,但是他没能做到。这时他真想再像那天在后山道口上那样仰天长啸,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怕惊动了村里的人。
王良站在那里,直到望不见李秀秀的背影了,才再叹息一声,转身往前走。忽然他发现另一个人蹲在一幢房子的背阴处,正伸长脖子,张着嘴,呆呆地看着什么。那是李二狗。王良顺着李二狗目光的方向望去,看见一个女孩子的身影,正猫着腰,低着头,手捂在下腹部,向一个低洼处快步走去,她的臀部和两条白光光的腿全都裸露着。过一会儿,这个女孩又用原先的姿势匆匆走回来,钻进一个圆形的窑洞般的住屋里。这时李二狗正立起身来往村里走,王良叫住他问一句:
“李二狗,你就住这里?”“啊,不,不,我住那头。”李二狗头也不回,指一指前面,不再跟王良搭话,就赶忙跑开。
王良到食堂,李二狗也在那里,正在跟李明贵说地里的事。两人有些争执,原来是二狗子那天没领到豆种,没去种,今天领到了,他合计一下,觉得他下午一个人种不完,想让李明贵跟他一同去,李明贵不肯。见他们争执不下,王良便说,下午自己去给李二狗做帮手。吃过午饭不久,他喊上李二狗,二人一同上山,找到那块三角形梯田,便干起来。李二狗刨坑,王良点种,边干边聊。李二狗告诉王良,他上次奔出去到过宁夏、包头,干过一阵建筑工地临时工,后来被当盲流遣送回省城。王良问他在外混了多久。
“半年。”“回省城多久了?”“不到两个月。”“在省城日子咋过的?”
“先是关在收容所里,后来人多挤不下,溜出来了。找不到活干。那里盲流也不少,天天蹲在饭馆子门前,瞅准机会捞一点吃的。”
王良在省城遇上过像他这样的人。有一回,他买一盘炒面,刚坐下,肩后便伸过一双肮脏的手,像铲子一样把盘中的面条一下子全部刮进那双手心里,接着便往抢到手的面条上吐口水,缩着头向门外逃。当这人从两排餐桌中间挤过去,店堂里的人都狠狠往他头上和背上猛击,还有人用吃剩的汤水泼他,这些他全不在乎。那天王良只好自认晦气,没吃上饭。
“哪天回县城的?”王良又问李二狗。“上前天。县城收容所里不好过哟,打人凶得很。我不等他遣送,自己溜回来了。”李二狗停了停又说,“有火车,便当得很。”说起那天他挨李山梁打的事,李二狗说他不记恨山梁叔,再说也没打疼。他说:
“若不是山梁叔,谁给我埋爹娘啊。”他告诉王良,李山梁亲手下葬的无依无靠的死者至少有五六十人。
“早知爹娘没了,我就不回来啦。唉--”“爹娘为了叫你活下去才叫你奔的,是吧?不回来死在外头图个什么?”“回来就不死啦?”
“国家有救济粮呀。”“这五六斤粮一个月,就能活人啦?”“那你还想奔?”“吃不饱,难活命,我就奔。”
这年轻人身上有一股犟劲,虽然饿得这样,还要挣扎。王良见他还可以谈得通,劝他相信党的政策,安心跟全村人一同努力度过这灾荒。李二狗不回话,脸上也没有表情,只闷声刨着土坑。
王良想起午饭前的事,便乘机问他:“你早晌去村东头干了什么事?”
一听王良问这个,李二狗好不自在,哼哼唧唧说不出话来,王良马上猜到是怎么回事。
其实王良哪是想要责备李二狗。这傻小子,只不过是在自以为别人不知道的情况下,表现出了自己的一种违背社会的,但却又是出于自然需要的欲望而已。世上做这种事的,远非他一个人。早上一看见李二狗那副姿势,王良马上就想到过去的一个同事,一位有点名气的单身大学教师,中国古典文学专家和作家。那一年春天,他被人抓住时,正躲在学校女浴室的角落里偷看女同事们洗澡。见李二狗那张尴尬面孔,王良觉得真好笑,便问他:
“看人家姑娘家上茅房,是吧?”李二狗低着头,停住脚,手里的锄头也不动了,像是等着听王良再说什么严厉的话。
“你呀,不嫌丢脸!你多大啦?”王良说。
“十七啦。”李二狗低着头回答。“想讨女人啦?那就好好干,过几年找个对象成个家吧。”王良眼盯着李二狗,看他那副熊样,心里只想笑。“对象?就凭我?”听王良的口气并不严厉,李二狗把头抬起来说。“你怎么啦?正正当当做人,还怕找不到个媳妇?”王良说着便笑了起来。这小子机灵得很,见王良没有跟他为难的意思,也放心地笑了,他主动把话题扯开去:“说起‘对象’,我倒是已经当过五六年的‘对象’啦。”李二狗说。“什么‘对象’?”王良不理解他的意思。
“批斗对象呗。高级社时候就说我是资本主义种,就为前几年我爹叫我去卖过甘草啥的。去年更不对了,说我是反革命破坏,反对人民公社化。”
“为什么?”“为我说过几句话呀。”“什么话?”
“怪话呗。”
“什么怪话?”王良真好奇了,所以追问李二狗。也因为四周除了黄土山,没有人能听见,他才胆大些。
李二狗抬头把王良看一眼。在他那似笑非笑的脸部抽搐中,王良不知怎的发现他并不拒自己于千里之外。
“我编过个顺口溜,只说过一回,就狠狠斗我好多回。”李二狗说。“你还会编顺口溜呢?”这年轻人说得舒畅了,收不住嘴,便告诉王良,公社化正高潮的时候,有一天他不知怎么顺口说了四句话:“绿化白吃馍,鏖战砸铁锅,排队上厕所,婆婆比狗多。”他指的是那时号召绿化荒山,一人一天发五个大馒头,大家在山上乱撒些种子,并没树长出来,但是不几天就把村里的存粮吃光了;为了完成全李家沟炼出一吨钢的伟大光荣的任务,上级号召大家“鏖战三十天”,结果是砸了家家的铁锅作原料,也没炼出一块真正的钢来;那时下地干活要排队,休息时才许去撒尿,又要排长队;从县里到公社,到大队、中队、小队,当干部的人比下地干活的人多,当真比村里的狗还多。听了李二狗说的这些,王良心里暗想,这个小家伙还真聪明呢。但他不能不顾及自己的身份,便故作严肃地对李二狗说:
“往后说话要当心!要注意影响!‘婆婆比狗多’,这不是辱骂干部吗?”李二狗的回答是:
“我怕啥?爹娘跟我哥,一家人都死光了。还怕啥?”“那你自己呢?”“我自己?你们反正不会把我当好人。”“我们?你指谁?”
“干部呗。”“你这是对立情绪呀,这不好。干部都亏待你啦?”
在王良最后这句话的提醒下,李二狗也觉得自己话说过头了。他有些自惭,便告诉王良,李山梁昨天找几个人,帮他把一间屋拾掇得能住人了,他的口粮在回村的当天就发下来了。他说:“要遇上别人,先拖你十天半个月,给你点颜色看看。”
太阳落坡了,还有一半没种上,还不能收工。四周的黄土丘荒寂得给人一种可怖的肃杀感,此时此刻他们两人各自的存在对于另一个在精神上和心理上都是重要的。谈话是他们唯一驱除恐惧的办法,他们谈起狼,王良告诉李二狗他那天夜晚的所见。李二狗告诉他,那只狼叫老灰,十岁了。它总是在同一个时辰出来,总是走那同一条道。
“它不乱吃人的,你莫怕。”他告诉王良,那年他爹喝醉酒回来,误走了沟右边的路,睡在狼道上,老灰也没碰他一根汗毛。
不过,李二狗又说,现在也说不定,还是小心些好。他说:“那时候野物多,兔子啥的,有它吃的,就不吃人了。现在人饿,狼会不饿?
人都要吃人,狼会不吃人?”“你胡说什么,人怎么会吃人!”王良又不觉地摆出了干部的口气。“咋不吃,活人不敢吃,就吃死人。”李二狗跟王良熟了,对他有了信任,还要把话说下去。王良听李二狗话里有话,明明是指上村李树旺家孩子的事,但他实在没有勇气谈起这件事,便不去问李二狗什么。可是李二狗却偏要说下去,像是有意让王良知道些事情。
“王组长,你们查出树旺家娃是谁吃的没有?”“薛组长没说要查的话。”
“要查也不难,我说个人你们去问问。”“谁?”
“李七姑。”李七姑!王良心里一震,她?这个女人?白白净净的,她做得出这事?但王良没说话,脸上仍保持着镇定。顷刻之间他思想中绕了几个弯:是该查查,这么大的事;但是我何必去管,既然薛组长不要查下去;多么可怕的事,能不想就不去想它!
他决定不接李二狗的话,只低头干活,李二狗也知趣地不再说下去。两人默默地点着豆。
正当这时,王良一抬头,望见李山梁的妻子一个人坐在中村边沿一块梯田的田埂上,他便自言自语道,天这么晚了,山梁嫂子咋不回家?二狗子一抬头也看见了。他说:
“是山梁婶子。怄气呢。昨天晌午把屋里碗砸了好几个,还去李顺家门口吵呢。”“为什么事?”
“准是为李顺家寡妇盼水的事。没啥,人都知道的。”“到底怎么回事?”王良定要李二狗说明。“李顺死了,那寡妇肚里怀着娃,六七个月了。山梁叔怕她生不下来,偷偷给过她吃的。婶子知道就怄气,她一怄气就大吵大闹,脾气躁得很。这些事我前那天一回来就晓得了,你咋不晓得?”李二狗停了停,喘口气,又说一句:
“给那女人送食的,又不是山梁叔一个。”他又停了停,再说一句:“全李家沟,能生出一个娃来,也好啊。”
“说来也怪,”二狗子继续告诉王良,“山梁婶子为她男人给盼水婶子送吃的怄气。可是今天早晨,我亲眼看见,她自己把一小篓子马兰头,拿去放在那女人的院子边。”
“你看见的?”“谁还哄你?她还叫我莫给别人说呢。”
眼看天黑了,今天不可能种完这块地,王良便和二狗子收工,一同往下村走。王良提着种子口袋,李二狗扛锄头。这天的黄昏比前两天阴冷,二狗子说怕要下雨了,若不是他家水窖塌了,现在第一要紧的,是赶回家把水窖眼子的塞头拔开。
“有条水渠就啥都有了!”二狗子带着见过世面的神气对王良说。“有水源吗?”“有--”李二狗用力气拖长声音,以一种先升后降的语调回答王良,表示一种郑重的肯定。“翻过那座山,”他指沟西那天老灰走过的山,“就是桃花河。只要打个洞子,开条渠,再接个过沟槽,水就来了。不难呀。”
一听李二狗说起桃花河,王良立刻又想起秋眉嫂讲的那个美丽的故事。但他没让自己走神,仍继续跟李二狗交谈。
“那为啥祖祖辈辈没有把水引过来?”“从前人心不齐,就莫说啦。解放后这些年,光顾办社呀,整人呀,这些事倒不忙去抓。”
王良感到李二狗这后半句话显然是一种偏见。解放十年来,共产党为人民办过的许多好事,他竟然全看不见。就拿他说的办社整人来说,也是共产党在努力为人民办好事。办社是发展生产,整人是整治坏人,都是当务之急。二狗子有这种思想,说明他是个落后群众。不过王良又觉得,这二狗子人聪明,也单纯,是个材料,要能改变他这些落后思想,以后能为队里做许多事情的。而且,他这一趟出走,对他未必是坏事情。他见到了这个山沟沟以外的世界,扩大了眼光,增长了见识,这也就减少了他身上与生俱来的蒙昧。他们二人默默地走着,天更暗了,王良不自觉地贴紧李二狗走,李二狗也不避开他。
快到下村时,李二狗忽然没头没脑地问王良一句:“王组长,人血好吃吗?”“什么?人血?”王良一下子没弄懂他的意思。
“我说那羊血、牛血、猪血、鸡血都能吃,我都吃过的。这人血也能吃吗?”王良还是没有把握住他问题的含义,只用两眼瞪着他,没有回答。李二狗却也不要王良回答,他自言自语着:“准是能吃的吧。”王良只笑了笑,把这当做李二狗灵活的头脑中一时浮起的胡思乱想,没当回事情。到了下村,王良去食堂帮李山青清理粮食账,便和李二狗分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