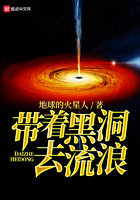常念提着一个竹篮子进来,她说,奶奶熬了粥炖了汤。说着就用勺子先盛两碗汤,一碗给肖芸,一碗给我。我靠着枕头斜躺着,念一勺一勺地喂我。吃着吃着,我心里酸酸的,鼻子痒痒的,喉咙里像噎住了什么东西,眼睛都红了。
常念却是恬美的,嘴巴一抿一抿的,那汤像是喂给自己吃了。她带着笑意,咬着唇,说,给你们猜个谜语吧。两个伙计,同眠同起,亲朋聚会,谁见谁喜。说着用筷子夹起汤钵里炖得稀烂的鸡肉放在碗里,她眯缝着眼睛。谁猜对了,奖一块肉吃。她对我与肖芸这般说。
肖芸乐了,她举起手,像课堂里的学生。哎呀,我想,我想,这物就是,两个伙计,为人正直,贪馋一生,利不归己。我强打精神,也掺和。呵呵,这物就是,两个伙计,终身孤凄,走遍天涯,无有妻室。念端着那碗鸡肉愣在那,咂嘴弄舌的,举起手里的筷子,呵呵笑,说,怎么都像啊。我们也笑。
念的到来,总是能带来笑声。不完全是她的可爱,大多的成分是老人对孩子因为怜爱而发自内心的一种迎合。顺着童真,开心大笑是自然的事,心灵的愉悦在那刻是绽放的。在笑的时候我忘了疼痛忘了疾病。念每天都来,趴在床前做会作业看会书,肖芸总是忍不住要伸手抚摸她,或是凑过去看她写字。种种迹象表明,有可能恢复高考。所以,有一天我对念说,你一定要答应我,好好读书,考到外边去上大学,去了解世界征服世界。肖芸马上反驳。为什么要到外边去,不要,就在这里,这里才有快乐!才有平静!我失神地望着激动的肖芸。把天资聪颖的念,一生都定在这是残忍的。而外边是否更残忍,是不可预知的。我闭上眼睛,思绪又乱起来。
念曾经缠着肖芸问,香港是什么样子。面对荒凉的村野,起伏的茶山,香港遥远得有些不真实,可是自己出生在那,年事已高的父母在那,兄弟姐妹在那。她抚着念,没想到自己能那么平淡地回答说,就是比我们这人多点车多点,吃的用的玩的复杂点。一个如此模糊的概念,让念顿然失去了解的兴趣。
疼痛再次袭来,我晕睡过去。淅淅沥沥的雨,一波又一波,时急时缓,连梦都是湿淋淋的。雨声一直很大,在雨中我纠缠着自己,醒来吧,醒来。可上眼皮却是沉沉的,无论怎么努力,就是睁不开。
梦与非梦之间,还能看见人影在晃动,可是自己却不能动不能说,一个人在那抗争,累得心力憔悴。倒是那个清晨,没有任何挣扎,我就醒来了。窗外湿漉漉的,空气像是从水里刚刚拎起,屋檐上的雨水滴滴答答,与床前铁架子上吊瓶里的水,一快一慢地往下落,不同的是,雨水落入大地,吊瓶里的水流进我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