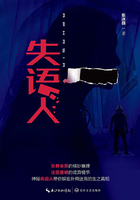凯特当晚就打了电话,弗兰克不想浪费时间。电话机里主人的录音让她愣了一下。这么多年了,这是她第一次听到这个声音,从容、干练、有节奏,就像步兵训练有素的跨步声。当那个声音响起时,她竟然浑身颤抖起来。她鼓足勇气才说出那几句简单的、意在诱使他步入圈套的话。她想见他,想和他谈谈,越快越好。她不断地提醒自己,他那么机警,不知道这个精明的老家伙会不会嗅出这是个圈套。然后她又想起她们父女俩最后一次面对面的情景,意识到他绝不会想到这是个圈套。他绝对不会把欺骗这样的事同当年那个把自己最珍贵的秘密告诉他的小姑娘联系在一起,就连她也认为他会这么想。
刚刚过去一小时,电话就响了。她伸手去拿听筒的时候,真心地希望自己从来没答应过弗兰克的请求。坐在餐馆里酝酿一个抓获杀人嫌疑犯的计划,与亲自参与唯一目的旨在把自己的父亲移交到当局手中的骗局,两者是迥然不同的。
"凯蒂。"她感到对方的声音有轻微的改变,还掺杂着一丝疑惑。"嗨,爸爸。"谢天谢地,这些话居然脱口而出了。这个时候,她似乎连最简单的思想也不会表达了。到她的公寓来不太好,他能理解这点。因为那样会显得过于亲近,过于私密。去他的房子也不合适,原因很明显,这点她也知道。他提议他们到中立地点会面。这当然可以。她想说话,他当然想听,迫不及待地想听。他们约定了时间,明天下午四点,在她办公室附近的一个小咖啡店。白那个时候,那里没有顾客,比较安静,他们可以慢慢谈。他会去的。她坚,除了死亡之外,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挡他。
她挂上电话,又给弗兰克打电话,告诉他会面时间和地点。听着自己的音,她终于意识到自己都做了些什么。她可以感觉到,突然之间,一切都始崩溃,她无法阻止。她砰地扔下听筒,泪水夺眶而出。由于身体抽搐得此厉害,她一头栽倒在地板上,身上的每块肌肉都在痉挛。小小的公寓里满了她的呜咽声,就像气球里充满了氦气,随时都可能发生猛烈的爆炸。弗兰克真后悔自己没及时挂上电话。他冲着听筒大吼大叫,可对方根本不见。其实就算她听见了,也没什么作用。她做得对,她没什么可羞愧,也没有什么可内疚的。他最后终于放弃努力,挂上电话。突然间,那种要接近猎物的亢奋消失了,就像燃尽的火柴那样熄灭了。他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她依然爱他。作为探长,塞思·弗兰克想到这便心烦意乱,不过还能克制。但作为三个孩子的父亲,塞思·弗兰克想到里便泪眼模糊起来。他突然发现,自己不像以前那样十分热爱自己的工作。
伯顿挂上电话。弗兰克探长果真守信,邀请这位特勤处特工参与行动。几分钟后,伯顿出现在拉塞尔的办公室里。"我不想知道你的行动方案。"拉塞尔看上去忧心忡忡。伯顿暗自好笑。不出所料,她开始谨慎起来了,既想把事情尽快了结,不想把自己漂亮的指甲染脏。"你现在要做的事,就是把情况告诉总统。而且你还得确保总统在我们动之前转告沙利文。他必须那样做。"拉塞尔满脸不解。"为什么?""这个你就不用操心了。你只需记住,按我说的去办。"拉塞尔正要发,他已经走了。
绎绎绎
"警察已确定就是他?"总统的声音里有一丝焦虑。他从办公桌上抬起头来。
拉塞尔本来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这时她停下来,看着总统。"嗯,艾伦,我在想,如果不是那个人,他们是不会费那么多周折去逮捕他的。""格洛丽亚,他们以前又不是没出过错。""这倒是没什么好说的,人人都可能犯错。"总统合上正在审阅的文件,站起身来,从窗口俯视着白宫的庭院。"这么说来,这个人很快就会被拘禁起来了?"他转身看着拉塞尔。"看来是这样。""那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最精心构思的计划有时也会出错。""伯顿知道吗?""整出戏好像都是伯顿导演的。"总统走到拉塞尔身旁,把手按在她胳膊上。"你在说什么?"拉塞尔把最近几天发生的事情全部告诉了老板。
总统揉着下巴。"伯顿在搞什么名堂呢?"这个问题与其说是在问拉塞尔,倒不如说总统是在问自己。
"你干吗不给他打个电话,问他本人呢?他绝对坚持的唯一一点,是你要把这个消息转告沙利文。""沙利文?我为什么要……"总统没再想下去。他打电话找伯顿。但接电话的人告诉他,伯顿突然生病,去医院了。
总统的两只眼睛死死盯住办公厅主任。"伯顿会去做我认为他应该去做的事吗?"
"那要看你认为他应该做什么。""少来这一套,格洛丽亚。你很清楚我指的是什么。""如果你指的是伯顿想确保这个人不被拘捕,那答案是肯定的。我也想过这个问题。"
总统用手指抚摸着办公桌上一把沉重的拆信刀,重新坐回椅子上,脸向窗外。看见那把刀,拉塞尔浑身一颤。她已经把自己办公桌上那把扔了。"艾伦?你想让我做些什么?"她瞪着他的后脑勺。他可是总统,你只有在那里耐心等待的份儿,哪怕你恨不得伸手把他掐死。
他终于转过身来,那双眼睛乌黑、冷漠、逼人。"什么也不用做,我不让你做任何事情。我最好还是跟沙利文联系一下,把行动地点和时间再跟讲一遍。"向总统复述信息的同时,她早先脑子里有过的想法又浮现出来。哼,还是朋友!
总统拿起电话。拉塞尔伸过手去,按住他的手背。"艾伦,尸检报告上,克里斯蒂娜·沙利文下巴上有很多伤痕,她差点被掐死。"总统没有抬头。"噢,真的吗?""艾伦,卧室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嗯,我只记得一些小片断。她比我还粗暴。你说脖子上的伤痕?"他顿顿,放下电话。"这么说吧,格洛丽亚,克里斯蒂娜有很多怪癖,包括性窒息。你知道的,有些人高潮时要喘不过气来才觉得销魂。""这个我听说过,艾伦,我只是没想到过你也有这种癖好。"她的音调很耳。
总统反唇相讥:"别忘了你的位置,拉塞尔。我没必要向你或任何人交我的行为。"
她后退一步,赶忙说道:"当然。对不起,总统先生。"里士满脸上的表情这才缓和下来。他站起身,摊开双臂,表示不再计。"我也是为了克里斯蒂娜。格洛丽亚,怎么说呢?女人有时对男人有奇的影响力。我对此肯定没有免疫力。""那么,她为什么企图杀你呢?""正如我刚才所说,她嫌我不够粗暴。她当时喝醉了,已经失去自控能。是很不幸,可事情就是发生了。"格洛丽亚的目光从他身体上移向窗外。克里斯蒂娜·沙利文的事不是偶然"发生的。去那个地方会合的时间和计划都是精心策划的,最后居然和激烈的竞选挂上了钩。那天夜里的情景又涌入她脑海,她摇了摇头。
总统走到她身后,抓住她的双肩,将她的身体转过来面对着他。
"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这都是一场糟糕的经历,格洛丽亚。我当然不想让克里斯蒂娜死。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我去那里本来是为了跟一个漂亮女人过一个温馨、浪漫的夜晚。我的天,我可不是魔鬼。"他脸上掠过的笑容让你自然地消除了戒备之心。
"这个我知道,艾伦。只不过有那么多女人,发生了那么多次。糟糕的事就在所难免了。"
总统耸了耸肩。"嗯,正如我以前跟你说过的一样,在这个职位上,我不是第一个从事这种业余活动的人,也不是最后一个。"他用手托起她的下巴。"格洛丽亚,你要比大多数人都更了解对我这个职位的要求有多高。世界上再没有其他这样的工作了。""我知道你的压力很大。这个我明白,艾伦。""是啊,这个工作的要求远远超出凡人的能力。有时,你得把自己从老虎钳中挣脱出来,释放一些压力,只有这样,你才能面对现实。我如何缓解这种压力是非常重要的事,因为它决定了我可以为人民工作得多好。他们选择了我,他们把信任寄托在我身上。"他转身回到办公桌旁。"此外,和美女共度良宵是一种相对无害的排解压力的方式。"格洛丽亚愤怒地盯着他的后背。他好像指望她,代表所有人,被这番狗屁爱国演讲打动似的。"但对克里斯蒂娜·沙利文来说,那肯定不是无害的了。"她脱口而出。里士满转身面对着她。他脸上已经没有了笑容。"我真的不想再谈论这个话题了,格洛丽亚。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该考虑未来了。明白吗?"她毕恭毕敬地低头表示赞同,然后大步走出房间。总统又拿起电话。警察精心设置了圈套,他要把所有必要的细节都告诉好友沃尔特·沙利文。电话接通的过程中,总统不禁笑了。看样子问题很快就要解决了,他们已差不多取得胜利了。他可以指望伯顿,指望他正确行事,为了他们每个人。
卢瑟看看手表,才一点钟。他冲了个澡,刷了牙,然后修了修刚刚长出的胡须。他在头发上下了好大功夫,直到满意为止。他今天的气色看上去些了。凯特的电话产生了奇迹。他曾把听筒放在耳朵上,一遍又一遍地听个留言。他就是想听听那个声音,听听那些他从来没指望过还能再听到的。他还冒险去了市中心的一家男士用品商店,买了一条崭新的宽松长裤,件运动上装,还有一双黑漆皮鞋。他还考虑过买条新领带,但后来又放弃那个念头。
他穿上那件新上衣。感觉不错。裤子显然有些太宽松了。他瘦了,得多一些。他甚至可以请女儿吃顿晚餐,以此作为谈话的开始。不过不知她是愿意。他不得不想想这个问题,他不想勉强她。
杰克!一定是杰克!他肯定把他俩见面的事告诉她了。他告诉她说她父现在遇到了麻烦。前因后果就是这样,肯定是这样。他真蠢,当时怎么没应过来。但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她在乎我?他感到脖子颤抖起来,且这种颤抖自上而下地游走,最后他的双膝也哆嗦了一下。这么多年过去后,她在乎起我来了?他低声诅咒着命运做出的这种时间安排。时机选得该死!可他主意已定,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能改变这个决定了。就连他心爱女儿也不能。罪恶必须得到严惩。
卢瑟确信,里士满对他和办公厅主任之间的通信一无所知。她唯一的希是悄悄地把卢瑟手中的证据买下来,以确保没人能再看到它。她只想收买,希望他就此永远消失,让世人永远不知道这件事。他已经核实过,汇款经到达了指定账户。对那笔汇款的处理方式将成为他们的第一个惊奇。不过,第二个惊奇才会使他们全然忘掉第一个惊奇。最精彩的是,里士将毫无察觉。他十分怀疑总统会在任何时候知道自己就要完蛋了。但是,果这都还不符合弹劾的标准,那他就不知道还有什么才符合标准了。这件让水门事件看起来都像小学三年级学生的恶作剧了。他不知道以前那些被劾的总统都做过些什么。他希望他们是在自取灭亡的烈火中消失的。
卢瑟从口袋里掏出那封信。他要安排一下,以便让她在期待最后一个指的时候收到这封信。至于回报嘛,她会得到回报的,他们都会得到。这很值得。她会坐卧不安的。他知道,这段时间以来,她一直如坐针毡。
尽管他一再努力,可就是不能把记忆从脑海中抹去。那个女人从容地在一具还有余温的尸体旁边交媾,好像那个死去的女人是一堆垃圾,根本不用去在意。还有里士满,那个烂醉如泥、口流涎水的狗杂种!那一幕幕情景再次让卢瑟怒火中烧。他气得牙关紧咬,然后脸上又突然露出了笑容。
无论杰克能替他争取到什么刑期,他都认了。二十年也好,十年也好十天也罢,他已经不在乎了。让总统和他周围的人都见鬼去吧。让这个城市所有的人都见鬼去吧。他要煞煞他们的威风。
但他先要去见见女儿。然后,他就真的什么都不再在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