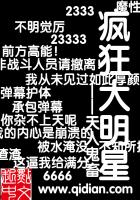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要做的事情是,去卫生室,和撞三次墙。当然我还总是会想起王蓓,我真的很想她。
卫生室的那个姑娘叫沈思思,每次在卫生室里见到她的时候她总是笑语盈盈。我在一旁看她给别人买药和扎针。她对我说过:我每天都要给人扎针,每个人都不止扎一针,我都快麻木了,现在看到别人的手臂都想拍几下。
不过现在我得说说我们的正事儿了。
火车站是个好地方,比公交车上有意思多了。我们不敢进到车站里面作案,因为里面装满了监控,而且由于疤庄的治安太差,车站出口还有荷枪实弹的武警把守。在这里作案除了我们几个之外,还有一个经验丰富的台湾人,他叫阿明。阿明一脸的雀斑,他自己却非说那是没长成熟的痣。他说话嗲声嗲气,起初我还以为他是装的,后来听说他是台湾人,才理解。王易是爱国青年,这点无需我多说。他总是爱缠着阿明让他说些台湾的事,逼到最后让阿明吟诵那首余光中的《乡愁》他才罢休。跟对待韩国佬不同,王易对待阿明显得温柔得多,毕竟大家是同胞。更重要的是,他们之间不必为了争中秋节而闹的不愉快。
阿明不喜欢跟王易说这些事,既然大家都是中国人,干吗非得讨论那些乱七八糟的事。阿明年纪不小,个头不高,不过下手狠。我们作案的对象大多是些老年人或者妇女,信哥告诉我们,一定不能抢别人的证件,不然别人就会报警。一般人知道疤庄治安不好,通常都会把小钱放到口袋或钱包里,别人来抢,老实配合就好了。
在我们行业里,不把“作案”称为“作案”,而是一个很诗意的称谓:嘘嘘。
这个在别人听来是上上厕所的意思,在我们眼里异常神圣。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用这两个字来代替“作案”,“嘘嘘”有两个意思,一个表示搜别人的裤子,一个表示脱自己的裤子。
有阿明和信哥在,我们的嘘嘘就会进行的很顺利,要是有时候他们不在,可能就会遇到麻烦。
我的工具是匕首,是单刃的匕首。因为刚来到疤庄的时候我们被劫过,所以就算信哥不教,我们也大概知道如何嘘嘘。除了匕首之外,我们还有一样工具,是一个写有“住宿”两字的牌子。我就不解释它的作用了。
车站外面集结了大量的人,他们都是些没有表情的人,就像不敬业的群众演员一样。纵观整个车站,最有活力的只有我们了。我们看准了一个目标,他走出车站,提着重重的箱子,这种人也常常成为我们作案的目标。我们举着住宿的牌子走向他,他不耐烦的摇着头,我贴近他,用刀背挨着他。他立即举起左手,右手提着箱子。他说:哥们,同道中人。
我心想,以前我被劫的时候怎么没想到这样说。老方和王易才不管这些,往手心吐了口口水就搓着手走上去搜身。
那人把肚子往前一顶,刀口划在我的手上,我觉得自己流血了。他说:这是嘘嘘人的弊端,总是习惯把刀口对自己,怕伤到别人。
老方王易停止了动作,我抬起手,鲜血顺着我的手臂往下流。时隔多月,我再次晕倒。
需要解释的是我并不晕血,晕倒的原因可能是太热了。但是他们却以为我晕血,后来拿刀子的事就不让我干了。
拿刀的任务就交给了老方,他做了改善,把刀背对向自己。
目标从远处走来,我们早就开始注意到她了。她看起来年纪不大,但也不能用“小姑娘”来称呼她,一脸的浓妆,眼影都画到眉毛上了,拉到片场就能演科幻片。另外小腿很粗,大腿和小腿一样粗,从远处看就像两根柱子。两根柱子支撑着一副复杂的躯体,极有节奏的走出车站。一般对付女性目标我们都不会用到那个写有“住宿”的牌子。
目标出了车站,我们扔掉烟头,像斯巴达将士走向波斯军队一样坚毅的走向她。
等她注意到我们时,老方已经把她拎到一边,边上的人虽然全都川流不息,却都跟没看见似的,因为这种事在疤庄的火车站太常见了,有时候走出车站没看见抢劫的还会觉得不习惯呢。女子被吓懵了,老方已经把刀架在她脖子上。我都害怕老方会一不下心杀死她。
老方说:钱拿出来。
我们这行有个规矩,绝对不能搜女人的身,因为在疤庄不能容忍猥亵罪蔓延,更重要的是犯猥亵罪会被同行耻笑。在看守所里,最高等的是杀人犯,最低等的是******,最最低等的是强奸犯。
我们围在女子四周,她脸都吓白了。
老方以为女子没听懂,于是用标准的普通话说了一遍:把钱拿出来。
女子不说话,眼珠往上转,然后倒在地上。我们三人立即互相看了看,接着低头看地上的女子。她先抽搐了几下,翻了个身,然后口吐白沫。他们两人互相看了看,我没加入进去,因为我很早就认为面面相觑不是好事。我说:怎么办?
老方说:空手而归是个大忌,一次失手,步步失手。
一个行人走过来低头看女子,然后问我们:怎么回事啊?
我说了声“没事”就把他往外推,他看起来并不胖,我使了一个足以令一个胖子往后退三步的力气,但没能使他退后。我再次发力,他还是纹丝不动,我心想这是高人。再一细看,他背后竟然站满了人,四周也围满了人。我挪了一步,差点踩到地上的女子。而老方和王易早就离开了人群,并且消失在人海。
我的四周围满了人,他们嗡嗡嗡的说着什么,我恨他们一如鲁迅笔下的看客。黑压压的一片,我的阳光被遮住了,没有了阳光我就觉得自己快要窒息,并且想到自己快要晕过去了,接着我就真的晕过去了。
醒来时我的身边一群护士在摆弄针管,窗子外面就是云彩。我在想自己是升天了还是马上要被这些护士送上天了。一个护士看到我,惊奇的说:呀,你醒了。
这群护士纷纷扭头看我,药水顺着手上的针管往下滴。我突然觉得自己左手挺疼,具体哪里疼我也说不上来。我想看看自己的左手,但是抬不起来它。我想扭头但是觉得头顶上也很疼。只好用右手摸我的头,一摸就觉得不对劲,头发居然没了。我说:我的头发呢?
护士们不说话,咯咯地笑。
再仔细一看,旁边柜子上全是用过的针管。我说:怎么回事啊?
一个护士坐到我床边,装作很可爱的样子,掀开我左手上的被单。我吓了一跳,因为多多少少我都有些密集恐惧症,左臂上居然全是针孔。我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她说:我们都是实习生。
我说:然后呢?
她说:我们看你血管粗,就在你手臂上实习了。
我说:我的头发呢?
边上站着的一个护士说:有些孩子需要在头顶上扎针,我们就剪了你的头发借用了你的头顶。
这个护士左手拿着针管,右手上拿把剪刀,上面沾满了头发。我问她:你也是护士?
她脱掉护士帽,然后扯掉护士服,一头黄发落在肩上,说:哦不,我是理发师。
我说:你也扎我了?
其他人还在咯咯地笑,她轻声说:我只想试试。
我想说话,又觉得有地方不对劲,便用舌头舔了舔自己的牙齿,少了好几颗。我大声说:我的牙齿呢。
又一个小姑娘颤颤巍巍的走向前来:对不起,我是学牙科的。
我准备起床,腹部感到一阵疼痛,一个戴着口罩的姑娘连忙过来扶着我,她眨巴着眼睛说:你还不能起床。
我说:你们又做了什么?
她说:我在边上看她们扎你,就一时短路觉得你是刚从福尔马林里捞出来的,破开你的肚子顺便割了你的扁桃体。
我摸了摸喉咙,她往前一步说:不对,我割的是阑尾,这两样东西我老是分不清。
我说:那我的肾还在吗?
她低着头说:我没找着,刚计划着给你切****的,你就醒了。
我不敢再跟她们说话,只好换掉衣服准备走人。临出门,那群姑娘叫住了我。戴口罩的姑娘快速眨着眼睛,我还以为她要跟我说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结果她说:你刚开完刀,这卷胶带你拿着吧。
她手上是一卷很厚的透明胶带,我从来没在医院见过这种东西。她说:先缠几圈吧,万一伤口没缝严实。
说完,那群护士就冲上来扒光我的衣服给我缠胶带,在我的肚脐眼四周缠了一道又一道。戴口罩的姑娘说:千万不要做剧烈运动,要是真得运动的话,你就再自己多缠几圈吧。
我说:我到底得了什么病?
戴口罩的姑娘说:反正你不是阑尾炎。
我不愿久留,穿上衣服就走了出去。走出院门时我回头一看,疤庄县医院。
回到信哥家,他们已经开饭了,两小孩正试着啃碗,唐兰坐在角落里默默落泪,其他人全都抬头看着我。我一言不发,走进唐兰的房间。
不一会儿信哥冲进房间,焦急的说:我爸还等着你呢。
伺候完老人家吃饭,出来时桌子已经清理好了,信哥和他们坐在桌子边看着我。他们做了个手势,让我过去坐。我坐在信哥旁边,老方最先开口说话:你没事吧?
我笑说没事。
王易说:我们真不是有意丢下你,当时你已经被人群围住了,我们看不见你,以为你跑出去了。
我说没事。但是我知道事实并不是这样,他们当时肯定还能看见我。
回到房间时,唐兰已睡熟,她的大腿露在外面,我知道她只穿着内衣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