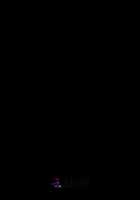带上他曾经用过的一些用品,跟我到芒街去找他,牛慧说,我知道他的脾气。我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把牛慧的话当做耳边风。牛红梅说我太累了,已经没有再走下去的力气,现在我需要睡觉。牛慧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严肃认真地看着我,说他是你们的父亲,又不是我的父亲,你干吗一动不动地坐着?我说我宁愿他死了。牛慧抽动双肩,发出神经质的尖叫,说你真没良心。我说我宁愿他死了,他为什么还要活着?为什么在消失十年后,又回来打乱我们的生活?只要他还活着,就说明我们全错了,何碧雪错了,金大印错了,牛青松白死了,我们白活了。因为他的出现,我们所做的一切,包括我们为他流过的眼泪,全部变得没有意义了!
牛慧像是被我说服,带着征求的口气问,那还去不去找他?我说不去。她沉默了几分钟后,跑到我卧室的书桌边,寻找牛正国曾经用过的用品,从书桌里翻出几张旧照片、一把旧牙刷和一支旧钢笔。她用手抹这些旧东西,想把上面的灰尘抹掉,一边抹一边说还是去见一见他,说不定他发财了,我们可以分一杯羹。
第二天,我背着还未打开的旅行包,跟随牛慧向着东兴进发。牛慧要去见她阔别十年之久的哥哥,我代表牛红梅、牛青松去见曾经死去、现在又复活的我们的父亲。青松已死,父亲健在,我愤怒、恐慌、好奇、悲伤、怀疑地坐在汽车上,想象我父亲的模样。牛慧问我见到他时会怎样?她连拥抱的姿势都已经想好,并且决定给他一个吻,这将是她此生中献给男人的第一个吻。我告诉她我一点儿都不激动,我很想激动,但是我的大脑、心脏它们一点儿也不激动。
牛慧通过熟人,在东兴办了我们两人的临时护照。我们踏上木船,夕阳正好西下,北仑河红得像一摊血。船每移动一下,河水就皱起一条又一条波纹,人的倒影、土堆的倒影、楼房的倒影全都不见了,只有晚霞的倒影那么红色地刺激我的眼睛,好像要把我的眼睛刺瞎。一船人说着乱七八糟的语言,他们的语言从船头飘到船尾,又从船尾荡回船头。我想起胡须飘扬满身伤疤的哥哥牛青松,我们的船仿佛正从他的尸体中间穿过。我提高警惕,认真聆听周围复杂的空气,仿佛闻到了父亲的气息。他的这种气息,在几十公里之外,我也嗅得出来。
姑姑手里拿着父亲给她的信件,迈着殷勤的步伐。尽管她年过40,但她的身材苗条,女性的气息饱满。我用力迈开大步,总跟不上她的速度。她近乎小跑,好像要一直跑进父亲的怀抱。遇到十字街口,我们就停下来,向行人打听父亲留下的地址。他们听不懂我们的话,我们也听不懂他们说些什么。牛慧用手指把他们的目光拉到信纸上,他们仍然摇头。他们不认识我父亲写的汉字。
我们只好站在路口,等待机会,对所有从我们面前走过的人点头、微笑。姑姑叫我对着街口喊谁知道芒果路10号。我说我不喊,要我这样喊,还不如回家去。姑姑白了我一眼,很失望,用手抹了抹颈脖,对着街口喊谁知道芒果路10号?谁知道芒果路10号?她的喊声尖利高亢,十足的美声喊法。在她的喊声中,几十张面孔稍稍调整了一下角度,面对着她。面孔们或笑或不笑地看着姑姑,他们或许认为姑姑正在歌唱。他们只看了几十秒钟,便背叛了姑姑的喊声,又把他们的面孔调回到他们原先保持的角度。
谁知道芒果路10号?谁带我们去芒果路10号,我给他100元人民币。谁带我去,我给他130元人民币。终于有一位我们的同胞,从人群中脱颖而出,迎着姑姑的喊声走过来。他说我带你们去。姑姑说走吧。他站在姑姑的身边不走。姑姑说走呀。他说先付钱。姑姑从小挎包里掏出130元人民币递给他。他的双腿为人民币而开始迈动,我们一左一右地跟随,生怕他突然跑掉。
左转大约200米,遇到一个路口。路口全是中国人开的餐馆。从一个粤菜馆的巷口往右转,过两个路口后再往左。他一边走一边抬头看门牌号,说快到了。我突然闻到一股特别的气味,这种气味铺天盖地带着越南人的特色,我一时还搞不清这是什么气味。越往前走,这种气味越浓烈,我抽一抽鼻子,想原来这是厕所的味道。他站在厕所前,转了一下头部,说怎么会是厕所?芒果路10号怎么会是厕所?他从姑姑手里拿过信,眼珠子在信纸上滚了一圈,然后说是这里,就是这里。我们认为他在行骗,所以拦住他。他指着厕所上的“10”说,这就是芒果路10号,我已经把你们带到了目的地。我们说不可能,这不可能是真的。他说怎么不是真的,这里明明写着芒果路10号。他冲开我和姑姑的肩膀,从来路走回去。从他气冲冲的步伐和摇晃的背影判断,好像是我们骗了他。
我们认真打量这两间厕所,它没有丝毫特别之处。它的左边画着男人头,右边画着一个女人头,墙根之下,堆着一大堆碎玻璃。我想父亲不可能变成厕所,假若窗口是他的眼睛,砖墙是他身子,那么他的头呢?在哪里?还有他的尾巴,他的尾巴会不会变成一根旗杆,立在厕所的后面?这样想着的时候,我的心头掠过一阵痛快,大声笑起来。我想我错了,父亲又不是猴子又不是孙悟空,他怎么会有尾巴?姑姑说你笑什么?这有什么可笑的。
天色完全暗淡了,我已经看不清姑姑的面孔。我说有人在开我们的玩笑?姑姑说是谁?我说给你寄信的人。姑姑说寄信的人是谁?我说我怎么知道?但是他一定知道我们,我们看不见他,他看得见我们。我们不知道他,他知道我们。姑姑说是谁在戏弄我们呢?
晚上住在一家简陋的旅店,姑姑一直没有睡意,要我陪着她说话。她把身边的人回忆了一遍,认为在她的朋友中或熟人中或反目为仇的人当中,没有谁会做这么缺德的事。她又把我和牛红梅的敌人过滤一遍,始终找不出合适人选。我感到很疲劳,说睡觉吧。姑姑说再说一会儿话。再说什么话呢?我实在找不出什么话好说,便问她为什么不嫁人?她的脸色很难看,站起来想走,但刚走出去两步,又倒退着回来,坐在那张唯一的椅子上。我说姑姑,你还是不是处女?她的脸突然红了。她竟然脸红了,跳起来走出去,好像屁股下忽然长出了钉子。她说我哥哥怎么生出这么一个儿子?我想姑姑终于走了,我可以好好睡上一觉了。
刚刚睡着,我就被一阵拍门声惊醒,拉开门,看见一位小姐站在门外。她不说话,只用手指做了一个下流的动作。虽然我还没有下流过,但我无师自通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我把她挡在门外,她用力往门缝里挤,快挤进门时,我猛一使劲儿,把门关上。她仍然拍打门板,声音悦耳诱人。如果她总这么拍下去,我会挺不住的,赶紧用枕头捂住耳朵。捂了一会儿,拍门声消失,世界上没有声音,我再也没有睡意,脑子里飞舞着小姐的各种器官。那些器官像塑料做成的,它们飞舞着,显得很虚假。我尽力想把它们变成真实的肉体,但我没这方面的经验。塑料继续塑料着,虚假依然虚假吧,我的脑子里突然蹦出这么一句。
又是一连串拍门声,它肆无忌惮地勾引我。我忍无可忍,决定打开门,把拍门的小姐抱到床上。房间里一片漆黑,走廊上的灯也熄灭了,我没开灯,摸索着走到门口。拉开门,抱起拍门的。拍门的双脚来回晃动,踢打我的腰部,由于害怕跌下去,她的双手吊住我的脖子。我把她丢到床上,床板发出一声喊。她说开灯,我是你姑姑,开灯。打开灯,我看见躺在床上的真是我姑姑,她的眼睛像是不适应灯光,依然紧闭着。闭了一会儿,她睁开眼,从床上爬起来。
姑姑说睡不着,所以把你叫醒了。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走了差不多两个小时,然后说戏弄我们的人会不会是吴明天?我问谁是吴明天?她说我过去的恋人。我说你谈过恋爱?她说谈过,我们还一起生活了好长一段时间。他要我跟他结婚,我不愿结婚。我认为爱可以超越一张结婚证书,何必那么不自信,非领结婚证不可。他说总要有一个说法。我不喜欢有说法,他一定要有说法,就这样我们分手了。就这么简单,我们分手了。我说你原来不是老处女?姑姑说谁规定我一定要做老处女,谁的规定?我说不是谁的规定,只是有人在背后曾这样骂你。
姑姑说了一会儿吴明天,又回她的房间睡觉去了。我不知道她能不能入睡,反正我是在极度疲劳之下睡着了。不知睡了多久,我又听到了敲门声。姑姑一边敲门一边叫我。我打开门。姑姑说我真蠢,我后悔了一个晚上,我们为什么不走进厕所去看一看,哪怕进去撒一泡尿都好,说不定厕所里藏有什么秘密。天亮之后,我们还得去厕所,不进去看一看就这么回去,我不甘心。
天很快就亮了。我和姑姑再次来到芒果路10号。姑姑说我进女厕所,你进男厕所,我们都进去撒一泡尿。我说我没有尿。她说没有也得进去。我说我不进去。姑姑跑进女厕所。我没有听她的吩咐,盯住墙根下那一堆玻璃。那些玻璃闪闪发光,有几块稍大的出现了我的头像。在我的头像后面是一间三层的楼房,有两颗脑袋正伏在二楼的栏杆上,张望我的后脑勺。我猛一回头,好像看见了牛正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