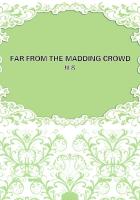我听到哐地一声,战士把我们价值连城的铜盆和九龙壶丢在屋角,那里已经堆了一大堆类似的东西。他们说假的,你们走吧。我们又坐回的士,好像又回到了人间。司机掉过车头,把我们拉回翠亨。坐在车上,牛青松一言不发,像是被吓呆了。回到405号房间,牛青松一头扑到床上,失声痛哭,眼泪像泉水一样从枕巾的两端汩汩而出。我伸手拎住他的衣领,问他为什么哭?他不回答,只是哭。服务员听到哭声,打开门跑进来,问我出了什么事?我说我也不知道。服务员拍拍牛青松的肩膀,问他是不是哪里不舒服?牛青松摇头,仍然哭着。我说他失恋了,你不要去惹他。服务员提着一串密密麻麻的钥匙走出去。
我最听不得哭声,特别听不得大人的哭声,一听到哭声我就想打人。我庄严地举起拳头,说如果你再不停止这种声音,我就揍扁你。他用手抹一把眼泪,说10万元,10万啦!为什么别人那么容易发财?为什么10万元眼看就到手了还要飞掉?为什么别人可以享尽荣华富贵,我却险些坐大牢?为什么别人可以去美国,我连长城也去不了?我仅仅是想给牛红梅买一套裙子,给牛翠柏买一套西服,可是我连这一点都做不到。牛青松不是在哭,简直是在唱。他这么一唱,我的鼻子也有些微微发酸。我把牛仔包从窗口丢出去,他也把牛仔包从窗口丢出去。他说都怪你。我说怪我什么?我们不挨坐牢已经万幸了。他说我原本是来找我父亲的,可是你偏要我跟着你搞什么古董生意。你说我父亲在翠亨,现在你告诉我,他在哪里?
翠柏,你知道,我对你父亲在不在翠亨没有一点儿把握。我只是为牛青松提供一个假情报,目的是想让他跟着我做成一桩生意,然后让他发财,让他人模狗样地抖起来。但是我的好心被狗吃掉了,牛青松根本不能体会我的用心,只是一个劲儿地质问我。
当时已经是晚上八点多钟,我们都不开灯,只有狮子和老虎的嚎叫,填满了黑暗的房间,我和他彻底地闹翻了。当一个人的好心被人误解时,那是多么令人伤心啊。我说你滚吧,我再也不想见到你。我刚这么一吼叫,就立即后悔了。牛青松在我的吼声中拉开房门,走了出去。他走出去时的背影我至今仍记得,他关门时的愤怒声也不时地回响在我的耳朵边。现在,我也仍在为我的那一句“滚吧”而后悔。牛青松就那样消失在翠亨茫茫的夜色,也许说他消失在路灯的光芒中更为准确。我知道他身上已没有多少钱,拉开门追出去,问他需不需要钱?现在要往什么地方去?他推开我,说别管我,我去找我的父亲。我很想跟他说你的父亲我压根儿没有见过,他已经死了,但是我想让一个人拥有希望,总比让他没有希望好。就这样,我和抱着希望的牛青松分手了,我看着他充满希望的身影消失在翠亨隐约的路灯的余光中。
我跟随刘小奇在翠亨转了两天,没有牛青松的任何消息,我想翠亨之行该结束了。当我们收拾行李,准备离开405房时,刘小奇在翠亨结交的朋友姜八闯了进来,他告诉我们,牛青松曾有一段时间住在群乐旅店,那是一个极不起眼的旅店。
姜八带着我们转了几个小巷,我们看见一块破烂的招牌,上面竖写着“群乐旅社”四个大字。在招牌下坐着一位肥胖的中年妇女,她正在一只大塑料盆里洗窗帘,周围全是污水和肥皂泡。她看见我们时,脸上的五官堆叠到了一起,说住店啦?姜八说不住。她说不住店来这里干什么?姜八说找一个人。她说找什么人?刘小奇把我推到妇女的面前,说找这么样一个人。妇女的双眼定在我脸上,眼睛愈睁愈大,好像我是一块磁铁。忽然,她把双手抽出水盆,不停地甩动,想把手上的肥皂泡甩干净,但她还没有甩干净肥皂泡,便用健康强壮的双手抓住我的右手臂,我感到她锋利的指甲已陷进我的肉里。她说你终于回来了。
姜八问妇女到底是怎么回事?妇女说我在她旅店住了差不多半年时间,没有交一分钱住宿费便逃跑了。妇女说我是骗子,是流氓是阶级敌人。姜八说你有没有搞错?他是第一次来翠亨,你再好好看一看。妇女犹豫了一下,松开她的双手。姜八示意我们快跑。我和刘小奇像是被人拍打的苍蝇,撒开腿,皮凉鞋从那些污水上跳跃而过,把踢踏踢踏的追赶声甩在身后。我们像超音速飞机跑回宾馆,每人跑掉了一只皮凉鞋。
等了好久,姜八才回到我们身边。他告诉我们牛青松曾在群乐旅店住了半年时间,因为交不起住宿费,所以悄悄溜走了。老板娘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刚才还误把我当成了牛青松。我们把详细地址留给姜八,委托他打听牛青松的去向,只要一有牛青松的消息,就请他告诉我们。姜八拿着我们留给他的纸片,对着我们挥了挥手,我们便告别了翠亨。
其实,在我离开南宁去翠亨的第二天,牛红梅便收到了一封来自东兴的信,发信人牛青松。他在信上简单地汇报了他一年来的行踪,以及他去银行领走父亲留下的3000元钱的经过。就在我和刘小奇苦苦寻找牛青松的时刻,牛青松已经狗急跳墙,向牛红梅揭开了谜底。
牛红梅每天怀揣着那封信,期盼我从翠亨归来。她站在阳台遥望长青巷口,企图从平凡的人群中,突然看见我卓绝的头发。但是她看也白看,颈脖拉长了,我还没有回来。于是她每天在阳台上垫一块砖头,站得高看得远,目光越过楼群。我走进长青巷的那个上午,看见她站在四块红色的砖头上,大声呼喊我的名字,手里扬着几张信笺,想从阳台上跳下来。我推门而入,和她撞个正着,额头碰撞额头。我发觉她的骨头坚硬得可以,似乎不把我的额头撞出一个疙瘩誓不罢休。
不等我放下行李,牛红梅便把我推了出来,先在我口袋里塞了200元钱,然后又塞给我一个塑料袋,说没有时间了,你快点儿走吧。她推着我往车站走。在往车站的路上,她复述了一遍牛青松的来信,然后指着信笺的最后一行让我看:
8月26日下午6时,务必赶到东兴中越大桥桥头。
8月26日,也就是今天,如果你还不回来,我就得亲自跑一趟了,牛红梅说,边境证我已为你办好,塑料袋里是牛青松最爱吃的粽子,我亲手包的。如果你见到他,一定叫他回来。牛红梅不停地说,双手推着我的后背和臀部,把我硬推上拥挤的发往东兴的客车。
我是从客车的窗口跳下来的。客车到达东兴时已是下午6时30分,比牛青松约定的时间晚了半个小时。坐着三轮车赶到中越大桥桥头时,我没有看见牛青松的踪影。我提着塑料袋站在桥头等他,相信他会到来。
这时,我把目光投向那座经历过战争的桥,桥被拦腰炸断,两边的桥墩还保存着,许多钢筋裸露出来,像被炸断的血管。我的这种感觉在十年之后找到对应。十年之后我26岁,认识了一位钦州地区的诗人严之强,他在一首诗里写了这座桥,写那些裸露的钢筋是被炸断的血管。后来,中越关系恢复正常,这座有名的大桥再度修复,严之强写道:修桥,就像是对接那些血管。但是十年前,我孤零零地站在桥墩旁,傻乎乎地等待牛青松。
在我等待的过程中,有几丝夏天的风掠过发梢,桥下三四十米宽的河惊涛拍岸,对面是连绵的小山堆,上面布满碉堡。我向一个路人打听这条河流的名字,他告诉我叫北仑河。我足足等了一个小时,仍然没见牛青松,他失约了。正这么想着,一具膨胀的尸体从北仑河上游漂下来,一直漂到桥墩边。死者拖着长长的头发,像是一个女人,但我仔细看了一下,死者的嘴角和下巴挂着浓密的胡须,绝对不是女的。尸体在桥墩边逆时针转了一圈,向着下游漂去,他的五官和下巴、胡须消失了,尸体更像尸体。
我的脊背一凉,对着漂出去十几米的尸体叫了一声哥。尸体停了下来,并且慢慢地靠向河岸。我看见放大了的牛青松,他的身上布满伤疤。我说哥哥呀,你怎么变成了这副模样?说完,我一下子瘫坐在河边,对着哥哥的尸体痛哭,尖锐的哭声穿透异乡的天空,像一阵雨落在北仑河两岸。我忽然觉得我像一只遗落在荒原的羊羔,很孤单,好像地球上所有的人都死了,只剩下我凄凉地坐在河边……哥哥的尸体紧贴着河岸一动不动,河水从他的下面走过,波浪鼓荡着他。他做着要站起来的模样,但他怎么也站不起来。我把姐姐亲手包的粽子丢下北仑河,三个粽子激起三朵浪花,我感到粽子像刚从滚水里捞起来那么烫手。一切都充满着暗示,姐姐发烫的粽子,还有哥哥在桥墩边逆时针旋转的一圈。哥哥是不是要告诉我,他迟到了一个小时?
尸体停了十分钟,便恋恋不舍地漂走了。我对着漂走的尸体说请原谅我不能安葬你,哥哥,请原谅一个年仅16岁,身上只有200元钱、身处异乡的少年,他没有能力打捞你安葬你,只能让你继续流浪。我重复着这一句话,一直说到深夜。
第二天,我向河岸的居民打听有关牛青松的情况,向他们描绘牛青松的长头发和长胡须。他们告诉我,牛青松已在北仑河岸徘徊了近半年时间,起先人们以为他是偷渡者,后来又觉得他像走私犯,再后来都说他像诗人。他好像在河岸边寻找什么,上下求索,但好像永远没有找到。我说他是不是在找一个人?一位卖锑桶的中年人告诉我,他好像是在寻找父亲,有时他会站在柜台外边跟我聊天,说一说天气和物价。河对岸遍布地雷,一些动物常常引爆它们,每一次爆炸火光就会映红半个天空。他常常站在我的柜台边,看对岸的火光听那边的爆炸声,说他父亲肯定还活着。他想找到父亲,但没有办法进入越南。他相信他父亲在越南的芒街,说南方之南,北水之滨,指的就是越南芒街。
牛青松终于破解了父亲留在日记上的谜题,可惜还没有见到父亲,他便沉尸北仑河。我不知道他对父亲的猜测对不对?更不知道他的死因。带着这一大堆试题,我回到南宁。姐姐问我见没见到牛青松?那些粽子他喜欢吃吗?他为什么没跟你回来?我说没有见到牛青松,牛青松失约了。姐姐说我的天哪,他怎么能够这样?
在姐姐说“天哪”的时刻,姐夫杨春光正穿过南京火车站的检票口,爬上了西行的火车。他的肩上挎着一个半新旧的牛仔包,包里除了装着日常用品之外,还装着一双特别宽大的臭烘烘的球鞋以及两盒避孕套。你们能够理解杨春光带着避孕套回家,但你们永远也猜不透,他为什么携带一双半新旧的臭烘烘的比他的脚长出三公分的球鞋?
还差十几天,我就是艺术学院美术系的学生了。我从一大堆相册里翻出几张牛青松的相片,它们像秋天的树叶陈旧不堪。我支起画架,临摹牛青松的头像,他的微笑从相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