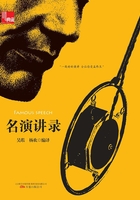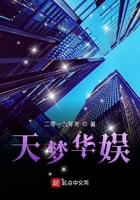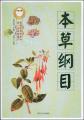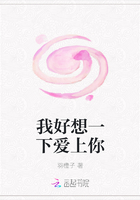《雨夜的列车》在2012年岁尾开来。
书何以此为名,有人问我。其实这个画面在我心中过了不止一遍,那种穿越的速度令人迷恋,那种流离的气息又使人感怀。每每踏上旅途,哪怕是短暂的一段儿,这种体验都能让人产生莫名的酸楚和忧伤。
——2007年从豫北涉渡黄河移居郑州,距今已五年有余了。
其间,火车不断出现在我的生活和睡梦中,连接着豫北和省会两地。现实中经历过的意象不断纠缠在我脑海里,仿佛已谱写了我的命运,“某个夏季的雨夜,从中原腹地驶来一趟奔腾叫啸的列车,它巨大的冲击力,犹如不可遏制的力量,裹挟着旅客驶向迷雾笼罩的目的地”。
工业化产物的火车本身就是现代社会的符号,人生的诸多感受在它身上交集。孤寒羁旅不仅是古人才有的情思,放到现代除了深感天地间的渺小无奈,分明还有一种速度的催迫与挤压。即使物质生活中的一切都安顿下来,现代人也难以摆脱失去心灵家园的困惑,这种危机感时时如影相随,难以消弭。
《雨夜的列车》是我一篇散文的题目,现在随手拎来拿它作了书名,以志这一时期的现实情态与内心世界。
对于我,文字分为两类:消息的与文学的。两者都在用力分争一个人的时间版图。媒体这份工作需要曝光自己,在一个又一个现场奔波,在规定的时间里画地为牢。
而文学的性情与之大为不同,它住在幽深悠长、铺着青石的巷子里,院里长着古树青苔,在隐居的静谧中投射自己的影子。
这样的矛盾统一在我身上,互作表述,难以平衡。文学是最私人化的事情,所以,最愿做的事便是清茶一杯,与内心交谈。
《雨中的列车》便是在碎裂的时间内孕育的产物。在电掣般的光阴里留下这些文字,宛若四季生长的植物,留下它们昼夜间的气息和静默的记忆。
民国才女张爱玲曾说:“时代在仓促中……”这句话拿到现在同样适用。
世上的变数与奇迹总是让人难以把握,给人们带来意外的恐慌或惊喜。2010年1月6日采访作家莫言后写下了《一声蛙鸣》,那时莫言还是莫言。将小文《一声蛙鸣》编入此书时,他已入列茅盾文学奖。书未问世,莫言已是天下尽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书店原本不怎么好卖的纯文学作品,也让莫言打破了纪录,莫言小说售罄,出版社未免窃喜。
在仓促的时代中,落在后面的普通人,日子繁琐忙碌如我,虽然少有色彩,但也种下了不可知的收获和机缘。
来到世上,我们带着自己孤单的面孔,去与众生融会,远远地会有人朝你走来,或是你远远地朝他走去,当彼此相遇,灵魂会传递出些微的战栗与惊喜。至此,我们会以为找到自己的“类”和“群”,心上冰雪似的寂寞不知不觉化开了,甚而以为,此生的一颗心可以借此托付了。一本书既是一个人的化身,愿它在茫茫人烟海中,能与读者相识相惜。
同上一本集子《彼岸灯花》一样,诗人兼画家冯杰先生又一次给予我无私支持,出版社的朋友说,冯杰的插图为这本书增色不少。(这)在我心里已不只是感动,而是骄傲这位师兄的深切情谊。
感谢河南文艺出版社的郑雄副总编、刘晨芳女士为这本书的出版所付出的辛劳!
感谢《莽原》杂志社主编李静宜老师为这本书作序。
2012年11月2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