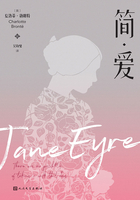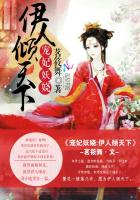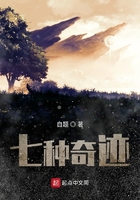“如果有江冬秀那个泼辣劲儿就不一样了。”
“(母亲)没有任何泼辣劲儿。”
季承说,他俩都值得同情。责任不在他们本人,因为这是历史的产物,这是一个历史阶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有什么好说的?你喜欢就喜欢,不喜欢也得喜欢,这是历史阶段。
孤悬海外长达十一年的季老,在二战爆发后,同家里断了书信,全然不知家里近况,但他无不时时挂牵,可季承还是说,父亲心里有,行动少一些。
生疏、隔膜一直横亘在父子之间。父亲留德回来首次回济南,十一年来的角色缺失使姐弟俩不知如何面见亲生父亲,“我记得,叔祖母一再嘱咐我和姐姐要有礼貌,见了父亲要叫‘爸爸’……我们虽然进行了练习,可是叫起爸爸来还是感到不自然。一直到现在,我对叫爸爸仍然觉得别扭”。
“对叔祖母、妻子儿女,对那个由他们组成的家庭,他虽感异己但没有背叛的勇气。他既不背叛,又不去培植爱……他是为了求仁,才委曲求全的……做文人固然美妙,但他身处一个没有爱的家庭,那文人做起来也不会快乐。”
可以体会到,儿子季承的每行字都有对父亲的怨怼,儿子当然期待父亲为他提供一个圆满的大家庭,其情融融,其乐融融。但父亲还是冷漠地拒绝,既不配合,也不抛弃,他这种中庸姿态难为了他一辈子,也给子女心灵上投去抹不掉的阴影。
“不完满才是人生”——季老曾这样说过。也是,大智大慧的季老没什么会看不开的。
倾听故乡的声音
啊啊,君不见秋天的树叶纷纷落下
我虽浪子,也该找找我的家
我听见我的民族,
我的辉煌的民族在远远地喊我哟
我的灵魂原来自殷墟的甲骨文
所以我必须归去
我的灵魂原来自九龙鼎的篆烟
所以我必须归去
…………
我的灵魂必须归家
君不见秋天的树叶纷纷落下
——痖弦《我的灵魂》
两年前的秋天,海峡对岸的诗人痖弦回来了。他的诗名含金量太高了,及至听说要在河南文学院与河南诗人座谈,我便心里捧着一束崇敬之花,从报社门口坐上K9出发了。
八十岁高龄的痖弦笑容可掬,奕奕神采,身上看不出一点儿暮色的影子。一位女诗人当面与他开玩笑:“很喜欢你这个老头儿。”
与痖弦相熟的诗人冯杰低语道:痖弦在舞台上饰演过孙中山呢,金嗓玉音,红极一时。抬眼再望时,便找出他气度不凡的因由了,原来他是有过舞台表演经验的,怪不得有如此魅力。
在诗人们的陪伴下,痖弦首先参观了河南文学史展览馆,馆里展示着各个历史时期的河南作家剪影。走到“痖弦诗人照片与介绍”板块前,痖弦停下来留影,文学院的领导有点儿忐忑地说:这个板块有点儿小了,我们计划重新整,整得大一点儿。痖老笑言,这个角落就很好。
痖弦用河南话与诗人们座谈,他风趣地说:我是1949年离开河南的,我的河南话还停留在1949年,河南话后来有所改变,我的河南话没有变化,可以说是河南话的活化石,可能还具有学术研究价值。
痖弦很关注河南的文坛,一直在画一个河南诗人地图。从古代到现代、当代,出一个诗人就画一个红点。痖弦说,河南人口多,文学人口当然多。河南的许多事业都在发展,文学也要加强。
痖弦讲与河南作家的交集,小时把姚雪垠读作姚雪“恨(谐音)”。为什么姚雪垠能写出《李自成》,还有一个原因,姚雪垠幼时豫西一直有土匪,从未平静过,姚雪垠也被土匪抓去过,本人有这样的经历。他评价姚雪垠的小说写得很人性,写农民如何变成土匪,变成土匪的人还会对着一块田地说,这是好地啊,一脚能踩出油。这是很深刻的人性描写。后来痖弦在新加坡见到姚雪垠,姚雪垠对痖弦说,俄国是文学大国,我们也是文学大国,自己写的字数不能少于托尔斯泰,一定要超出托尔斯泰。“看得出,姚雪垠是一个很雄健的作家。”
痖弦深情地回忆与苏金伞的见面……那是在十年前,当时我和他约定,拿着他的《窗外》和前来接站的人见面。《窗外》我保存了许多年,纸都快碎了。他回忆苏老的情诗:“……走着吻着,晚风把河里的星星吹得叮当作响。”
痖弦还谈到与自己同时期的南阳籍诗人周梦蝶。周梦蝶在台湾诗坛是一位很有影响的现代派诗人。因受佛教影响,他的诗歌具有浓厚的宗教情怀。但他是热爱生活的人,与一些女性有过交往,这份情感比柏拉图还柏拉图,对女性只是热烈地向往,他的诗干净纯洁,把世俗与禅味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周梦蝶现在台湾明星咖啡馆前摆书摊,过着一个苦行僧的生活。
在痖弦的讲述中,周梦蝶不仅是一个苦行僧,也是一个悲苦的父亲。离开大陆四十多年后,周梦蝶回到了南阳老家,留在大陆的儿子当时染病在身,最终死在父亲怀里,这一次是重逢也是诀别。
痖弦对编辑工作当作宗教性的使命来做。他说:我不会电脑,每天几乎要手书二十封信给作者。对于这样的敬业,如今没有哪个编辑能做得到。从这点看,痖弦十分富有牺牲精神,并乐于奉献,他自谦是一个失败的诗人,但是一个成功的编辑。据说,他以通信形式曾对席慕容等诗人的诗作点评多年,人格实为可敬。
他还说,故乡的肯定是最真的肯定,是最重要的肯定。
在诗人们的踊跃发言中,他听到了故乡的声音,故乡的肯定。与痖弦有着深切交往的文学院专业作家、诗人冯杰向痖弦献上一幅手书:我的灵魂原来自殷墟的甲骨文,所以我必须归去。我的灵魂原来自九龙鼎的篆烟,所以我必须归去。
冯杰与痖弦的交往由来已久,冯杰的诗文屡屡在台湾获奖,痖弦应是评委之一,但其投票制度相当严密,冯杰获奖是实至名归。痖弦笑着说,恐怕冯杰家里的房子都是用奖金买的。
在痖弦看来,诗是很不容易戒掉的瘾,诗也是一种信仰,宗教家可以以身殉道,诗人可以以身殉美,诗人的最高完成也就是诗的完成。
镌刻在汉砖上的图说
在我印象中,书法家以写字为业,收藏家以收藏为主,而将收藏与书法联姻独创出另一艺术领域的并不多见。当我打开刘炜东先生的《汉画拓本精品》,犹如打开一个神奇的汉画像瑰丽宝库,世相百态,人间天上,几可呼之欲出。与之相配的,是作者以各种书体专门为汉画写的题跋,呈现出艺术形式的缤纷异彩。可以说这本书填补了河南汉画像砖研究的空白,是汉画艺术与书法艺术的完美结合。
几年前的一天,作者的一位朋友为他带来几张汉画像砖拓片,看着那简洁刚劲、夸张大胆的线条,寥寥数笔勾勒出长袖飘飘的人物,昂首嘶鸣的天马,各种鲜活的生活场景,这位擅长金文的书法家被深深吸引了。从此,他的目光再没离开过这一神秘的方寸之地——汉画像砖。
中原地区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秦砖汉瓦,七丘八索,中原文化的精华除了《诗经》《汉书》等古书记载,以及钟鼎文饰的刻画,更为直观形象的则是汉画像砖(石)对社会生活的描绘,这是比诗书碑刻更为生动的古代中原文化,是最为原始的形象资料,而汉画像砖以河南出土的作品最为生动,它图解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反映了当时不同阶层的意识形态,有利于我们全面认识汉代社会。
对汉画像砖的痴迷与独钟,使刘炜东先生开始了艰辛的收藏和题跋。考证,阐释,旁征博引,《诗经》中的大雅小雅、汉赋唐诗,被他信手拈来,用文学的笔触,诗意地再现遥远的汉代。
这是一件寂寞而深具意义的事。无数个日夜他围着这些汉砖拓片,发掘着距今近两千年的汉代传来的信息密码,他忘记了身处的现代社会,精神与灵魂在汉代的天地大风中呼吸游走,沉醉逍遥,且独出心裁,将汉画像砖拓片一一装裱起来,再在旁边以大篆、行草书写题跋。各种书体大小不同,颜色不同,墨笔凝重,朱砂热烈,相互映衬渲染,巧妙相融。大篆有浓厚的金石气,隶书显得沉雄内敛,而汉简帛书风格的隶书,与画像中家居生活和田园风光相呼应,表现了书写者自然率真的心态,看去轻松随意,浑然天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