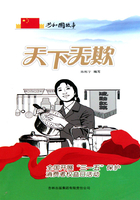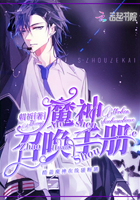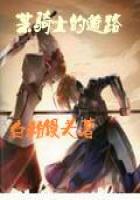“那时你父亲对我无话不谈,心里有什么烦恼都对我说。你父亲因为家贫,没有参加高考,选择了返乡务农。”杨伯伯接着说,“我考大学所进行的专业考试,似乎与这次下乡有关。在你家住的那段,你的一个伯母,正在缝制一个小孩裹肚,裹肚上要绣上‘五毒虫’图案,民间有这样的风俗,说是小孩在阴历五月穿上可以辟邪。你伯母知道我喜欢画画,便让我画一个五毒虫的画样给她……专业考试的题目是‘抗美援越’,考试时,你伯母左手抱着孩子,右手在刺绣的形象忽然给了我启发,我便画了这样一个农村妇女,绣的内容不是‘五毒虫’,而是‘保家卫国’四个字。当时国家正在抗美援越,这幅画很是吻合时事,主题切入的角度也很巧妙。”
“这幅画很关键吧?”
“当然了。老师们都给予很高评价。”杨伯伯还说,文化考试中的“作文”一项,也要求以“抗美援越”为内容,于是,他把专业考试的绘画过程用文字表述出来,照样考出了好成绩。
杨伯伯顺利考入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在河南美术出版社做编辑,直至退休。
嵩山笔会后,杨伯伯短时间内创作了系列嵩山山水画,分别是嵩山之月、之树、之路、之溪、之石。关于嵩山,他已写生多次,自然胸有丘壑。
伯母端详着杨伯伯的大作,会幽幽提出自己的见解:“太黑了,不该画这么黑。”伯母希望他画得眉清目秀。
杨伯伯不以为然,依旧温和地笑,但有自己的坚守,“我的画可能看起来没那么好看,不像市场上流行的画好卖,但我坚持自己的画法,不会为了迎合市场而去改变自己。超市里的顾客很多,那只是大众商品,有人买不能说明那些商品全是精品”。
他在一篇文论《砚边余言》中这样表白:“很多很高水平的画家的画,往往从一般审美者看来,其画面并不美,甚至是粗、黑、野、怪,例如黄宾虹、李可染、李苦禅等。然而,他们的作品却体现了中国画最高层次的美的本质与表现性。由此,在画面的形态的把握上,我选择了并不被常人喜欢的画面感。”
尽管他一直痴迷绘画,但编辑始终是他的主业,绘画始终是他的业余。白天他以一个编辑身份出现在出版社,尽职尽责,选题,组稿,看稿,设计书籍,忙着一个又一个程序。晚上,则在自己的画室里泼墨挥舞,恣意丹青,畅意抒怀山水之间。这时,他的思想是自由的,与山岳观照,与江河对话,驰奔在天地万物间,这样的工作与创作状态一直持续到退休。
由于常年在出版社当编审,广泛涉猎历史、哲学、文学、美学等门类,他的画给人以哲思和诗意。在他的书房,四屏野趣禅意画令人玩味。
那位独居千峰顶上的老僧,清雅安然,与云为伴,却比云还心定闲适。还有一幅画的是一方水田,三两低首插秧的农人,背后是笼罩在云雾中的山峦。题款是首禅诗:“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心地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杨伯伯说:“这幅画是我读禅诗时有感而作,中国的许多古诗词都具有禅意,本身就是一幅画。这些诗表达了古人专注淡定的生活态度,抒发了胸中的逸远之气。”
伯母讲,杨伯伯在编辑岗位上默默耕耘数十载,毕生专注于做事、作画,心无旁骛。其间曾有提拔升职机会,他却不似别人闻之则喜,而是闻之惶恐,生怕担任了行政工作而影响绘画,忙托人“辞官”。
他的这个举动让一些想做官的人不解,但从杨伯伯一心治画的态度上,从“退步原来是向前”的释义里,他的人生寄托就变得清晰起来。
杨伯伯退休后,没有了工作的挂碍,再加上淡泊心志的淘洗,画风有了大变。他说,作画,要追求一种看似平淡无奇,而越看越有深厚味道的画感。有的画纵有张狂瑰丽之状,却贫乏而无任何回味之处。要有一部分画家从热闹的展厅走出来,选择这种平淡的境界。
行走的诗意
金秋飒西风,我儿将远行
鸿鹄一冲起,从此万里征
…………
人本神兽体,善恶有两性
中人和西人,心理乃相通
谦谦与人处,急急勿互争
…………
学习艰又艰,在乎深邃精
中西都学会,法理皆溶融
国家有用材,凤凰栖梧桐
…………
身为母亲的我,不止一次被诗人高治军笔下情深挚浓的亲情所打动。爱孩子是一个连母鸡都会做的事情,但如何爱又是一个复杂的哲学命题。
爱子即将出国求学,诗人作为父亲,内心自然涌动着诸种强烈的情感,国外生活能否很快适应,学业能否顺利完成,孤独之感如何排遣。孩子年轻气盛,遇事会不会鲁莽冲动,还有时时刻刻的“安全”也萦系在诗人心头。隐隐担忧,切切叮嘱,谆谆教诲,布满了字里行间,阅之让人为之动容,共鸣。《示儿远行》诗近三十行,读后仍有不尽之意,浓厚的儒家思想加上深沉的中国式父爱,成为叩动心灵、充满哲思的教子佳篇。那天,得到治军兄的赠书《天籁之音》后,迫不及待地翻阅起这本厚厚的诗作,看到《示儿远行》,不由脱口吟诵起来,忙呼来孩子和家人共同赏读。私下以为,这是一封令人深受启益,以诗为简的现代经典家书。
这两年,常常跟一帮写诗的朋友搅和在一起,作为缪斯的孩子,大家忘记了年龄,诗词唱和,快意如歌。几位诗兄性情各异,在我印象中,出席在各种场合的高治军先生总是那么低调,言辞不多,但又分明给人厚重之感。他有着领导与诗人的双重身份,白天他处理着繁重驳杂的公务,晚上埋首在寂寂星空下耕云种月,收获着灵光乍现、翩然而降的优雅诗章。“勿负平生志,愿做一书郎”,“若问人生何为美,夜雨闭门读诗书”,更多时候,他把读书写诗当作自己的日常功课和心灵归宿。
2012年,他获得“河南诗人年度奖”,主办方的颁奖辞是“机智敏锐,平淡自然,凸现着才思和学养,这是高治军诗、人合一的真实写照。他的写作充满自觉和率性,不仅富有个性和想象的智慧,也显现出他很好地达成了诗人和社会人这两重身份的契合与互融。诗无新旧,只有好坏。打破形制,推陈出新,这是高治军‘新古体诗’的生根之壤”。颁奖辞十分精准地道出了他作为诗人和社会人“这两重身份的契合与互融”,以为他一向坚守的诗观。
在诗歌圈里,高治军是大家公认的劳动模范。数量之多产,意境之纯美,为同道甚为推崇。至今出版了《我手写我心》《沐春踏歌行》《大河飞歌》《微雨燕子飞》《明月清风吟》等八部诗集、千余首诗,几乎每年都有诗集问世。写诗不是马拉松赛,但在日日的坚持中却有了输赢分晓,如果把写诗比作一场马拉松赛,那么数十年如一日坚持“诗歌日记”,日有诗篇,年有诗集的高治军必定是当之无愧的冠军。他获得了诗神的桂冠,同样也获得了诗友的尊重。
高治军是带着自觉的使命意识去写诗的,他曾讲,游览时如果只是沉醉于风光,疏于思考创作,到此一游后印象全无,什么东西也不会留下。“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苏轼),及时记录思想的闪电灵光,是他生活中首先要做到的。在快节奏的今天,手机自然成了他随身携带的“文房四宝”,随时随地用手机记下脑海中涌现的清诗丽句,是他的创作习惯。他还以“手机”为题吟诗一首,赞赏它的得心应手与奇妙神通。
候车厅里,观赏途中,宴会间隙,当别人在高谈阔论,或是推杯换盏之时,都可能是他创作的良机和佳地。可以说,他几乎每天都沉浸在诗的氛围中,用诗记录生活,生活在诗意中开花,用“诗意人生”来形容他最恰当不过。
高治军是一个崇尚创作自由的人。所写的诗,大多不受格律限制。他在诗论中说,对于新古体诗,诗意、诗格永远是第一位的。诗很大程度上乃造意、命格而已。诗力求着意,无意则无魂。有了上佳的诗意、高尚的诗格,看似寻常的诗也是好诗。诗是诗人人格情操的外化,有什么样的人生境界,就有什么样的诗歌表达。几年前,他与老诗人贺敬之交往时有一段佳话,贺老器赏他创作的新古体诗,并收下他的诗集《大河飞歌》。与贺老的接触,再一次使高治军确定了自己的诗路和诗观。
“夕阳西下时,布谷声声里。亲朋三五个,伸手摘李子。”观眼前物,道心中诗,诗句来得寻常自然,它就像树上的李子,举手可得。还有一类诗则十分机巧,“但闻故人一一去,始觉新颜个个来。”写出贺知章《回乡偶书》的未尽之意。“谁说相距咫尺间,却翻心事万重山。”就像午夜里的小提琴,不适合白天的喧闹,只有在暗夜里独自聆听。“天上一玉轮,世间万颗心。不知今夜月,是否照莱茵。”这首思儿之作近乎白描,却情思丰沛,气息畅然,呼吸之间,出口成章。儿子求学地为异国莱茵,诗人仰望明月,思儿心切,于是,一首飞至海外的越洋诗诞生了。这首诗让人想起唐诗《春怨》中的思妇形象,“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两首诗的后两句,一个写“月”,一个写“黄莺”,都以独特意象成就了诗篇,在构思、韵律与节奏上多么相似,实乃异曲同工之妙。
“伊水奇兮,源自山央。伊水潺兮,汇入我乡。伊水远兮,悠悠古长。伊尹生兮,深山凤凰。伊阙开兮,龙门之旁。石窟成兮,举世无双。伊水秀兮,乐天诗香。伊水丽兮,多出佳娘。伊水伊人,在水一方。伊水涟兮,清波微扬。”整首诗一咏三叹,音节铿锵,韵味悠长。诗人出生于洛阳偃师,伊河与洛河在偃师交汇,交汇处恰在作者家乡的地头处。伊水是作者的母亲河,它孕育了先贤、诗香、佳人,充满了妩媚、斑斓和圣洁的形象。面对伊水清潆的波纹,诗人怀想古今,情感跌宕。
读高治军的诗,能够感受到一条贯穿古今的诗歌之河,诗歌的源头是诗经、楚辞、唐诗的古典神韵,中间流动着儒家的敦厚和道家的空灵,流转的光波里,又闪烁着现代精神意蕴的勃发与创新。
正如清人沈德潜所言:“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高治军的诗,或触景生情,或托物言志,或借古喻今,大都格调明亮、立意高远,展现了他内心的超拔和高标,带给人美的享受和哲理的启迪。“世上纵然黄金贵,怎及一片明月情。”“天上人间都寻遍,天堂原本人心间。”诗行间充满大道之美,大美之道。
“人生应有梦,无梦无人生。若有心中想,此梦终会成。”对梦的咏叹是他对诗歌追求的隐喻。对于一个诗人来说,梦就是诗之所在,写诗始终是追梦的美好过程。
“诗歌在远处,梦在远处,在游走时彼此才会相遇。”这是他的名言。不痴不成魔,在他平静敦厚的外表下,有一颗为诗而狂的诗心。这颗澎湃的诗心是他人生潮涌的动力,他因此而一次次远行,一次次手携诗囊而满载而归。
“诗词本系浮生事”。对于一位歌者来讲,他远行的不仅仅是脚步,而是一颗背负自由与理想的心灵。
激情、率真、坦荡,是高治军诗词的风格。他的诗里,没有纤弱、暗淡的情感粉尘,有的是洁荡、明亮的情感流波。他的情感,以流水的形态在诗里翻涌,他的诗,便也有了河流一样开阔的境界。他的人生旅程,是与众不同的快意的“踏歌行”。
晓白、简约、自然,也是高治军另一诗词风格。诗里有温度可感,有奇景可赏。正如他的人,没有一丝做作的派头,却蕴含着不寻常的情感。其实,人们对高治军致敬的原因,除了他多产瑰丽的诗作,更深层的还有他本身待人作诗的至善至诚。因而,人们愿意走进他的诗,更愿意走近他的人。
中庸姿态
一个偶然机会认识了某出版社社长,他谈起刚刚出版的《我与父亲季羡林》一书,用倾慕的口气介绍作者季承,说他是搞物理的专家,与物理学家李政道有着长达三十年的亲密合作,并出版有《李政道传》。
后来,收到了他寄来的这本书。它给我的印象是,搞自然科学的季承,文字有着学者的严谨,叙述自然真挚。书中采用写实白描手法,披露了父亲季羡林为外人所不知的一面,个别细节令我印象深刻。
季老对外人宽厚大方,对家人苛刻小气。比如,他常年因病住在医院,与护士的关系很是融洽,过节还给她们发红包。对家人,却是另一种情形。女儿要给家里置一台洗衣机,他不肯,原因竟是嫌洗衣机费水,让人不可思议。
2010年6月初,我和季承先生有过一小时左右的通话采访,季承先生和蔼、通达,不避讳,无保留,十分善谈,有着山东人的坦诚和直爽。
读了他的书,再加上一些交谈,季承的家庭及季羡林的感情生活渐渐真切地呈现眼前。
季承从小没有父亲陪伴,所以自然在感情上对母亲更倾向一些。季承母亲虽然文化水平很低,但人很朴实,按照传统来思考做事,即便很长时间和丈夫分离,后来婚姻也不那么美满,但她对子女非常爱护。对婚姻的遗憾,季承母亲并没有很多的表露,但懂事的季承很能体会母亲的心情,他和姐姐在母亲面前,尽量少谈这些事情,觉得这样对母亲更好。
成长过程中父爱缺失,心理会不会受到影响?季承回忆,在童年时期也没有感觉到特别的不适,好像也没什么影响。但是,是不是有了父亲陪伴会有什么变化呢?也不好推测。季承和姐姐后来都考上了大学。母亲文化水平不高,家务劳动沉重,但她抚养的一双儿女很争气。
作为男孩,季承对女性隐秘的心理并无敏感察觉。相反,姐姐与他不同,姐姐对家庭的事情想得多,且会表现出一些忧虑。
季承童年的无意识与后来和父亲之间的风波形成对照。因为写这本书,他也因此受到人们“犯亲”的指责。
在《我与父亲季羡林》这本书中,季承毫不避讳地把笔触伸向父亲曾爱恋过的女性:德国“伊姆加德”、山东济南“荷姐”,让读者从中窥探到季老丰盈动人的感情生活。最有非议的是照顾季老、与季老在一起长达十几年的李玉洁,季承说她是“一个有图谋的女人”。“并且季先生在她身上也有感情寄托,季先生的文章也有很动感情的叙述……这个人也有变化,她开始可能是一腔热情地来照顾季先生,后来就变了,想占有季先生。”
季羡林出国后夫妇一直是分离状态。回到中国以后,两人又没有真正在一起,没有夫妻之实,双方没有健康的婚姻生活。那么,他回国后真正的感情生活是怎样的呢?
回国后季老还正值盛年。在季承的书中看到,季老采取的是保守态度,既不婚后恋,又不婚外恋,而是一头扎在学问里,真有点圣人的味道。他这样选择,内心实在是悲凉和绝望,对自己也是一种自虐。
季承说:像我父亲这代人,婚姻处理方式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忍耐,另外一种就是完全背叛,这是两种极端。我父亲由于各种原因,最后选择了忍耐。似乎,从那时他就给自己的婚姻宣判了死刑,不过是无限期地缓期执行罢了。
季承告诉我,最近研究了几个民国人物。一个是鲁迅先生,一个是胡适先生。“胡适先生的情况我觉得还不错。这三个人(包括季老)是三种类型。鲁迅那么伟大的人物,他就不理他那个夫人,虽然住在一起,也不和她同居。我父亲呢,是捏着鼻子,也生了孩子,也在一起生活,但就不是夫妻的正常关系。这三个人三个典型,其中高低大家可以分辨。还有郭沫若,也是一种类型。这四种类型哪个好,说起来可能还是胡适比较好一些。江冬秀很厉害,把胡适抓住了,这是她的本事,和个人的本能有关。”
“这也说明你父亲很倔强,你母亲在他面前是不是很屈让、示弱?”
“是的,我们都是让着他的。”